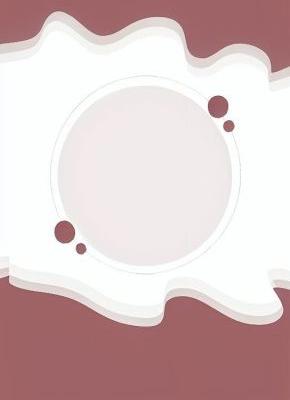
十六岁生日那天,我妈递给我一条新裙子。
湖蓝色的,化纤面料,吊牌上印着39元。
“穿上。”她避开我的眼睛,掏出一管劣质口红。
口红蹭到我牙齿上,味道像过期糖果。我爸在门口抽烟,看见我出来,吐了口烟圈:“走吧,要迟到了。”
“去哪儿?”我问。
他掐灭烟头,阴影笼罩下来:“去了就知道。今晚听话点,你弟弟下个月的药钱就指望这次了。”
弟弟李明,八岁,先天性心脏病,每月医药费两千三。
这个数字像把刀,悬在我们全家脖子上。
面包车在夜色中颠簸。车停在“悦来旅馆”门口,霓虹灯缺了几个字。我妈下车前,往我手里塞了块硬糖,绿色糖纸已经皱了。
“含着,别哭。”她的声音很轻。
307房间。
我推开门,看见他坐在床边——五十来岁,头顶微秃,肥胖的身体陷在廉价床垫里。他抬头看我,眼睛亮了一下。
“来了?把门锁上。”
那一夜很长。
疼痛像烧红的刀,反复切割我的身体。我盯着天花板上水渍的形状,它像一只破碎的鸟。时间失去意义,只有他沉重的呼吸,和我指甲陷进掌心的疼。
天快亮时,他终于停下,很快响起鼾声。
我艰难地坐起来。床单上一片暗红,蓝裙子下摆被血浸透,变成了深紫色。
扶着墙挪出房间。走廊尽头,父母在车里数钱。我妈接过我递去的劳力士表,在车灯下看了看,递给我爸。
“真货。”我爸吹了声口哨,“这趟值了。”
回家路上,我妈递给我止痛药。经过一座桥时,我摇下车窗,把手里黏糊糊的糖扔进河里。
糖纸碎屑还粘在手上,甜腻的味道渗进皮肤里。
回到家,弟弟在发烧咳嗽。我给他掖被角时,他迷迷糊糊问:“姐姐去哪了?”
“加班。”我说。
“加班赚钱给我买药吗?”
我的喉咙发紧,点了点头。
“姐姐辛苦。”他睡着了。
我回到房间,从床垫下摸出小铁盒。里面有四张糖纸,加上今晚的绿色,五张。
五道伤口,在月光下泛着微光。
天快亮了。我躺到床上,看着天花板的裂缝。
十六岁,花一样的年纪。
我的花期,在307房间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