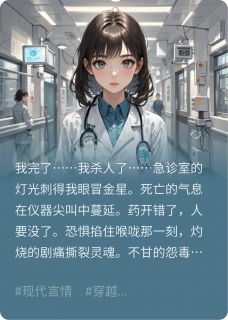
休息结束,正式去新科室报到。
我打定了主意要低调。
前世在皇宫太医院行走,深知藏拙才能活得长久。一个“实习生”骤然展露惊世医术,招来的绝不会只是赞叹。
于是,我谨遵这现代医院的规矩,用着那些奇奇怪怪的“仪器”,听诊器、血压计,尽力表现得像个普通的新手医生。诊断时,我刻意让自己慢一点,笨拙一点。
然而,真正的医者之心和对疾病的洞察力是藏不住的,尤其是我那融入骨血的“望闻问切”功底。
科室里送来一个被几个医生诊断为“普通感冒”而久治不愈的孩子,一直在反复发烧、打蔫。他母亲抱着他,满脸愁苦。
“用了好几种抗生素了,还是时好时坏…”
我放下听诊器。那仪器贴在孩子胸前传回的杂音只是佐证,我指尖搭上孩子细细的手腕,凝神片刻。
脉搏浮紧带滞。再看孩子面色萎黄,舌苔厚腻微黄,口唇微干却并非燥渴。
“这位小哥儿,这几天是不是没什么胃口?大便也不太通畅?”我温声问孩子母亲。
“对对对!医生你怎么知道?”母亲连连点头,“以前调皮得很,能吃能拉,这几天就不爱吃饭,拉稀又臭又黏糊糊的。”
西医用药压制了表象,但寒邪夹湿、困阻脾胃的根本没解,反被误伤了些中气。
“试试这个吧。”我顺手拿起桌上的便签纸,写下几味极寻常的中药名:藿香、苏叶、陈皮、焦山楂、神曲。剂量也标得极小。“这些药材药房应当就有,抓一剂,小火慢煎一小碗,每天两回,就饭前一小会儿给他喝。喝两天看看。”
我尽量说得轻描淡写,甚至有点底气不足的样子:“不是什么药方…就是家里常用暖脾胃、助消化的法子,没什么大碍的。”
两天后,那位母亲抱着活蹦乱跳的孩子回来了,找到我科室道谢,声情并茂。小小的科室被这充满喜气的母亲渲染得热闹了几分。
同事们有些惊讶地看向我。
类似的“意外”又在几天后发生。
一个被顽固性失眠折磨了半年的中年大叔,眼圈黑得像熊猫,整个人萎靡不振。常规的安眠药吃到量大了效果也不佳,反而让他白天头昏脑涨。
他一脸绝望地坐在我诊桌旁。
我让他伸舌,舌质淡红胖大,苔少薄白。搭脉,脉象细弱无力。这是典型的心脾两虚,加上思虑伤神、神不守舍。
“您平常是不是总爱琢磨事?想得多,晚上越想睡脑子越清醒?”我问。
大叔一拍大腿:“可不是嘛医生!这脑袋瓜一到晚上就跟装了马达似的停不下来!”
“试着…睡前一杯热牛奶,或者一小碗酸枣仁汤?小米粥加点莲子也行。”
我斟酌着用词,不敢提任何专业术语,说得像个民间偏方,“还有就是…用掌心,就这里。”
我伸出自己双手,掌心向内,“每天抽空在脸上搓一搓,尤其是太阳穴和眉骨这一圈,轻轻搓,搓热了,感觉能舒服些,可能…会好睡点。”
这其实就是最简单引导气血、安神助眠的推按导引,不算高深医术。
大叔将信将疑地走了。一周后,他专程来感谢,说虽然不是完全睡着,但每晚能迷迷糊糊睡上三四个小时了,而且白天精神好了很多。他觉得是我的“土办法”起了作用。
几次三番,效果立竿见影,又带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土气”,反而引起了不大不小的惊叹。
同事们私下里开始传,急诊室那晚之后,苏晴好像哪里不一样了,虽然看起来还是那个安静沉默的女孩子,但偶尔出手,总能误打误撞解决些小问题。
“行啊小苏,看不出来还有几手家传的偏方?”同诊室的赵医生半开玩笑地调侃我。
我连忙低头,露出点不好意思的浅笑:“就…以前老家学的土法子,糊弄人的,没想到瞎猫碰上死耗子了。”
这份刻意为之的低调,带来了一点意想不到的好处,一份不算亲密,却让我感觉还算温暖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