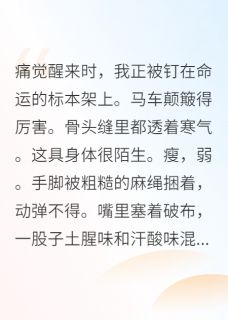
谢沉舟昏迷了整整三天。
高烧不退。
气息微弱。
王府里死气沉沉。
张伯寸步不离地守着他。
眼睛熬得通红。
王府最好的大夫被秘密请来。
诊脉后。
老大夫摸着胡子,眉头紧锁。
“奇怪…真是奇怪…”
“王爷体内那蚀骨之毒…似乎…被压制下去了?”
“虽然霸道反噬伤了元气,但那股跗骨之蛆般的毒性…真的弱了!”
“奇迹…简直是奇迹!”
张伯猛地看向我。
眼神震惊到了极点。
我守在一边。
默默听着。
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赌赢了?
那瓶不明液体。
真的是解药?
或者…是恰好能克制蚀骨的另一种奇毒?
无论如何。
谢沉舟活下来了。
第四天清晨。
谢沉舟醒了。
我端着熬好的清粥进去时。
他正靠在床头。
脸色依旧苍白。
但那双眼睛…
不再是死寂的深潭。
也不是血红的疯狂。
而是…
一种劫后余生的、带着深深疲惫的清明。
他看向我。
眼神极其复杂。
探究。
审视。
难以置信。
还有一丝…极其微弱的、连他自己可能都没察觉的…感激?
“是你?”
他的声音很沙哑。
很虚弱。
“嗯。”我把粥放在床边的小几上。
“那瓶药…”
“是原主…是我藏的。”我低下头,“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他沉默了很久。
目光落在我缠着布条的手腕上。
又移开。
“过来。”
我迟疑了一下。
走过去。
他伸出那只没有受伤的手。
苍白。
修长。
带着病后的虚弱。
轻轻。
握住了我缠着布条的手腕。
动作很轻。
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意味。
和他之前的粗暴冰冷,判若两人。
“还疼吗?”他问。
声音很轻。
我愣住了。
抬头看他。
他避开我的目光。
看向窗外。
枯树的枝桠伸向灰蒙蒙的天空。
“以后…”他顿了顿,声音依旧沙哑,“不用再放血了。”
我心头猛地一震。
难以置信地看着他。
“那毒…”
“压下去了。”他收回目光,看着我,眼神深邃,“那瓶药…以毒攻毒,虽然凶险,但…似乎真的解了蚀骨。”
解了?
蚀骨无解…
竟然…解了?
巨大的冲击让我一时无法反应。
“你的血…”他目光扫过我手腕上的布条,眼底闪过一丝极淡的…痛楚?“不再是药了。”
不再是药了…
这句话。
像一道惊雷。
炸响在我耳边。
不再是药奴了?
那我的价值…
“你…”他看着我,眼神复杂,“可以走了。”
可以…走了?
自由?
突如其来的两个字。
让我措手不及。
像在黑暗里待久了的人,突然看到刺眼的阳光。
不是喜悦。
是茫然。
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慌。
走?
去哪里?
这个世界。
我举目无亲。
身无分文。
一个孤女。
能去哪里?
王府再是牢笼。
至少…
有饭吃。
有地方住。
有…
我看着谢沉舟苍白的侧脸。
心里乱成一团。
“我…”我张了张嘴。
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张伯会给你备好盘缠。”他转过头,不再看我,声音恢复了惯常的平静,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足够你安稳度日。”
“离开京城。”
“越远越好。”
“忘掉这里的一切。”
他说完。
闭上了眼睛。
像是耗尽了力气。
“出去吧。”
我站在原地。
看着他那张苍白疲惫的脸。
看着他那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姿态。
心口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闷闷的。
有点疼。
我默默地。
退出了房间。
阳光有些刺眼。
我抬手挡了一下。
手腕上的布条。
在阳光下。
白得晃眼。
接下来的几天。
王府很安静。
谢沉舟在静养。
几乎不出房门。
张伯开始默默地为我准备离开的东西。
一个沉甸甸的包袱。
里面是几套崭新的、料子不错的衣裙。
一包碎银子。
几张面额不小的银票。
还有一盒上好的金疮药。
“这是王爷吩咐的。”张伯把包袱递给我。
他的态度很复杂。
不再有以前的警惕和审视。
多了几分…客气?
甚至…
一丝感激。
“王爷说…姑娘随时可以走。”
“府外有马车候着。”
“会送你到安全的地方。”
我接过包袱。
很沉。
压得手臂发酸。
心里也沉甸甸的。
“王爷…他怎么样了?”我问。
“王爷在静养,恢复得尚可。”张伯语气平静,“姑娘不必挂心。”
不必挂心…
是啊。
我算什么呢?
一个曾经的药奴。
一个歪打正着帮了他一把的…路人?
现在。
价值没了。
自然该走了。
“谢谢张伯。”我低声说。
张伯看着我。
欲言又止。
最终。
只是深深叹了口气。
“姑娘…保重。”
我抱着包袱。
回到那个小小的耳房。
东西很少。
没什么可收拾的。
我坐在床边。
看着这个住了几个月的地方。
窗纸是新的。
被褥是厚的。
桌子上有茶具。
炭盆里还有一点余温。
这里曾经是我的牢笼。
也是我在这异世唯一的栖身之所。
现在。
要离开了。
心里空落落的。
像缺了一块。
傍晚。
我最后一次去给谢沉舟送药。
张伯熬的药。
他靠在床头。
看着窗外。
夕阳的余晖给他苍白的侧脸镀上了一层暖金色。
少了几分阴鸷。
多了几分病弱的柔和。
我把药碗轻轻放在床边小几上。
“王爷,药好了。”
他转过头。
目光落在我身上。
又移到我放在旁边的那个包袱上。
眼神微微一暗。
“都准备好了?”
“嗯。”
“明日…就走?”
“嗯。”
一问一答。
干涩。
生硬。
空气有些凝滞。
他端起药碗。
黑褐色的药汁。
散发着苦涩的气味。
他皱着眉。
一饮而尽。
把空碗递给我。
我接过碗。
指尖不小心碰到了他的手指。
冰凉。
我微微一颤。
“王爷…保重身体。”我低声说。
他看着我。
眼神深邃。
像是要把我看穿。
“你…”他顿了顿,“出了王府,有什么打算?”
打算?
我茫然地摇摇头。
“不知道…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吧。”
他沉默了片刻。
“也好。”
“安稳度日…比什么都强。”
又是长久的沉默。
夕阳的光线慢慢偏移。
屋子里暗了下来。
“下去吧。”他最终说。
声音带着一丝疲惫。
“是。”
我端起空碗。
转身。
走到门口。
手放在门栓上。
脚步顿住了。
心里有个声音在叫嚣。
不甘心。
就这样走了?
像个用完就被丢弃的工具?
我猛地转身!
“谢沉舟!”
我喊出了他的名字。
他有些意外地看向我。
“你…”我看着他深邃的眼睛,心一横,“你就没什么话…想对我说吗?”
他看着我。
眼神极其复杂。
有什么东西在他眼底翻涌。
挣扎。
最终。
归于一片沉寂的深潭。
他缓缓地。
摇了摇头。
“没有。”
两个字。
冰冷。
决绝。
像一把刀。
狠狠扎进我心里。
最后一点微弱的火星。
熄灭了。
“好。”
我听见自己干涩的声音。
“我知道了。”
我拉开门。
走了出去。
没有再回头。
身后。
是沉入暮色的死寂。
第二天。
天刚蒙蒙亮。
下起了小雪。
细碎的雪花。
无声地飘落。
我抱着那个沉甸甸的包袱。
走出温暖的耳房。
冷风裹挟着雪粒打在脸上。
生疼。
张伯等在院门口。
旁边停着一辆不起眼的青布马车。
车夫是个沉默寡言的中年汉子。
“姑娘,上车吧。”张伯的声音在寒风里有些模糊。
我最后看了一眼这座沉寂的王府。
黑沉沉的。
像一头蛰伏的巨兽。
谢沉舟的主屋。
窗户紧闭。
看不到里面。
他大概…
还在睡着?
或者…
根本不屑于看我离开?
我深吸一口冰冷的空气。
压下心口那股尖锐的酸涩。
转身上了马车。
车帘放下。
隔绝了外面的风雪和…那座王府。
马车缓缓启动。
轱辘压在积雪上。
发出咯吱咯吱的轻响。
**在冰冷的车厢壁上。
抱着那个包袱。
看着车帘缝隙外不断倒退的、被雪覆盖的街景。
心里空荡荡的。
像被挖走了一大块。
自由了。
却感觉不到一丝喜悦。
只有无尽的茫然和…钝痛。
马车驶出城门。
外面的风雪更大了。
天地间白茫茫一片。
不知走了多久。
马车在一个岔路口停下。
车夫掀开车帘。
寒风卷着雪沫灌进来。
“姑娘,前面两条路。”车夫声音粗嘎,“一条往南,暖和,富庶。一条往北,冷些,偏远。您选哪条?”
我看着岔路口。
两条被积雪覆盖的路。
蜿蜒着。
伸向未知的远方。
往南。
温暖富庶。
往北。
寒冷偏远。
去哪里?
我茫然地看着。
雪花落在脸上。
冰冰凉。
融化。
像眼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