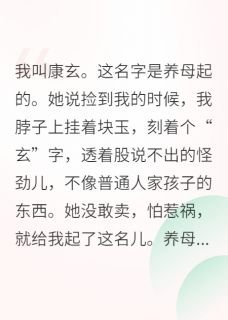
我叫康玄。这名字是养母起的。她说捡到我的时候,我脖子上挂着块玉,刻着个“玄”字,
透着股说不出的怪劲儿,不像普通人家孩子的东西。她没敢卖,怕惹祸,就给我起了这名儿。
养母对我,不好不坏。她是个寡妇,靠给人缝补浆洗过活,手头紧巴。
我七岁被她从街边脏兮兮的角落里拎回来,洗刷干净,就成了这个家的一份子。说是家,
其实就一间半塌的泥坯房,冬天漏风,夏天漏雨。她有个亲儿子,比我大三岁,叫铁柱。
好吃懒做,游手好闲,是镇上出了名的混混。我的活儿很多。天不亮就得爬起来,
去镇子东头的水井打水,那轱辘又重又涩。回来生火,熬一锅照得见人影的稀粥。
伺候铁柱起床,他总嫌粥稀,馒头硬。养母默许他抢我的那份。十二岁,
养母托人把我塞进镇上的小制衣厂。手指头被缝纫机针扎透好几次,血珠子冒出来,
组长眼皮都不抬,扔过一块脏纱布:“包上,别弄脏了料子。”计件工资,我做得慢,
钱少得可怜。养母收走绝大部分,只给我留几毛,说给我攒着“将来”。哪有什么将来?
我的日子就是流水线上永远走不完的布头,是养母永远填不满的抱怨,
是铁柱恶意的推搡和嘲笑。只有一样东西是我的。一块用红绳子系着的,小小的玉牌。温润,
带着一丝凉意。正面刻着那个“玄”字,背面是些弯弯曲曲的纹路,看不懂。养母捡到我时,
它就在我脖子上挂着。这是我被抱走前,属于“以前”的唯一证明。我把它贴身藏着,
睡觉也不摘。摸着它,心里会有一点点奇怪的安定感,好像茫茫黑夜里,
远处有一豆极微弱的光。虽然不知道那光是什么。我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像浑浊的河水,
缓慢又沉重地流下去。直到那天。厂里发工资,比平时多了十块加班费。
我偷偷藏了五块在鞋垫底下。想着也许哪天,能给自己买件新汗衫,身上这件补丁摞补丁,
实在没法穿了。晚上回去,养母的脸拉得老长。铁柱坐在门槛上,脸色灰败。“钱呢?
”养母劈头就问,眼睛像钩子。我低着头,把大部分工资递过去。她数了数,
啪地摔在破桌子上:“就这么点?你糊弄鬼呢!厂里老王家的闺女跟你一个车间,
人家拿回来比你多五块!”我心里咯噔一下。“死丫头片子,学会藏钱了?
”铁柱腾地站起来,一把揪住我的头发,往墙上撞,“说!藏哪了!”头皮撕裂般地疼。
我咬紧牙关,不吭声。养母冲过来,开始搜我的身。那五块钱很快被翻了出来。“好啊!
反了你了!”养母气得浑身发抖,巴掌劈头盖脸落下来。铁柱更狠,一脚踹在我肚子上。
我蜷缩在地上,疼得眼前发黑,五脏六腑都移了位。混乱中,我感觉脖子上一轻。
那根系着玉牌的红绳,断了。我惊恐地抬头,看见铁柱正捏着那块小小的玉牌,
对着昏暗的灯泡看。“妈,你看这玩意儿!”他咧着嘴,“我就说她藏着好东西!这玉,
看着不赖啊!”养母也凑过去看,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贪婪的光。“还给我!
”我不知哪来的力气,扑过去想抢。铁柱一把将我推开,我重重摔在墙角。“你的?
你连人都是我妈捡回来的!这破玩意儿,指不定是哪个死人身上扒下来的!
”铁柱把玉牌揣进自己兜里,“正好,我手头紧,拿去换点钱花花。”“不行!
那是我……”我嘶喊着,眼泪终于汹涌而出。那是我唯一的念想,
是我和那个模糊不清的“以前”唯一的联系!“闭嘴!”养母厉声喝道,厌恶地看着我,
“嚎什么丧!一块破石头,能抵你吃的饭?铁柱拿去卖了,正好抵你偷藏的钱!”那天晚上,
我缩在冰冷的灶台边,抱着膝盖。肚子的剧痛一阵阵袭来,但比不上心里的空洞。
那块玉没了,那点微弱的光,彻底熄灭了。世界一片漆黑。第二天,铁柱果然不见了人影。
养母脸色也不好看,骂骂咧咧,说铁柱又去赌了,那玉牌被他贱卖了,
根本不够他还赌债的窟窿。我沉默地干活,像一具抽掉了灵魂的躯壳。几天后,
铁柱鼻青脸肿地跑回来,身后跟着两个凶神恶煞的男人。他们逼债,
把家里仅有的破柜子都砸了。养母哭天抢地,最后,她的目光像毒蛇一样缠上我。
“两位大哥,宽限几天!宽限几天!”她扑到其中一个男人脚边,
“我……我把这丫头抵给你们!她年轻,能干活!让她去你们那做工还债!
”男人上下打量我,像看牲口。我浑身冰冷,血液都冻住了。绝望像冰冷的潮水,
瞬间淹没了头顶。那个模糊的“以前”,那个被夺走的玉牌带来的微弱念想,
此刻显得那么可笑。我连现在都保不住自己了。就在男人的手快要抓住我胳膊的时候,
我猛地转身,用尽全身力气撞开挡路的铁柱,疯了一样冲出那间令人窒息的泥坯房。
身后是养母尖锐的咒骂和铁柱的怒吼,还有男人气急败坏的追赶声。我不敢回头,拼命地跑。
跑过熟悉的、坑洼的土路,跑过散发着鱼腥味的市场,跑过镇口那棵歪脖子老槐树。
风在耳边呼啸,肺像要炸开。一直跑,跑到镇子外废弃的砖窑。我钻进一个黑漆漆的窑洞里,
蜷缩在最深处,瑟瑟发抖。外面传来隐约的叫骂声和脚步声,渐渐远去。我紧紧抱住自己,
指甲深深掐进胳膊的肉里,才没让自己哭出声。黑暗包裹着我,
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浓重、更令人窒息。玉牌没了,最后的锚点也断了。
我像一片被狂风从枝头撕下的叶子,不知道会被卷向何方。这一次,真的什么都没了。
我在废弃的砖窑洞里躲了两天。靠捡别人扔掉的半块干馍和路边洼地里的脏水活命。第三天,
饿得实在受不住,趁着天蒙蒙亮,我溜回镇子边缘,想看看风声。远远地,
看见养母家门口停着一辆半新的小货车。两个男人正把家里仅有的破桌子破凳子往上搬。
铁柱垂头丧气地站在一边,养母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哭嚎。“天杀的赌鬼啊!家都败光了啊!
我拿什么活啊!”看来是债主来搬东西抵债了。那个家,彻底空了。我心里一片麻木,
没有恨,也没有幸灾乐祸。只觉得空。我悄悄绕开,不敢再回那个地方。镇上不能待了。
养母和铁柱走投无路,一定会像鬣狗一样再把我找出来卖掉。我得走,走得远远的。没有钱,
没有方向。我沿着公路,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走。走了一天一夜,脚底磨出了水泡,
又磨破了,钻心地疼。饿得头晕眼花,看见路边田里有没长成的青玉米,掰下来生啃,
又涩又硬,剌得嗓子疼。走到下一个县城时,我像个乞丐。蜷缩在汽车站肮脏的角落里,
看着人来人往。巨大的电子屏幕上,花花绿绿的广告闪得人眼花。
一个综艺节目的预告片反复播放,主持人声音高亢兴奋。我木然地看着。活下去,
怎么活下去?一个微胖的中年女人在我面前停下,皱着眉打量我。她穿着花哨,
脸上涂着厚厚的粉。“小丫头,一个人?”她开口,带着浓重的口音。我警惕地往后缩了缩。
“别怕,”她挤出一点笑,“我看你怪可怜的。想不想找份工?管吃管住。
”饥饿和疲惫压倒了警惕。我点了点头。她把我带到县城边上一个不起眼的小旅馆。
所谓的“工”,就是在后厨帮忙择菜洗碗,住在楼梯间改的杂物房里。老板娘很凶,
工钱少得可怜,但至少有口饭吃,有个不漏雨的屋顶。我像块沉默的石头,埋头干活。
洗堆积如山的油腻碗碟,擦洗永远有污垢的地板。手指泡得发白发皱。老板娘心情不好时,
会骂骂咧咧,把抹布甩到我脸上。我忍了。这里再差,也比那个泥坯房好。至少没人打我,
没人要卖掉我。我把自己缩得更小,更不起眼。偶尔,
旅馆大厅的破电视会放着那个叫《寻亲驿站》的综艺节目。主持人煽情的声音,
嘉宾痛哭流涕的脸,台下观众抹眼泪的画面。我匆匆瞥过,心里毫无波澜。寻亲?
那都是别人的故事。我的“亲”在哪里?或许早就没了。或许,就像铁柱说的,
我只是个没人要的累赘。日子像生了锈的齿轮,缓慢而滞涩地转动。
我几乎以为自己会永远困在这个油腻的小旅馆后厨里。直到那天下午。我正在后巷倒泔水桶,
一股酸臭味熏得人睁不开眼。巷子口停着一辆看起来很贵的黑色轿车,锃光瓦亮,
和周围破败的环境格格不入。车门打开,下来两个人。走在前面的女人,
穿着剪裁精致的米白色套装,头发挽得一丝不苟,气质温婉,
但眉眼间带着深深的疲惫和一种说不出的焦灼。
她身边跟着一个穿着黑色夹克、身形健硕的男人,像是保镖。女人一眼就看到了我,
目光停在我脸上,愣住了。她的眼神很奇怪,像是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
又带着巨大的震惊和……痛苦?我下意识地低下头,想赶紧倒完泔水离开。
这女人一看就不是普通人,我不想惹麻烦。“小姑娘……”她却叫住了我,声音有些发颤。
我僵在原地,没回头。她快步走过来,高跟鞋踩在脏污的地面上也毫不在意。她走到我面前,
离得很近。那股泔水的酸臭和她身上淡淡的、好闻的香水味混合在一起,
形成一种诡异的对比。她伸出手,似乎想碰我的脸,又猛地停住,手指微微发抖。
“你……”她盯着我的眼睛,嘴唇翕动,“你……你叫什么名字?”她的眼神太奇怪了,
像燃烧着两团火,里面有太多我看不懂的情绪。我害怕了,后退一步,
紧紧抓住泔水桶的边缘,指甲抠进油腻的木纹里。“康……康玄。”我小声说,声音干涩。
“康玄……”她喃喃地重复着,眼神更加复杂,像是在确认什么,
又像是巨大的失望瞬间淹没了她。“多大了?”“……十七。”我回答,心里警铃大作。
她想干什么?“十七……”她闭了闭眼,再睁开时,
那里面翻涌的激烈情绪似乎被强行压了下去,只剩下深不见底的悲伤。
“十七年前……我的女儿,丢了。”我的心猛地一跳。丢女儿?十七年前?她看着我,
努力想挤出一个温和的笑容,但比哭还难看:“你……长得很像我年轻的时候。尤其是眼睛。
”我愣住了。像她?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脸,粗糙,沾着油污。再看看她,皮肤细腻,
保养得宜。天壤之别。“对不起,吓到你了。”她深吸一口气,恢复了那种得体的仪态,
只是声音依旧不稳,“我叫沈静。我……我在找一个孩子。十七年了。
”她示意了一下旁边的保镖,保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塑封过的旧照片,递到我眼前。
照片有些发黄,上面是一个年轻的女人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女人眉眼温柔,
赫然就是眼前这位沈静年轻时的模样。她怀里的婴儿很小,闭着眼睛,脸蛋圆圆的。
“这是我女儿,刚满月的时候拍的。”沈静的声音带着哽咽,“她……她叫宁宁。康宁宁。
”康宁宁?这三个字像一道无声的惊雷,在我死寂的心湖里炸开!康?我也姓康!玄字玉牌!
十七年前!被抱走!无数碎片在我混乱的脑海里疯狂冲撞,嗡嗡作响。
“你……”沈静紧紧盯着我的脸,不放过我一丝一毫的表情变化,“你脖子……脖子上,
有没有……有没有一块玉?小小的,刻着‘玄’字?”轰——!我脑子里那根一直紧绷的弦,
彻底断了!玉牌!她怎么知道玉牌?!那块被铁柱抢走卖掉的玉牌!
我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得一干二净,身体控制不住地颤抖起来,
手里的泔水桶“哐当”一声掉在地上,刺鼻的馊水溅了我们一身。沈静被溅了一身污秽,
却毫不在意,她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瞬间惨白的脸和剧烈颤抖的身体,
那里面燃起了狂喜和不敢置信的火焰!“你知道!你知道那块玉对不对?!
”她猛地抓住我的胳膊,力气大得惊人,指甲几乎嵌进我的肉里,“它在哪?它在你身上吗?
宁宁!你是不是我的宁宁?”保镖见状立刻上前一步,警惕地环顾四周。
“我……我……”我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巨大的冲击让我眼前发黑,
耳朵里嗡嗡作响。我是康宁宁?那个襁褓里的婴儿?眼前这个穿着名牌、气质高贵的女人,
是我的……妈妈?怎么可能?那个模糊的“以前”,那点微弱的光,
在这一刻突然变成了一轮刺目的、灼热的太阳,几乎要将我烧成灰烬!恐惧,
巨大的、灭顶的恐惧瞬间攫住了我!比被养母打骂,比被铁柱抢走玉牌,
比被债主追着要卖掉时更甚!我猛地抽回手,用尽全身力气推开她,转身就往旅馆后门里冲!
“宁宁!你别跑!”沈静带着哭腔的呼喊在身后响起。我像受惊的兔子,
一头扎进油腻昏暗的后厨,反手死死关上门,背靠着冰冷的门板滑坐到地上,
心脏狂跳得像是要冲破胸膛。“发什么疯!泔水桶呢?”老板娘尖利的声音传来。
我充耳不闻,只是剧烈地喘息着,脑子里一片混乱。沈静的脸,那块玉牌,养母刻薄的脸,
铁柱凶狠的眼神……所有画面疯狂交织。外面传来拍门声和沈静焦急的呼唤:“开门!孩子,
开门!我们谈谈!求你了!”“滚开!什么人敢来老娘这里闹事!
”老板娘骂骂咧咧地要去开门。我像被针扎了一样弹起来,不能让她开门!
不能让老板娘看到!我扑过去死死抵住门。“老板娘!别开!是……是坏人!要抓我的!
”我语无伦次地喊。老板娘狐疑地看了我一眼,隔着门吼道:“外头的!听见没!
再不走我叫人了!”外面的拍门声停了。过了一会儿,
传来沈静极力压抑但仍带着颤抖的声音:“好,好,我们不走。我们就在外面等。孩子,
你别怕,我们不会伤害你……你好好想想,我等你。”脚步声似乎退开了一些。我瘫软在地,
冷汗浸透了后背的破衣服。老板娘叉着腰,狐疑地打量我:“死丫头,你惹什么祸了?
外头那女的,看着挺有钱,不像坏人啊?”我蜷缩在门后的阴影里,浑身发抖,
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坏人?什么是坏人?养母算坏人吗?铁柱算坏人吗?
那个要卖掉我的**打手算坏人吗?
沈静……她说她是我妈妈……她看起来那么难过……可我呢?我是谁?康玄?
还是……康宁宁?混乱像无数只手撕扯着我。那个被遗忘的、模糊的“家”,
突然以一种极具冲击力的方式出现在面前,我却只想逃。我习惯了黑暗,
那点微弱的光曾是我唯一的慰藉,可当真正的太阳出现时,我只觉得刺眼,
只想躲回熟悉的阴影里。我害怕。害怕这突如其来的“身份”。
害怕那个看起来高贵却陌生的“家”。害怕未知的一切。我更害怕……希望。
那一点点在心底死灰复燃的、对“亲”的渴望,让我恐惧得浑身发抖。如果希望再次破灭呢?
如果这又是一场空呢?我承受不起。接下来的两天,我像惊弓之鸟。
沈静和那个保镖真的没有离开。他们的车就停在巷子口。沈静每天都会在固定的时间过来,
轻轻敲几下后门,隔着门板,用那种极力放柔、却依旧带着哽咽的声音说话。
“宁宁……我知道你一时接受不了。没关系,妈妈等。
”“妈妈找了你好多年……去过很多地方……”“你小时候,
最喜欢听我给你唱歌……摇篮曲,还记得吗?”“那块玉,是你太爷爷留下的,
上面刻的是祈福的符文,保佑你平安长大的……背面是‘宁’字的古体……当年,
就挂在你脖子上……”她絮絮叨叨地说着,说她的寻找,说她的悔恨,说家里还有一个哥哥,
一个弟弟,都在等我回去。说爸爸因为我的丢失,身体一直不好。她的声音透过薄薄的门板,
像细细的针,扎进我麻木的心脏。疼,又带着一种诡异的酸胀。我蜷缩在冰冷的灶台边,
捂紧耳朵,却又忍不住去听。玉牌背面的纹路……是“宁”字?原来我一直贴身戴着的,
是自己的名字。康宁宁。这个名字像滚烫的烙铁,烫得我心口发疼。
旅馆老板娘看我的眼神越来越怪异,充满了八卦的探究和一丝不易察觉的算计。沈静的出现,
显然让她嗅到了不同寻常的味道。第三天傍晚,沈静的声音带着前所未有的疲惫和一丝绝望。
“宁宁……明天,妈妈要去录那个《寻亲驿站》了。妈妈……妈妈想最后试一次,
在全国观众面前……再找找你。如果你……如果你不想认我,也没关系。
妈妈只想知道你过得好不好……”她哽咽着,说不下去了。外面安静下来。脚步声渐渐远去。
**着门板,慢慢滑坐到地上。冰冷的地面透过薄薄的裤子传来寒意。黑暗中,我睁大眼睛。
《寻亲驿站》……那个在破电视里看到过的,哭哭啼啼的综艺节目。她要去上那个节目?
在全国人面前……找我?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
一股巨大的恐慌和……一种难以言喻的冲动,撕扯着我。不能去!不能让别人看到!
不能暴露在那么多人面前!那太可怕了!我只想躲起来,像阴沟里的老鼠一样活下去!
可是……她看起来那么难过。
了十七年……那块玉牌……我的玉牌……被铁柱抢走了……混乱的情绪像毒藤一样缠绕着我,
几乎窒息。这一夜,我睁着眼睛,直到天亮。第二天,
旅馆的破电视被老板娘搬到了前厅显眼的位置。她嗑着瓜子,招呼着几个住客:“快看快看!
昨天找那丫头的有钱太太,上电视了!《寻亲驿站》!我就说那丫头来路不正!”屏幕上,
演播厅灯火辉煌。沈**在嘉宾席上。她化了妆,但依然掩盖不住浓重的黑眼圈和憔悴。
她穿着素雅的米白色套装,和我第一次见到她时一样,只是此刻,
那挺直的脊背透着一股孤注一掷的悲怆。
主持人用夸张的语调介绍着:“今天来到我们《寻亲驿站》的沈静女士,
十七年来从未放弃寻找她被拐走的女儿康宁宁!十七年的煎熬,十七年的泪水,今天,
她能否在这里,找到一丝希望的曙光?”镜头推近沈静的特写。她的眼睛红肿,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却倔强地没有落下。她紧紧握着一个旧得发黄的小拨浪鼓。
“宁宁……我的女儿……”她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出来,沙哑得厉害,带着极力压抑的泣音,
“十七年了,妈妈每一天都在想你……想我的宁宁,是不是冷了,饿了,
有没有被人欺负……”她拿出那张塑封的婴儿照片,
展示给镜头:“这是你满月的时候……你那么小,那么软……你脖子上,
挂着一块小小的玉牌,上面刻着‘玄’字,
背面是‘宁’字的古体……那是太爷爷留给你保平安的……”镜头给了照片特写。
那婴儿脖子上,确实系着一根红绳,下面隐约可见一块小小的玉饰。
“妈妈对不起你……是妈妈没有看好你……”沈静的眼泪终于决堤,她捂着脸,
肩膀剧烈地颤抖起来,那压抑了十七年的痛苦和自责,在这一刻彻底爆发,
哭声凄厉得让人心碎。台下观众席一片唏嘘,许多人跟着抹眼泪。主持人也被感染,
声音低沉下来:“沈女士,您有什么话,想对可能在电视机前看着您的女儿说吗?
”沈静抬起头,泪眼婆娑,却努力看向镜头,仿佛要穿透屏幕,
看到那个不知身在何处的孩子。“宁宁……妈妈不知道你现在叫什么,
长成了什么样子……妈妈只求你,
如果你能看到……如果你还记得一点点……给妈妈一个机会,让妈妈看看你,好不好?
妈妈什么都不求,只想看看你……知道你平安……让妈妈……弥补一点点……”她泣不成声,
对着镜头,深深地、卑微地弯下了腰。那画面,像一把烧红的刀子,狠狠捅进了我的心脏!
痛!痛得我无法呼吸!我猛地从旅馆前厅的角落站起来,撞翻了旁边的凳子。
老板娘和住客们都吓了一跳,诧异地看着我。屏幕上,沈静弯下的腰,
那卑微到尘埃里的姿态,和她身上那套价值不菲的米白色套装,形成了无比刺眼的对比。
那是我的妈妈?那个在破旧旅馆后巷被我溅了一身泔水的女人?那个十七年来,
从未放弃寻找我的女人?“玉牌……背面是‘宁’字……”她哽咽的声音在我耳边回响。
铁柱抢走它时猥琐的笑脸,养母刻薄的咒骂,
债主砸东西的巨响……和眼前屏幕上沈静绝望痛哭的画面,疯狂地交织、碰撞!
一股巨大的、无法控制的冲动,像火山一样在我胸**发!“啊——!
”我发出一声嘶哑的、不像人声的尖叫,在所有人惊愕的目光中,转身冲出了旅馆!跑!
我要去那里!我要去那个演播厅!我要告诉她!告诉她玉牌的事!告诉她……我在这里!
这个念头疯狂地燃烧着我,驱散了所有的恐惧和犹豫。十七年的黑暗,十七年的压抑,
十七年“康玄”这个名字背负的沉重和屈辱,在这一刻被一股更原始、更强烈的洪流冲垮!
我要去找她!找我的妈妈!康宁宁的妈妈!我不知道演播厅在哪里。冲出旅馆,
外面是陌生的县城街道。我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撞,看到人就抓住问:“《寻亲驿站》!
电视台!在哪里?”路人被我疯狂的样子吓到,纷纷躲避。
有人嫌恶地甩开我的手:“神经病啊!”我不管!继续跑,继续问。汗水糊住了眼睛,
嗓子眼**辣地疼。脚上破旧的鞋子磨得脚底血肉模糊,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终于,
一个好心的环卫工大爷指了个方向:“闺女,电视台?在城东新区呢!远着呢!
坐公交车得坐好几站!”城东新区!公交车?我看着路上飞驰而过的车辆,
再看看自己空空如也的口袋。绝望再次袭来。就在这时,一辆出租车在我旁边停下,
司机探出头:“姑娘,去哪?”“电视台!《寻亲驿站》演播厅!快!
”我像抓住了救命稻草,语无伦次。司机打量了我一眼,大概是看我一身油污、神情癫狂,
有些犹豫。“求求你!我妈妈在上面!我要去找我妈妈!”我几乎是哭喊着哀求,
眼泪混着汗水流下来。司机愣了一下,眼神复杂地看了我几秒,猛地一挥手:“上车!
”车子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出去。我紧紧抓住前排座椅的靠背,指甲掐进劣质的皮革里。
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擂动,几乎要跳出来。窗外的景物飞速倒退,模糊成一片光影。快一点!
再快一点!演播厅里。沈静的倾诉已经接近尾声,巨大的悲伤和绝望笼罩着全场。
主持人正在做最后的总结,试图引导一个“充满希望”的结尾。“……沈女士的故事,
让我们看到了母爱的伟大和坚韧。虽然今天,奇迹没有在舞台上发生,但我们相信,
电视机前千千万万的观众,一定会……”后台的导播间却突然一阵骚动!
一个工作人员指着监控屏幕,失声叫道:“有人闯进来了!”只见监控画面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