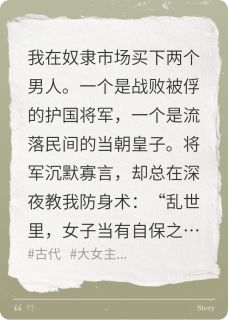
1乱世双雄我在奴隶市场买下两个男人。一个是战败被俘的护国将军,
一个是流落民间的当朝皇子。将军沉默寡言,却总在深夜教我防身术:“乱世里,
女子当有自保之力。”皇子风流倜傥,常赠我珠宝:“待我归位,许你贵妃之位。
”我笑着收下礼物,却总在月下与将军对酌。那夜皇子率兵围住院落:“要么交出虎符,
要么看着他死。”将军忽然将我揽入怀中,吹响骨哨。城外铁蹄震天,玄甲军如黑潮涌来。
他吻着我耳垂低笑:“王妃,该验收你的军队了。
”---2奴隶市场的邂逅腐草、汗酸和铁锈混杂的气息,浓稠得几乎凝成实体,
沉甸甸地压在玉京城南这方巨大的奴隶市场上空。阳光灼热刺眼,却穿不透棚顶厚重的油毡,
只在缝隙里漏下几道斜斜的光柱,光柱里尘埃狂舞,像无数躁动不安的魂灵。人声鼎沸,
粗野的吆喝、绝望的哭泣、皮鞭破空的尖啸,还有买家挑剔的议论,
汇成一片令人窒息的嘈杂泥沼。林晚舟的皂色软靴踩过泥泞的地面,步履平稳,
对周遭的污秽与喧嚣视若无睹。她一身素净的湖蓝衣裙,
在这粗犷混乱的场子里显得格格不入,像一泓误入浊流的清泉。管事阿福佝偻着腰,
脸上堆满了讨好的笑容,亦步亦趋地跟在她侧后方半步的位置,
如同一条熟谙主人心意的老狗。“林**您瞧,新到的好货色!”阿福的声音在喧嚣中拔高,
带着一种特有的市侩热情,他伸手指向一排排散发着霉味和汗臭的木笼,
“都是些健壮能干的,耕田、拉货、看家护院,都是一把好手!
”林晚舟的目光平静地扫过笼中那些或麻木、或惊恐、或带着讨好谄媚的面孔,并未停留。
她今日来此,并非为了寻常苦力。她需要一个契机,一个能撬动某些沉重棋局的小小支点。
脚步在靠近角落一个稍显孤立的铁笼前,停了下来。
一股更浓烈的、尚未散尽的血腥气和铁锈味扑面而来,比别处更刺鼻。笼子里,
两个男人背靠着冰冷的铁条,姿态迥异,却同样引人注目。左边的那个,身形异常高大魁梧,
即便蜷坐在肮脏的草堆里,依旧像一块沉默的磐石。污秽的囚服几乎看不出原色,
紧贴着他虬结贲张的肌肉轮廓。脸上沾满血污和泥垢,几乎辨不清五官,唯有一双眼睛,
幽深锐利,如同藏在枯枝败叶下的寒潭。他的背脊挺得笔直,那不是刻意为之的倔强,
而是长年累月浸入骨髓的习惯,一种千锤百炼后的本能。即使深陷囹圄,
骨子里透出的某种东西,依旧未被彻底碾碎。右边的青年则不同。他斜倚着笼壁,
姿态甚至带着一丝慵懒的颓废。一张脸虽然同样污迹斑斑,狼狈不堪,
但五官的底子异常俊秀,轮廓清晰如刀刻。只是那双漂亮的桃花眼,
此刻却盛满了毫不掩饰的倨傲与戾气,像一头落入陷阱却仍不肯低头的猛兽,
目光扫过笼外的人群,带着冰冷的审视和毫不遮掩的轻蔑。两道目光,
几乎在林晚舟停步的瞬间,便如实质般投射过来。一道沉凝如渊,
带着穿透性的审视;一道灼热如火,充满了不甘的敌意。阿福立刻凑上前,压低声音,
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幸灾乐祸:“**您可别被这俩的皮相唬住!左边那个,
据说是北边战场上被俘的,打废了好几个看守才抓住,凶得很!右边那个,啧啧,
更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自打送进来,就没给过谁好脸,自称是什么龙子凤孙,呸!
就这德性?”他啐了一口,满脸鄙夷,“是两个扎手的刺头,可不好**!您要买人,
还是看看那边几个……”林晚舟仿佛没听见阿福的劝阻。
她的视线在那两道迥异的目光之间缓缓逡巡,唇角极细微地向上弯了一下,那弧度转瞬即逝,
快得让人以为是错觉。她伸出纤细的手指,指尖干净,指甲修剪得圆润,指向那个铁笼。
“就要这两个。”声音不高,却清晰地穿透了周围的喧闹,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平静。
阿福脸上的谄笑僵住了,绿豆大的小眼睛瞪得溜圆,难以置信地看着林晚舟:“小…**?
您是说……这两个?”他以为自己听错了,买这种一看就麻烦缠身的奴隶,
不是给自己找不痛快吗?“嗯。”林晚舟淡淡应了一声,目光依旧落在那两个男人身上。
魁梧的那个眼神似乎微微动了一下,而俊秀的青年则挑衅似的抬了抬下巴,
唇边勾起一抹冰冷的、充满嘲弄的弧度。阿福咽了口唾沫,脸上的肥肉抖了抖,
终究不敢再多言。这位林**年纪虽轻,手段和背景却深不可测,她决定的事,
从来无人能改。“好…好嘞!您慧眼!小的这就给您办契!”他点头哈腰,
忙不迭地吆喝看守过来开锁。沉重的铁锁链哗啦作响,如同开启了某种未知命运的序幕。
---3沉默的将军马车碾过青石板路,发出单调而规律的辘辘声,
车厢内却弥漫着一种近乎凝固的沉默。方才奴隶市场的喧嚣被隔绝在厚厚的车帘之外,
只余下车轮滚动和马蹄踏石的声响。污秽的囚服被换下,两人穿着林府下人准备的粗布衣衫,
坐在林晚舟对面,隔着一张小小的紫檀木几。魁梧的男人坐姿依旧挺直,双手搁在膝上,
指节粗大,布满老茧和伤痕。他微垂着眼睑,
目光落在自己那双刚刚洗净、却依旧残留着污痕和冻疮印记的手上,
沉默得像一块历经风霜的山岩。浓密眼睫遮住了他眼底的情绪,只有那笔直的脊梁,
无声地诉说着某种刻入骨髓的坚韧。俊秀的青年则显得放松许多,甚至有些刻意为之的慵懒。
他斜靠在柔软的车厢壁上,一条长腿随意地曲起,目光毫不避讳地打量着对面的林晚舟,
以及这辆装饰雅致、处处透着昂贵气息的马车。那眼神带着审视,带着估量,
也带着一丝玩味和不易察觉的探究。仿佛他不是被买来的奴隶,而是误入此间的客人。
“名字?”林晚舟的声音打破了沉默,清冷如水,听不出喜怒。魁梧的男人抬起眼,
目光沉稳地迎上她,声音低沉沙哑,如同粗粝的砂石摩擦:“沈砚。”两个字,简洁有力。
青年嗤笑一声,带着明显的轻慢,桃花眼斜睨着林晚舟,唇角的弧度带着讥诮:“怎么,
买主盘问家底了?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萧景恒。”他刻意加重了“萧”字的发音,
目光灼灼地盯着林晚舟的脸,似乎在期待从这张过分平静的脸上捕捉到一丝惊诧或惶恐。
然而林晚舟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仿佛听到的只是“张三李四”这样寻常的名字。
她的目光掠过萧景恒,落在沈砚身上,语气依旧平淡:“沈砚?好名字。砚台沉实,可研墨,
亦可镇纸。”沈砚的浓眉几不可察地动了一下,幽深的眼底似乎有什么东西飞快地掠过,
快得难以捕捉。他重新垂下眼帘,只沉声道:“**谬赞。”依旧是那副磐石般的沉默姿态。
萧景恒脸上的倨傲微微一滞,显然没料到林晚舟会是这般反应。他盯着她那张波澜不惊的脸,
眉头微蹙,一丝被忽视的不快在眼底悄然滋生。车厢内再次陷入沉默,
只剩下车轮单调的滚动声,以及三人之间无声涌动的暗流。
马车驶入城东一处闹中取静的深巷,在一座门楣高阔却并不显张扬的府邸前停下。
朱漆大门无声打开,门楣上悬着的匾额写着两个古朴苍劲的大字——“林府”。
管家林伯早已带着几个伶俐的小厮候在门口。看到林晚舟下车,他微微躬身,
目光飞快地扫过她身后跟着的两个高大身影,
尤其是看到萧景恒脸上那尚未完全收敛的桀骜时,老成持重的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
“**,您回来了。”林伯的声音恭敬而沉稳。“嗯,”林晚舟应了一声,踏上台阶,
“林伯,这两位是新入府的人。沈砚,萧景恒。”她顿了顿,语气如常,
“安排在西跨院相邻的厢房,一应份例,照府中护卫的标准。”“是,老奴明白。
”林伯躬身领命,目光转向沈砚和萧景恒时,已恢复了惯常的平静,“二位请随我来。
”萧景恒闻言,眉头猛地一挑,桃花眼里瞬间燃起被冒犯的怒火:“护卫?”他冷笑一声,
声音拔高,带着毫不掩饰的讥讽,“林大**,你可知你在跟谁说话?让我与这等人同列?
”他下巴微抬,指向一旁的沈砚,眼神轻蔑至极。沈砚只是沉默地站着,
对萧景恒的挑衅置若罔闻,目光平静地落在庭院中一株苍劲的老梅树上,
仿佛那虬结的枝干比眼前的一切纷争都更有吸引力。林晚舟的脚步在门槛前顿住,并未回头。
晚风拂过,吹动她耳畔一缕碎发,声音清晰地传来,不高,却带着一种冰锥般的穿透力,
瞬间冻结了萧景恒脸上的怒意:“阶下之囚,何谈尊卑?林府,自有林府的规矩。”她抬步,
身影消失在影壁之后,只留下那句冰冷的话语在暮色渐合的庭院中回荡。萧景恒僵在原地,
俊脸一阵青一阵白,拳头在身侧紧握,指节捏得发白。他死死盯着林晚舟消失的方向,
眼底的怒火几乎要喷薄而出,最终却只是化作一声压抑在喉间的冷哼,猛地甩袖,
跟着引路的小厮,大步朝着西跨院的方向走去,每一步都踏得极重,
仿佛要将满腔的屈辱踩进青石板里。沈砚沉默地跟上,脚步沉稳。在路过那株老梅树时,
他的目光似乎在那遒劲的枝干上停留了一瞬,随即也消失在西跨院的月洞门内。
---4暗流涌动西跨院的厢房简洁干净,一应用具虽不奢华,却也齐全。
对于刚从污秽囚笼中出来的两人而言,已是天上地下。然而平静并未持续多久。
沈砚的沉默寡言和萧景恒毫不收敛的倨傲,如同投入林府这潭静水的两颗石子,
不可避免地激起了涟漪。府中的管事、护卫,乃至洒扫的下人,
目光总是不自觉地被这两个气质迥异却又同样引人注目的男人所吸引。
沈砚的存在像一块沉重的铁。他不爱说话,除了林晚舟偶尔的吩咐,几乎不与任何人交流。
分配给他的活计,无论是清扫庭院、搬运重物,还是修缮一些粗笨的家什,
他都做得一丝不苟,动作精准而高效,带着一种近乎严苛的军人作风。那双布满厚茧的大手,
仿佛天生就该握着更沉重的东西,而非扫帚或斧凿。他常常独自一人坐在院中角落的石凳上,
目光沉静地望向北方遥远的天际,像是在凝望一片早已失去的土地。那沉默的背影,
无形中散发着一种难以接近的孤绝气息。萧景恒则截然不同。他像一团不安分的火焰。
林晚舟并未限制他的行动,只要不出府门,他可以在府内大部分区域行走。于是,
花园的亭台楼阁、藏书阁的幽静角落,乃至靠近林晚舟起居院落的外围,
常常能看到他慵懒闲逛的身影。他挑剔饮食,对仆役呼来喝去,
言语间总带着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府中下人们私下议论纷纷,
对这个“身份不明却架子奇大”的奴隶又惧又厌。冲突的种子悄然埋下。一日午后,
沈砚正在后院劈柴。沉重的斧头在他手中仿佛轻若无物,每一次落下都带着沉稳的力量,
木柴应声而开,裂口光滑整齐。汗珠顺着他棱角分明的下颌滑落,滴在古铜色的肌肤上。
萧景恒恰好路过,不知是心情不佳还是存心挑衅,他瞥了一眼地上堆积的柴薪,
嗤笑道:“堂堂……呵,竟沦落到做这等粗鄙活计?林大**真是物尽其用啊。
”他故意拖长了调子,眼神里的轻蔑毫不掩饰。沈砚劈柴的动作没有丝毫停顿,仿佛没听见。
斧头再次落下,又是一块圆木应声裂成两半。这无声的漠视彻底激怒了萧景恒。
他猛地一脚踢飞了脚边几块劈好的柴火,木块四散滚开。“跟你说话呢!聋了还是哑了?
”他上前一步,逼近沈砚,声音带着压抑的怒火。沈砚终于停下了动作。他缓缓直起身,
高大的身躯投下一片阴影,将萧景恒笼罩其中。他转过头,幽深的目光落在萧景恒脸上,
那目光并不凶狠,却沉凝如万仞山岳,带着一种经历过尸山血海的、令人心悸的平静。
“让开。”沈砚的声音低沉沙哑,只有两个字。萧景恒被他看得心头莫名一凛,
但骄横之气随即占了上风。他梗着脖子,不但不让,反而又逼近半步,
几乎要贴上沈砚的胸膛,眼中戾气翻涌:“怎么?一个败军之将,
也敢对本……也敢对我呼来喝去?”话音未落,沈砚动了。快得只留下一道残影!
萧景恒甚至没看清他的动作,只觉手腕猛地传来一阵剧痛,仿佛被铁钳狠狠夹住,
紧接着一股无法抗拒的大力传来,他整个人天旋地转,后背重重砸在冰冷的泥地上,
震得他五脏六腑都仿佛移了位,眼前一阵发黑。沈砚甚至没有多看他一眼,
弯腰捡起地上的斧头,仿佛刚才只是拂开了一只恼人的飞虫。他重新站定,举起斧头,
对着新的圆木,手臂肌肉贲张,斧刃划破空气,带着沉闷的风声,精准落下。“咔嚓!
”清脆的裂木声响起,掩盖了萧景恒摔在地上那声痛苦的闷哼。萧景恒狼狈地躺在地上,
浑身骨头像是散了架,手腕更是疼得钻心。他死死瞪着沈砚沉默劈柴的背影,
那笔直的脊梁如同无声的嘲讽。羞愤、不甘、还有一丝难以言喻的惊悸,
如同毒蛇般啃噬着他的心脏。他挣扎着爬起来,拂去身上的尘土,眼神阴鸷得可怕,
却终究没有再上前。他捂着剧痛的手腕,踉跄着离开了后院,只留下一个充满怨毒的背影。
消息很快传到了林晚舟耳中。彼时她正在书房对账,青葱般的手指拨弄着乌木算盘珠,
发出清脆的声响。林伯垂手侍立在一旁,低声禀报了后院的冲突,语气带着担忧:“**,
那萧景恒怕是不会善罢甘休。沈砚身手虽好,
可那萧景恒的性子……”林晚舟拨动算珠的手指并未停顿,甚至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声音平静无波:“知道了。”林伯等了片刻,见**再无吩咐,只得躬身退下。
书房里只剩下算盘珠清脆的噼啪声,规律得如同心跳。
---5月下对酌日子在一种微妙的张力中滑过。自后院冲突后,萧景恒收敛了不少,
至少在沈砚面前不再轻易挑衅,但那眼神深处的怨毒和算计却愈发深沉。
他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林晚舟可能经过的地方,姿态也从最初的倨傲,
渐渐带上了一种刻意为之的、风流倜傥的意味。这日黄昏,林晚舟处理完铺子里的琐事,
带着一身淡淡的墨香和市井烟火气回到府中,穿过回廊时,正遇上倚在廊柱旁赏花的萧景恒。
暮色四合,廊下挂着的灯笼刚被点亮,柔和的光晕落在他俊美无俦的侧脸上,
倒真有几分浊世佳公子的风采。“林**。”萧景恒转过身,
脸上绽开一个恰到好处的、足以令寻常女子心旌摇曳的笑容。
他变戏法似的从袖中取出一个锦缎小盒,盒盖打开,里面静静躺着一支赤金点翠的凤头钗,
钗身线条流畅,凤眼用细小的红宝石镶嵌,在灯火下流光溢彩,精巧华贵,价值不菲。
“今日得见**,方觉这钗与**的清雅风华正是绝配。”萧景恒的声音低沉悦耳,
带着蛊惑人心的磁性,他将锦盒递到林晚舟面前,“一点心意,不成敬意。
他日……”他微微倾身,靠近些许,压低了声音,带着某种引人遐想的暗示,
“待我重登……必以贵妃之位相酬,共享这万里江山。
”晚风带着庭院里初绽的玉兰幽香拂过。林晚舟的目光落在那支华贵的金钗上,
神色平静无波,既无受宠若惊的欣喜,也无被冒犯的怒意。她甚至微微弯了弯唇角,
露出一抹极淡、看不出情绪的笑意。“萧公子有心了。”她伸出白皙的手指,
动作自然地接过了锦盒,指尖并未触碰到萧景恒的手,“这钗,确也精致。
”语气平淡得像在评价一件寻常的货物。萧景恒脸上的笑容微微一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