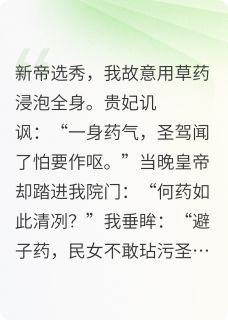
新帝选秀,我故意用草药浸泡全身。贵妃讥讽:“一身药气,圣驾闻了怕要作呕。
”当晚皇帝却踏进我院门:“何药如此清冽?”我垂眸:“避子药,民女不敢玷污圣体。
”他大笑册封,宠冠六宫。贵妃在御酒下毒那夜,皇帝把酒杯推到她面前。“爱妃替朕尝尝。
”他揽住发抖的我低语:“孤绝之地,才最安全。”……1四下里静得惊人,
唯有七月骄阳烧灼着空气,发出令人窒息的嗡鸣。苏晚垂着眼,汗珠从额角滑落,
沿着清瘦的侧脸滚下,滴在捣药的石臼边缘。“啪”地一声轻响,
瞬间被那无孔不入的燥热蒸腾得无影无踪。她指尖碾过石臼里晒得干脆的艾草,
碾过冰片、薄荷、金银花……每一味草药的苦涩清香都固执地渗透出来,
丝丝缕缕缠绕在她身上。小院偏僻,只有几株半死不活的绿植耷拉着叶片。
几缕刻意拔高的嬉笑随风飘过院墙,像针一样扎进来。“瞧咱们这位苏才人,倒是个勤快的,
成天捣鼓她那些神仙草呢。”“嗤,勤快?躲懒罢了!今日圣驾可是要从西苑那边过来,
隔着两道宫墙也能望见个影儿,谁不是卯足了劲儿梳洗熏香?偏她弄这一身药罐子味儿,
也不怕冲撞了贵人!”“贵人?怕是连只野猫都熏跑喽!贵妃娘娘不是说过么,一身药气,
圣上闻了怕是要作呕呢……”尖刻的声音渐渐远去。苏晚的动作丝毫未停,
木杵在石臼里一下下撞出沉闷笃实的声响。她抬起袖子,
深深嗅了一口袖口浸染的、浓得化不开的药草气息。
那是她这些时日刻意用汤药反复浸泡、熏蒸的结果。这味道,是她的盔甲,
是她为自己在这座巨大的黄金囚笼里,划出的孤岛界线。“孤绝之地,才最安全。
”她低声念着父亲临终前的告诫。苏家世代太医,卷入宫闱倾轧,最终落了个满门凋零。
院外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细碎的脚步声,紧接着是宫人们刻意压低的、带着惶恐的提醒。
“快快,都低下头!圣驾……圣驾的车辇往这边来了!”苏晚的心猛地一沉,
捣药的手顿在半空。怎么可能?这条窄仄、偏僻、连宫道都算不上的小径,
怎么会……念头未落,喧哗声已由远及近,如同陡然掀起的巨浪。
仪仗鲜明的队伍豁然停在了她这间小院的门口。刺目的明黄色帘幔一掀,
身形颀长的年轻皇帝萧彻一步踏出。深蹙的眉宇间带着挥之不去的躁意,
似是被后宫那些浓烈到令人窒息的脂粉香气缠得心烦意乱。
他身旁那位艳光四射、满头珠翠的贵妃秦氏,正用一方精美的蜀锦丝帕掩着口鼻。
眼波流转间,看向院门的目光充满了毫不掩饰的、幸灾乐祸的轻蔑。萧彻的目光,
却越过满院的寒酸和杂乱,越过地上摊晒的药材,牢牢钉在僵立在石臼旁那个单薄的身影上。
她穿着半旧的浅青宫装,发髻用一根简单的木簪挽着,脂粉不施,
却在那片被阳光和药草气息充斥的天地里,奇异地干净得扎眼。他大步走了进去,
步履带起的风掠过几株晒在矮桌上的草药。一股清冽、微苦、却又极其醒脑的气息,
瞬间冲散了他胸中的浊闷。“何药?”萧彻停在苏晚面前几步之遥,声音低沉,听不出情绪,
目光却锐利如鹰隼,将她从头到脚刮了一遍。那目光并不含狎昵,只有纯粹而冰冷的审视。
院门口的秦贵妃款款上前几步,丝帕依旧掩着口鼻,娇声笑道:“陛下,
这味儿冲得臣妾直晕呢!定是些粗鄙的野草,腌臜地方腌臜人,
莫要污了您的……”她的话被皇帝一个抬手的手势截断。萧彻的目光依旧锁着苏晚,
重复道:“朕问你,是何药?”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空气凝固得如同烧窑里冷却的琉璃。
苏晚能清晰地听到自己心脏在胸腔里撞出的擂鼓声。她深吸一口气,
那浓郁的、保护了她多日的药味灌入肺腑,带来一阵短暂而奇异的镇定。她缓缓屈膝,
双膝跪在滚烫的青石板上,额头轻轻触地,声音如流水击石,
清晰却带着一种决绝的冰冷:“回陛下,是避子之药,民女……体弱多病,性情孤僻,
宫规森严,不敢以秽体污浊之气,玷污圣体。”死寂。
连聒噪的蝉鸣似乎都在这一刻噤若寒蝉。秦贵妃手中的丝帕无声滑落,她惊愕地张着嘴,
一双美目瞪得溜圆,难以置信地看着地上那个卑微俯首的身影。
她竟敢……竟敢如此直白地、大逆不道地说出“避子”二字?!还说什么“玷污圣体”?
这简直是自寻死路!狂喜和一丝隐秘的恐惧同时在秦贵妃眼中闪过。周围侍立的宫人、太监,
更是瞬间面如土色,一个个死死地低下头,恨不得把脖子缩进腔子里去,连呼吸都停滞了。
时间被拉得无限漫长,每一粒尘埃在灼热的光线下都清晰可见。苏晚伏在地上,
只能看到皇帝明黄色龙袍的下摆,那象征着至高无上权力的颜色,
此刻仿佛一座沉重的大山压在她头顶。她等待着雷霆之怒,等待着死亡的裁决。
一声低沉的、毫无预兆的笑声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静。
那笑声起初只是喉咙里滚动的几声闷响,转瞬便扩散开来,带着一种近乎荒谬的畅快,
甚至称得上是愉悦。“哈哈哈……好!好一个‘不敢玷污圣体’!”萧彻朗声大笑,
笑声在寂静的小院里回荡,震得人耳膜嗡嗡作响。他猛地俯身,一把攥住了苏晚纤细的手腕,
力道极大,不容抗拒地将她整个人从地上提了起来。苏晚被他拽得一个趔趄,
几乎撞进他怀里。仓促间抬头,正对上皇帝那双深不见底的眸子。那里面没有她预想的暴怒,
反而像幽潭投入了石子,漾开奇异的光,混杂着兴味、审视,还有一丝……她读不懂的了然。
“苏家之女,果然……不同凡响。”他盯着她苍白的脸,唇角的笑意未散,声音却压低了,
只容她一人听清。“这满宫姹紫嫣红,独你这一味清苦醒神。”他松开她的手腕,
仿佛刚才那带着力道的钳制只是幻觉。转身,明黄的袍袖在阳光下划过一道耀眼的弧线,
声音恢复了一贯的威严。清晰地传遍整个小院,也清晰地穿透宫墙,
落入外面每一个竖着耳朵的人心里:“传旨,晋苏氏为贵人,赐居……清晏阁。
”旨意像一颗投入深水的巨石,激起的波澜瞬间席卷了整个后宫。清晏阁,位置绝不算顶好,
但胜在独立清幽,远离东西六宫中心喧嚣的漩涡。这深意已足够让人嚼舌。
更令人惊掉眼珠的,是皇帝当夜便踏入了清晏阁那道新漆未干的朱门。
苏晚成了宫中最不可思议的存在。她依旧不施脂粉,依旧满身药香,依旧深居简出。
皇帝却仿佛着了魔,仿佛是厌烦了那些浓烈到令人窒息的脂粉堆砌出的美人,
独独贪恋她这一味“清苦”。清晏阁里,并无想象中的旖旎风光。更多时候,
皇帝只是斜倚在窗边的软榻上,翻着书卷,或是批阅奏章。苏晚则守在小炉旁,
安静地煮她的药茶。药气氤氲,无声地流淌在两人之间,像一道无形的屏障,
又像一种旁人难以企及的默契。“陛下若嫌苦,可以加些蜜。
”她曾将一盏刚煎好的双花饮递过去,语气平静无波。萧彻接过来,
看也未看那盏清亮的褐色汤水,目光落在她低垂的眼睫上。“不必。”他仰头,一饮而尽,
眉头都未皱一下,“甚好。”那一刻,苏晚才惊觉,这男人眼中的探究从未散去,
只是藏得更深。盛宠之下,是无穷的暗箭。苏晚成了众矢之的,尤以秦贵妃为最。
她眼睁睁看着自己经营多年的荣宠被一个“药罐子”截断,嫉妒和怨毒几乎要将她烧成灰烬。
流言如毒藤般疯狂滋长,苏贵人乃妖魅所化,用药香蛊惑圣心;苏家罪人之女,
心怀叵测隐藏宫中;更有甚者,
直指她以药行巫蛊之事……一道道弹劾苏家的奏章也悄然递到了御前。风刀霜剑步步紧逼。
苏晚知道,秦贵妃的耐心已到了极限,下一场风暴,必是雷霆万钧。宫宴那夜终于到来。
为庆贺北疆大捷,宫内张灯结彩,笙歌鼎沸。
苏晚穿着贵妃“特意”为她备下的那件过于华丽、几乎不合身的宫装。
坐在灯火辉煌的大殿中,像一个被强行塞进水晶瓶里的异类,浑身不自在。
脂粉香气、酒菜气息和各种熏香混合成一股令人头晕目眩的浊流,
几乎要将她身上那点微弱的药气彻底淹没。萧彻高踞主位,面色如常,接受着臣下的敬贺。
秦贵妃端坐在他身侧,盛装之下,容光绝世,巧笑倩兮,眼神却时不时如冰冷的蛇信,
舔过下首的苏晚。酒过三巡,气氛正酣。乐师奏起新曲,舞姬彩袖翩跹。秦贵妃盈盈起身,
捧起一只精致的玉壶与配套的玉杯,袅袅娜娜地行至御座前。“陛下。”她声音婉转如莺啼,
带着恰到好处的妩媚。“此乃臣妾娘家特地从南地寻来的‘玉露春’,
窖藏足有二十年;清冽甘醇,最是解乏提神,臣妾……斗胆,恳请陛下品鉴。”她眼波流转,
有意无意地扫过苏晚的方向,指尖在玉壶壁上轻轻一点。
侍立在侧的内侍总管王德全立刻会意,上前一步欲要接过银针试毒。“不必试了。
”萧彻却摆了摆手,目光落在秦贵妃捧着的玉壶上,
唇角勾起一抹极淡、却让人心底发寒的笑意。“既是爱妃一片心意,朕岂有不信之理?
”秦贵妃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一下,一丝慌乱被强行压下,
取而代之的是更深的娇嗔:“陛下厚爱,臣妾惶恐……”萧彻却不再看她,
目光越过秦贵妃的肩头,精准地落在那道几乎要融进角落阴影里的身影上。“苏贵人,
”他的声音不高,却在骤然寂静下来的大殿里清晰得如同玉磬敲响。“你素来喜静,
今日也辛苦了这杯酒,赏你了。”空气骤然凝滞。所有的丝竹管弦、觥筹交错之声,
仿佛瞬间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扼住,戛然而止。无数道目光“唰”地一下,
从四面八方投射过来,聚焦在苏晚身上。
震惊、疑惑、幸灾乐祸、同情……种种情绪交织成一张巨大的网,将她死死笼罩。
苏晚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猛地窜起,瞬间冻结了四肢百骸。她抬起头,
越过秦贵妃瞬间褪去血色的脸,看向御座上的帝王。那双深邃的眼眸里,不见怒火,
不见酒意,只有一片冰封的、洞察一切的平静。秦贵妃捧壶的手几不可察地抖了一下,
指节因用力而泛白。她僵硬地转过身,脸上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尖利。“陛……陛下说笑了苏妹妹身子娇弱,
哪……哪能饮得这等烈酒?臣妾……”“怎么?”萧彻的身体微微前倾,
手肘随意地撑在御座的扶手上,指尖轻轻敲击着冰冷的鎏金龙首。目光却锐利如刀锋,
直直刺向秦贵妃,“朕赐的酒,苏贵人喝得,你……便替不得?”“替”字出口,
如惊雷炸响。死寂的大殿里,连呼吸声都被刻意压到了最低。秦贵妃脸上的血色彻底褪尽,
涂着鲜红蔻丹的指甲深深地掐进了掌心的嫩肉,留下几道刺目的月牙痕。她死死咬住下唇,
才没有让那声惊惧的抽噎溢出喉咙。皇帝的目光并非落在她身上,而是越过她,
锁住了那个角落里瑟瑟发抖的身影。那目光平静得可怕,平静底下,是即将择人而噬的寒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