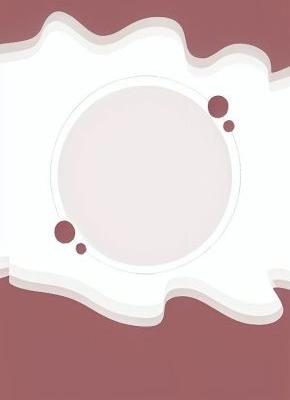
《夏蝉与星屑》第一章暴雨中的向日葵上海的八月末,空气黏稠得如同凝固的蜂蜜,
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蝉声在梧桐树梢嘶鸣,仿佛在用尽生命最后的气力,
为这个即将逝去的夏天奏响挽歌。下午六点,江远被人潮裹挟着挤出写字楼的旋转门。
热浪扑面而来,瞬间在他那副廉价的黑框眼镜上蒙上一层白雾。他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
视野重新清晰起来——映入眼帘的是灰蒙蒙的天空、行色匆匆的路人,
以及远处那排永远在堵车的红色尾灯。在这家名为“新锐”的广告公司实习三个月了,
江远依然无法适应这种快节奏的、充满了虚假热情的环境。他毕业于一所普通的二流大学,
凭着还不错的文笔获得了这个机会,
可他的文案总被总监批为“不够热血”、“缺乏打动人的力量”。“热血?
”江远在心里默默嗤笑。每天挤一个多小时地铁,住着月租两千的老旧阁楼,
面对永远不够花的工资,能心平气和地“活着”就已经耗尽了大部分力气。
这是他的人生信条,也是他面对这座庞大城市的最后防线。
他的“家”在浦西一个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老小区里。那是个不到十五平米的阁楼间,
低矮、闷热,夏天像个密不透风的蒸笼。唯一的优点是有一扇朝西的天窗,天气好的时候,
能看到夕阳将天空染成暖橙色,或是深夜时分,窥见几粒疏淡的星子。而此刻,
他最关心的是能否在下雨前赶到地铁站。天气预报说今晚有暴雨,他没带伞。
可惜天不遂人愿。刚走到半路,远处滚过一阵闷雷,天色迅速暗沉下来。还没等他跑起来,
豆大的雨点就噼里啪啦地砸落,瞬间连成一片雨幕。行人四散奔逃,
江远也只能狼狈地冲向最近的一家24小时便利店,躲在那狭窄的屋檐下,
看着眼前白茫茫的水世界发愁。衣服湿漉漉地贴在身上,又冷又黏。他叹了口气,摸出手机,
屏幕上是房东发来的催缴房租信息。一种熟悉的、深沉的疲惫感漫上心头。
他靠着冰冷的玻璃墙,望着滂沱大雨,几乎想就这样睡去。就在视线漫无目的地游移时,
他瞥见了角落里那个几乎与阴影融为一体的身影。一个女孩。
她蜷缩在便利店灯光照不到的角落,抱着一个看起来比她还大的素描本,整个人湿透了,
浅蓝色的连衣裙紧紧贴着身体,勾勒出瘦削的轮廓。她低着头,下巴抵在膝盖上,
湿漉漉的短发贴在苍白的脸颊边,像一只被暴雨打懵了、无处可去的小流浪猫。
江远的心莫名地动了一下。这么晚了,一个女孩独自在这里……他不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
“活着就好”的信条里,明确写着“不要自找麻烦”。但看着她微微发抖的肩膀,
那种几乎要与这冰冷雨夜融为一体的孤寂感,让他挪不动脚步。犹豫了几秒,
他鬼使神差地走近了一些,
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具有威胁性:“那个……你需要帮助吗?
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女孩猛地抬起头。便利店霓虹招牌的光线掠过她的脸,
照亮了一双极其清澈,却也写满了惊慌的眼眸。她的脸色很苍白,嘴唇冻得有些发紫,
左眼下方那颗小小的泪痣,在迷离的光线下,像一颗即将坠落的星屑。她没有回答,
只是用那双大眼睛警惕地盯着他,抱着素描本的手臂收得更紧了。然后,
她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飞快地翻开被雨水洇湿的素描本,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炭笔,
刷刷刷地画了起来。她的动作很快,带着一种孤注一掷的急切。寥寥数笔,
一朵向日葵的轮廓便跃然纸上。线条简单,甚至有些潦草,但那花朵的姿态却异常生动,
仿佛在迎着并不存在的风雨昂着头,带着一种倔强的生命力。她撕下那页纸,递向他。
手指纤细,微微颤抖着。江远愣住了。他看着那朵纸上的向日葵,
又想起自己阁楼窗台上那几盆真实存在的、金灿灿的向日葵,一种奇异的宿命感击中了他。
在这个冰冷的、令人沮丧的暴雨夜,在这个陌生的、沉默的女孩手中,
他收到了另一朵“向日葵”。他接过那张纸,指尖不经意触碰到她冰凉的皮肤,
感受到她细微的战栗。“……谢谢。”他哑声说,自己也不知道在谢什么。女孩依旧不说话,
只是看着他,眼神里的警惕稍微褪去了一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小心翼翼的探究。雨更大了,
风卷着雨水扫进来,打湿了他的裤脚。他看看手里的画,
又看看这个仿佛被全世界遗弃的女孩,心里那点微不足道的防线,悄然裂开了一道缝。
“我家就在附近,”他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哗啦啦的雨声里显得有些突兀,“是个阁楼,
不大……但可以避雨,等雨停了再说。”他顿了顿,像是为了增加可信度,
补充道:“我种了向日葵,真的。”女孩的目光闪烁了一下,
落在被他小心翼翼捏在手里的那幅画上。她沉默了很长时间,久到江远以为她拒绝了,
正准备放弃时,她才极其轻微地,点了点头。江远松了口气,同时又感到一阵莫名的紧张。
他脱下自己同样湿透的外套,笨拙地举过头顶,示意她一起冲出去。女孩站起身,
个子只到他肩膀,抱着她的素描本,跟在他身边,跑进了茫茫雨幕中。
阁楼比外面看起来还要小,还要简陋。一张单人床,一张旧书桌,一个简易衣柜,
几乎占据了所有空间。唯一的亮色是窗台上那几盆盛开的向日葵,在昏黄的灯光下,
花瓣上的雨珠闪烁着微光,散发着温暖的生命力。女孩一进门,目光就被那抹金色牢牢吸引。
她走过去,像举行什么仪式般,伸出冰凉的手指,极轻极轻地触碰了一下那柔软的花瓣。
然后,她就在花盆旁边的地板上蜷缩下来,抱着膝盖,
像一只终于找到角落可以藏身的小动物,很快就闭上了眼睛,似乎是累极了。
江远看着她湿透的衣服和头发,皱了皱眉。
他翻箱倒柜找出干净的毛巾和一件自己穿旧了的宽大T恤,轻轻放在她身边。
又去狭小的共用厨房烧了热水,冲了一杯板蓝根。等他端着杯子出来时,
发现女孩已经靠着墙壁睡着了,呼吸清浅,怀里的素描本抱得死死的。他叹了口气,
拿起一旁有些发硬的薄毯,动作尽量轻柔地盖在她身上。就在他弯腰,
毯子边缘滑过她手腕的瞬间,他清晰地看到,在那纤细白皙的手腕内侧,
有几道淡白色的、已经愈合却依旧刺眼的旧伤疤。江远的手顿住了,
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无形地捏了一下,微微收缩,泛起一阵酸涩的凉意。这个沉默的女孩,
究竟背负着什么?窗外,雨声未歇,蝉声已黯。在这个拥挤的、属于他的小小世界里,
突然多了一个沉默的、带着伤痕和秘密的闯入者。夏天的尾巴,似乎因此变得不同起来。
第二章阁楼里的星空第二天清晨,江远是被透过天窗的阳光唤醒的。暴雨过后,
天空碧蓝如洗。他揉了揉眼睛,下意识地看向墙角。女孩已经醒了,正抱着素描本,
安静地坐在那里画画。晨曦勾勒着她柔和的侧脸轮廓,那颗泪痣显得格外清晰。
她换上了他的旧T恤,宽大的衣服罩在她身上,更显得她身形娇小。
湿衣服被她仔细地晾在了椅背上。看到他醒来,她似乎有些紧张,停下了笔。“早。
”江远有些不自然地打招呼,嗓子因为刚睡醒而沙哑。女孩没有回应,只是看着他,
然后像是想起什么,在素描本上写下两个字,举给他看。林夕。字迹清秀,带着一点稚气。
“林夕?”江远念出声,“很好听的名字。”林夕微微抿了抿嘴,
似乎是一个浅淡的笑意向来。接下来的日子,一种奇妙的同居生活开始了。
江远依旧早出晚归,为那些“不够热血”的文案绞尽脑汁。林夕则安静地待在阁楼里,
与她的素描本为伴。江远发现,林夕虽然不说话,但她很爱干净,
会把小小的阁楼收拾得井井有条。她似乎对泡面纸箱很感兴趣,有一次,她指着空箱子,
又指了指墙角,用询问的眼神看着江远。“你想要这个?”江远问。林夕点点头。
江远帮她清理干净纸箱,看着她用美工刀(不知她从哪里翻出来的)熟练地裁剪、拼接,
竟然做出了一个像模像样的临时小书桌,正好放在天窗下面。第二天江远下班回来,
发现那张泡面箱书桌上放着一幅画。画的是夜晚的阁楼内部。视角是从下往上的,
聚焦在那扇天窗。窗外不是真实的、往往只有零星几颗星星的上海夜空,
而是一片浩瀚无垠、璀璨夺目的星河。银河倾泻,星云旋转,色彩浓烈奔放,
带着一种梵高画作般的燃烧感和生命力。星光透过天窗洒落下来,照亮了简陋的阁楼,
连角落里的向日葵仿佛都在星光照耀下熠熠生辉。画的右下角,写着一行娟秀的小字:房租。
谢谢。江远拿着这幅画,站在逼仄的阁楼里,却仿佛真的感受到了一片无垠的星空笼罩下来。
心中的疲惫和都市的逼仄,在这一刻奇异地被驱散了。“这房租……太贵重了。
”他喃喃自语,小心地将画收好,贴在了床头最显眼的位置。林夕看着他珍视的动作,
眼睛弯成了月牙。他们之间的交流,主要依靠简单的手势、表情,以及林夕的画。
江远会给她带一些零食和画具,
们的日常——江远吃泡面的样子、他睡着时微微皱起的眉头、窗台上的向日葵每一天的变化。
她的画就是她的语言,色彩鲜明,情感浓烈,与她的沉默寡言形成巨大的反差。一天,
江远在公司里那个关于“青春活力”的饮料广告提案再次被总监全盘否定,被批得一无是处。
“江远!我说过多少次了!要热血!要**!要让人看了就想立刻去奔跑、去追逐梦想!
你这写的是什么?温吞水!垃圾!”总监唾沫横飞,将打印稿摔在桌上。江远低着头,
默默承受着。他试图解释,他理解的青春不只有热血,还有迷茫、孤独和细碎的温暖,
但总监根本听不进去。下班后,他心情低落地去便利店买了几罐最便宜的啤酒,回到阁楼,
坐在地板上一言不发地喝着。林夕安静地坐在他旁边,看着他闷头喝酒,眉头微微蹙起。
直到江远醉眼朦胧地趴在泡面箱书桌上,她才轻轻拿起炭笔,拉过他放在桌上的手,
在他手背上仔细地、一笔一画地画了一个大大的、有点歪斜的笑脸。手背传来痒痒的触感,
江远抬起头,眼神迷茫。林夕指了指窗外。暴雨早已停歇,夜色如洗。
由于今晚片区临时停电,附近高楼的光污染减弱了许多,
竟然露出了难得一见的、虽然稀疏却格外明亮的星星。
看着手背上那个笨拙却充满善意的笑脸,再看看窗外那片久违的清澈星空,
江远胸中的郁气忽然就散了大半。酒精带来的眩晕感还在,但心里却奇异地安定下来。
他揉了揉林夕柔软的短发,声音沙哑:“谢谢。”林夕弯起眼睛,
露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温暖的笑容。那一刻,江远觉得,或许这个夏天,
也并非全然糟糕。然而,平静的日子很快被打破。一天深夜,江远被身边急促的呼吸声惊醒。
打开灯,发现林夕蜷缩在床上,脸色潮红,额头滚烫,浑身都在发抖。她发烧了,
而且度数不低。江远瞬间慌了神。他想起她手腕上的伤疤,想起她偶尔流露出的脆弱,
一种强烈的保护欲涌上心头。他二话不说,背起意识模糊的林夕,冲下了阁楼。
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只有他急促的脚步声和粗重的喘息在回荡。
背上的林夕轻得像一片羽毛,滚烫的呼吸喷在他的颈窝,带来一阵阵灼热感。
就在他拼命向附近社区医院奔跑的时候,他忽然听到一个极其沙哑、微弱,
几乎被风声盖过的声音,贴着他的耳廓响起。“谢……谢。”江远脚步猛地一顿,
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撞击,又酸又麻,几乎停止了跳动。他难以置信地侧过头,
看向伏在他肩头的女孩。她依旧闭着眼,眉头痛苦地蹙着,仿佛刚才那声呓语只是他的幻觉。
但他知道不是。那是林夕的声音。沙哑,生涩,却真真切切。这是她住进阁楼以来,
第一次发出声音。第三章无声的告白与蝉蜕林夕得的是急性肺炎,需要住院观察几天。
江远向公司请了假,日夜守在病床边。他用自己本就微薄的积蓄支付了医药费,
没有一丝犹豫。林夕醒来后,看着周围白色的墙壁,眼神有一瞬间的恐慌,
直到看到趴在床边睡着的江远,才渐渐安定下来。她伸出手,轻轻碰了碰他凌乱的头发。
江远立刻惊醒了:“你醒了?感觉怎么样?”他眼里布满血丝,但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林夕摇了摇头,表示自己没事。她拿起床头的素描本,
画了一个戴着口罩、举着针筒的卡通向日葵,旁边写着:我很好,别担心。江远看着那幅画,
哭笑不得,心里却软成一滩水。住院期间,林夕的画更多了。
她画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像探查向日葵的园丁,画输液瓶像给花朵浇水的神奇水壶,
画窗外一成不变的楼房和偶尔飞过的鸽子。她的画总是充满了奇妙的想象力,
将枯燥甚至痛苦的事物变得温暖而有趣。江远发现,当她沉浸绘画时,
那种萦绕在她周身的不安和疏离感会减弱很多,仿佛画笔是她与这个世界和解的唯一方式。
一次,他无意中看到林夕素描本的一页,
上面反复画着一个相同的图案——一座孤独矗立在悬崖边的灯塔,灯塔顶端射出的光束,
照亮了下方汹涌的黑色海面,而夜空中有无数细碎的星屑洒落。这幅画他似乎见过好几次了,
每次色彩和细节都有些微不同,但那种孤寂又渴望被照亮的感觉始终如一。“你喜欢灯塔?
”江远问。林夕握着笔的手指紧了紧,抬起头,眼神有些复杂。她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最终在画纸空白处写下:它在那里,等光,也等人。江远不太明白,但他没有追问。
每个人都有不愿言说的秘密,就像他从未问过她手腕的伤疤,以及她为何流落街头。
林夕出院后,似乎对江远更加依赖。他们之间的默契与日俱增。有时江远一个眼神,
林夕就能明白他想找什么;有时林夕只是安静地看着他,江远就能感觉到她细微的情绪变化。
夏天在不知不觉中走向尾声。窗外的蝉鸣声渐渐稀疏,带着一种力竭后的苍凉。一天周末,
江远打扫阁楼卫生,在床底最里侧发现了一个小小的、透明的东西——是一枚完整的蝉蜕。
薄脆,空灵,保持着挣扎脱壳时的姿态,在阳光下闪着琥珀色的微光。蝉蜕下面,
压着一页从素描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不是画,而是一行字,
是林夕的笔迹:“蝉在地下蛰伏七年,忍受黑暗和孤寂,只为了一个夏天的尽情鸣唱。
”“就像我,仿佛也等待了二十三年,才在这个夏天,遇见你。”江远捏着那张轻飘飘的纸,
看着那句无声却重若千钧的告白,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填满了,涨得发酸,又暖得发烫。
他转过头,看向正坐在天窗下,沐浴在阳光里安静画画的林夕,
金色的光晕勾勒着她认真的侧脸,美好得像一个不真实的梦。他走过去,在她身边坐下,
将蝉蜕和那张纸轻轻放在她的素描本上。林夕抬起头,看到那两样东西,脸颊瞬间染上红晕,
眼神有些慌乱,像是藏了很久的秘密被人发现。江远没有说话,只是看着她,
目光温柔而坚定。他伸出手,轻轻握住了她放在膝盖上的手。她的手很小,很凉,
微微颤抖了一下,却没有挣脱。阁楼里很安静,只有彼此呼吸的声音。窗外,
最后几声蝉鸣有气无力地响着,仿佛在为他们作证。这个夏天,即将结束。但有些东西,
才刚刚开始。然而,命运的急转直下,往往发生在最平静的时刻。好的,
我们继续这个温暖又带着些许伤感的夏日故事。---第四章风暴前夜蝉蜕下的告白,
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两人之间漾开了一圈圈暧昧而温暖的涟漪。
阁楼里弥漫着一种心照不宣的甜蜜,无声,却无处不在。江远用攒了许久的工资,
偷偷买了一个星空投影仪。在一个普通的夜晚,当阁楼唯一的灯泡也被他关上,
小小的空间瞬间被无数柔和的光点填满。银河蜿蜒,星云变幻,
仿佛将林夕画中的那片星空搬到了现实。林夕仰着头,瞳孔里倒映着流转的星海,
脸上写满了惊叹和迷醉。她盘腿坐在“星空”下,像个第一次看到宇宙的孩子。
在这样不真实的光影中,在只有彼此呼吸声的静谧里,林夕转过头,
看着身边同样沐浴在星辉下的江远,嘴唇嚅动了几下。然后,一个极其沙哑、缓慢,
却异常清晰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响了起来:“小时候……我住过……很大的房子。但很冷。
”她指了指自己的胸口,“这里冷。”“他们……给我很多玩具,很多衣服……但没有人,
听我说话。”“他们……要我……去见一个人。一个……我不喜欢的人。像……交易。
”“我害怕……就跑出来了。”她的叙述破碎,夹杂着长久的停顿和艰难的呼吸,
仿佛每一个字都用尽了力气。没有细节,没有名字,但江远听懂了。
他仿佛看到了一个穿着华丽却眼神空洞的小女孩,在空旷冰冷的豪宅里,
面对着名为“收养”实为“投资”的冷漠,最终在压力和绝望中,选择了封闭自己的声音,
并在成年后被当作了联姻的工具。当她说出“交易”两个字时,眼泪终于无声地滑落,
那颗泪痣仿佛真的承载了太多的悲伤。江远的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紧紧攥住,
疼得他几乎无法呼吸。他伸出手,将她轻轻揽入怀中。林夕没有抗拒,把脸埋在他的肩膀上,
瘦弱的身体因为压抑的哭泣而微微颤抖。两人在虚假却温暖的星空下,紧紧相拥,
像两只在寒冬里互相取暖的幼兽。“没关系了,林夕。”江远的声音低沉而坚定,
“不想说就不说,不想回去就不回去。只要我在这里,这个阁楼就是你的家。”他的承诺,
在那个星空摇曳的夜晚,掷地有声。然而,现实的阴影终究会追来。几天后的一个下午,
江远正在公司修改一份永远“不够热血”的策划案,手机突然响起,是一个陌生号码。
他下意识地挂断,对方却固执地再次打来。一种不祥的预感攫住了他。他接起电话,
那头传来房东焦急的声音:“小江啊!你快回来一趟!你家门口来了好几个人,凶神恶煞的,
说是来找什么林**的!我怕出事啊!”江远脑子里“嗡”的一声,来不及多想,
抓起背包就冲出了公司,一路狂奔回家。刚跑到楼下,
就看到几个穿着黑色西装、身形彪悍的男人守在他那栋旧楼的单元门口,
引得邻居们远远围观,指指点点。江远的心沉到了谷底,他拨开人群,冲上楼。
狭窄的楼梯口,站着一个身着昂贵西装、气质威严的中年男人。他看起来五十岁左右,
眼神锐利如鹰,正用一种毫不掩饰的鄙夷和愤怒,审视着这破旧的环境。
而阁楼那扇薄薄的木门敞开着,里面传来轻微的、像是东西被打翻的声音。江远冲过去,
被一个保镖伸手拦住。“你是谁?让开!”江远试图挣脱。中年男人冷冷地扫了他一眼,
那目光像冰锥一样刺人:“你就是江远?我是林夕的父亲。我来带我女儿回家。
”“她不想回去!”江远梗着脖子,与男人对视。“不想回去?”男人嗤笑一声,
带着上位者固有的傲慢,“她精神不稳定,需要治疗和静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