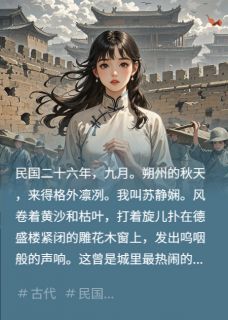
雅间里只剩下我和文远。
窗外的风还在呜咽。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棂,在他清瘦的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他疲惫地靠在椅背上,闭上双眼,眉头紧锁。那副沉重的担子,似乎将他单薄的身躯压得更弯了。
“文远……”我走到他身后,双手轻轻按在他僵硬的肩膀上,想揉散那积聚的愁苦。指尖触到的,是骨头坚硬的轮廓和衣衫下透出的凉意。
他睁开眼,握住我放在他肩头的手。他的手冰冷,微微颤抖。“静娴,”他的声音带着浓重的疲惫,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脆弱,“你怕吗?”
怕?我怎么会不怕?我怕得心都在抽搐!我怕那黑压压的炮口,怕那寒光闪闪的刺刀,怕那城破后必然降临的屠杀与**。但我更怕失去他!失去这个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失去我们共同构筑的、虽然清贫却充满温暖的小家!失去那个在灯下教我识字、给我讲家国天下道理的夫君!
千言万语堵在喉咙口,最终只化作一声哽咽:“我……我只想你活着……”泪水不受控制地涌出,滚烫地滴落在他冰凉的手背上。
他转过身,将我冰凉的手紧紧包裹在他同样冰凉的双手中。镜片后的眼睛里,有深不见底的痛苦,也有一种近乎悲悯的温柔。“静娴,对不起……”他低语着,声音沙哑,“身为一县之长,有些事,明知不可为,亦当为之。有些路,明知是绝路,亦当行至尽头。这……是我的宿命。”
宿命?这两个字像冰冷的针,刺穿了我最后的侥幸。那一刻,我清晰地感觉到,那个温润如玉、心怀理想的读书人夫君,正在被一种巨大的、残酷的力量重塑。他正在将自己,锻造成一柄注定要折断在国难前的剑。
接下来的两天,朔州城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寂静与骚动交织的状态。
通牒的消息像瘟疫一样传遍了全城。恐惧如同实质的浓雾,笼罩着每一条街巷。往日还算热闹的市集变得门可罗雀,商铺早早关门,街上的行人步履匆匆,眼神躲闪,彼此间连交谈都压低了声音,仿佛怕惊扰了什么。空气中弥漫着绝望的气息,还有一丝末日来临前的麻木。
然而,在这片压抑的死寂之下,暗流却在汹涌。
陈启明府邸的门槛几乎被踏破。惶惶不可终日的富商、地主、以及一些自诩“识时务”的士绅,纷纷登门,或晓之以“理”(保命为上),或动之以“情”(身家财产),或诱之以“利”(暗示投降后维持商会地位),目的只有一个:劝说陈启明联合众人,向陆文远施压,促成开城投降。陈启明的书房里烟雾缭绕,叹息声、争执声不绝于耳。他疲惫地应付着,捻着佛珠的手从未停过,眼底的挣扎与焦虑日益加深。他并非全无私心,他庞大的商业帝国是他一生的心血,投降或许能保全部分财产和家人的安全。但他内心深处,又何尝没有一丝读书人的气节?尤其是当他看到女儿陈书瑶那沉默而倔强的眼神时。
书瑶没有留在父亲身边。她回到了女校。这所由陆文远和陈启明共同出资兴办、她亲自担任校长的学校,此刻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堡垒。她没有在课堂上宣讲抗战,只是更加严格地要求学生们练习包扎、急救,讲解简单的战地护理知识。沉默的行动,胜过千言万语。一些年长些的女学生,眼神从最初的恐惧茫然,渐渐变得沉静而坚定。她们开始自发地收集干净的布条,**简易绷带。书瑶的行动,像无声的宣言,刺痛了陈启明,也悄然影响着部分人的选择。
而我的妹妹苏静姝,则像一只受惊后终于鼓起勇气的小鸟,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城防工事附近。她不再只是躲在姐姐身后哭泣。或许是赵烽那沉默而坚定的身影给了她力量,或许是被周振武那番话点燃了心底的火焰。她脱下心爱的学生裙,换上粗布衣裤,扎起辫子,加入了由城中妇女自发组织的后勤队伍。她们为守城的士兵和民夫送水送饭,搬运砖石木料加固城墙。那双曾经只拿画笔和书本的手,如今磨出了水泡,沾满了泥灰。每次看到赵烽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挥汗如雨,她都会悄悄地把最干净的水和最热乎的饼子塞给他。赵烽依旧沉默寡言,但接过东西时,眼神会变得柔和,甚至笨拙地低声说一句:“谢谢……苏二**。”静姝便会低下头,脸上飞起两朵红云,那点羞涩中,竟也生出几分奇异的勇气。
周振武和赵烽成了城里最忙碌的人。他们几乎不眠不休,带着仅存的几百名正规军士兵和临时组织起来的青壮民夫,加固城防。朔州城墙老旧,多处破损。没有水泥,就用黄土夯;没有钢筋,就用木桩顶。他们将城内能找到的木料、门板甚至棺材板都征用过来,加高加厚城墙。在城墙上凿出射击孔,用沙袋垒砌掩体。周振武亲自示范,教那些从未摸过枪的民夫如何装填土铳、如何点燃土**包(一种用火药和碎铁片自制的简陋武器)。他的声音嘶哑,眼神却像鹰隼一样锐利,巡视着每一处工事。赵烽则像他的影子,沉默地执行着每一项命令,同时不动声色地将一些最危险的任务揽在自己身上,尽量保护着那些生涩的民夫。他们身上散发出的那种视死如归的军人气质,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一些原本犹豫不决的年轻人。一些店铺伙计、作坊学徒,甚至街头游荡的小混混,默默地加入了他们的队伍,拿起能找到的任何武器——锈蚀的大刀、长矛、猎叉,甚至是削尖的木棍。一种悲壮的气氛,在恐惧的冰层下悄然滋生。
我的家,那处小小的县衙后院,也成了风暴的中心。
文远几乎不再回来。他要么在城防工地上与周振武、赵烽商议,要么在县衙大堂召集仅存的几位官员部署,要么就是深入街巷,试图安抚惊恐的百姓。偶尔回来,也是满身尘土,疲惫不堪,匆匆吃几口饭,又消失在沉沉的夜色里。我看着他那迅速消瘦下去的脸颊和布满血丝的眼睛,心如刀绞。
恐惧像藤蔓一样缠绕着我,日夜不息。我无法像书瑶那样投身实务,也无法像静姝那样找到宣泄的出口。我的世界太小了,只有文远。我无法理解他口中那宏大的家国大义,我只想我的丈夫活着!这个念头像毒蛇一样噬咬着我的心。
一个疯狂的念头在我心中滋生、蔓延。
那天深夜,文远伏在书案前,就着昏黄的油灯,起草着一份《朔州军民抗战宣言》。他的字迹刚劲有力,饱蘸着墨汁,也饱蘸着他的一腔热血。我悄悄站在门外,看着他专注而决绝的侧影,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头顶。
等他终于支撑不住,伏在案上沉沉睡去,我像幽灵一样溜了进去。油灯的火苗跳跃着,在他苍白的脸上投下晃动的光影。我颤抖着手,拿起他刚刚写好的那份宣言草稿。那滚烫的字句灼烧着我的眼睛。我咬着牙,将它卷起,藏进我贴身的小袄里。然后,我坐到他的位置上,铺开一张崭新的宣纸,拿起他常用的那支狼毫笔。
我的手抖得厉害,墨汁滴在纸上,晕开一团污迹。我深吸几口气,努力回忆他平日批阅公文的笔迹。一点,一横,一撇,一捺……模仿着他的字体,我写下了一封截然不同的文书——《朔州开城请降书》。每一个字,都像在我心上剜一刀。我写着日寇如何强大,朔州如何弱小,百姓如何无辜,恳请“皇军”仁慈,网开一面……写到最后,我的泪水早已模糊了视线,滴落在未干的墨迹上,晕染开一片绝望的墨花。
这封浸透了我卑微乞求和绝望泪水的“投降书”,被我小心翼翼地折好,藏在了梳妆盒的最底层。它是我为自己保留的最后一丝幻想,是我试图从命运手中抢夺文远性命的、脆弱不堪的筹码。
第三天,一种更深的焦虑开始在城中蔓延。关于日本人暴行的可怕传闻,如同长了翅膀的毒虫,在每一个角落滋生、传播。有说保定府抵抗的城市被屠得鸡犬不留的;有说大同投降后,富户被洗劫一空,女人被**的;更有绘声绘色描述日军如何用刺刀挑着婴儿玩耍的……这些传闻真假难辨,却像重锤一样敲打着人们本就脆弱的神经。投降派的声音似乎又大了起来。
这天下午,陈启明派管家悄悄递来口信,约我在城西僻静的关帝庙后见面。我知道他为何找我。揣着一颗七上八下的心,我裹紧了头巾,避开人群,来到了那座香火早已冷落、只剩残破神像的庙宇后。
陈启明早已等在那里,背着手,望着斑驳的墙壁,显得更加苍老和萧索。
“静娴侄女,”他转过身,脸上是掩饰不住的憔悴,“你……劝过文远了吗?”
我的眼泪瞬间涌了出来。扑通一声,我跪在了冰冷的地砖上。“陈伯父!”我哽咽着,声音破碎不堪,“我求您了!您德高望重,您去劝劝他吧!他不能死!他真的不能死啊!他是读书人,是县长,可他也是我的丈夫啊!他若有个三长两短,我……我也不活了……”我泣不成声,额头几乎要磕到地上。这几日积压的恐惧、委屈、绝望,在这一刻彻底爆发。
陈启明慌忙上前扶起我,浑浊的老眼里也泛起了泪花。“静娴,静娴,快起来!你这是做什么!”他扶我在旁边的石阶上坐下,深深叹了口气,带着无尽的疲惫和无奈。“我何尝不想劝他?我何尝不想保全这一城百姓,保全我们自己的身家性命?可是……静娴啊,你不懂文远。他这个人,看着温和,骨子里比谁都硬!比石头还硬!他认准的道,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他不是不懂利害,他是把‘气节’二字,看得比命还重啊!”
他颓然地坐下,捻着佛珠的手都在颤抖。“你知道吗?昨天我去找他,苦口婆心,把能说的道理都说尽了。我告诉他,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忍一时之辱,或许将来还能徐图恢复。可你猜他怎么说?”陈启明模仿着文远的语气,带着一种悲凉的决绝,“他说:‘启明兄,青山若易主,柴烧得再旺,暖的也是异族的心!今日我若忍了这辱,明日我的子孙后代,脊梁骨就再也直不起来了!’”
陈启明摇着头,老泪纵横:“我……我无言以对啊!静娴,他是一县之长,是朔州的魂!他的骨头硬,这朔州城的骨头,就不能软!可这骨头硬起来的代价……是满城的血啊!”他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他的话,像冰水浇头,彻底浇灭了我心中最后一丝幻想。连陈启明都无法动摇文远分毫,我那封可笑的投降书,又能改变什么?它只会成为我永远无法洗刷的耻辱,成为对文远那份赤诚信念的亵渎。
巨大的绝望攫住了我,让我浑身冰冷,连哭泣的力气都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