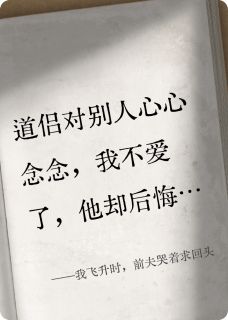
道侣对别人心心念念,我不爱了,他却后悔了第一章解契昆仑墟的雪,下了整整三个月。
我盘坐在寒潭边,指尖按在冰面上,试图用灵力逼出侵入肺腑的寒毒。可丹田空空荡荡,
昨日为救凌越挡下的那记玄冰刺,不仅震碎了我的金丹,还将这阴毒的寒气钉进了经脉深处。
每一次呼吸,都像吞进一把碎冰,沿着喉咙往下刮,疼得我眼前发黑。远处传来脚步声,
我抬头,看见凌越踏着积雪走来。他依旧是一身月白道袍,风姿卓绝,
腰间玉佩随着步伐轻晃,折射出冷冽的光。只是眉宇间那几分不耐,像针一样扎进我眼里。
"阿凝,你怎么还在这儿?"他站在潭边,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玄冰刺的寒气还残留在他袖角,混着清欢惯用的桃花香,"清欢师妹在丹房等着拿疗伤药,
你快去备好。"我望着他,忽然笑了。笑声牵扯起肺腑的疼痛,咳出的血珠落在冰面上,
像绽开的红梅,很快又被寒气冻住。"凌越,"我的声音很轻,
却带着连自己都未察觉的疲惫,"我快死了。"他皱眉,似乎没听清,
又或许是不愿听清:"你说什么?清欢师妹等着呢,她昨日为了帮我寻药,
被妖兽抓伤了手臂,耽误不得。"又是清欢。我垂下眼,看着冰面上自己苍白如纸的脸。
金丹碎了,经脉断了七处,寒毒正在啃噬五脏六腑,而我的道侣,
关心的却是另一个女人手臂上的轻伤。那伤口我见过,不过寸许长,以清欢的修为,
三日便能自愈。三年前,我为他挡下魔修的致命一击,修为倒退三十年,
咳出的血染红了他半幅道袍。他守在我床边三日,
第四日便被刚入门的清欢以"修炼遇挫"为由叫走,回来时袖袋里揣着给她买的桂花糕。
两年前,我寻遍万险秘境为他寻来突破元婴的仙草,九死一生,回来时肋骨断了三根。
他接过仙草,转身就送给了清欢,只因她说"这草开得好看,想插在花瓶里"。一年前,
我们的定情玉佩被他不慎遗落,那是我用本命精血温养的法器,能挡三次死劫。
他却为了帮清欢寻找走失的灵宠,让我在风雪里找了整整七天。我冻得失去知觉,
被弟子抬回来时,他正陪着清欢在暖阁里煮酒,看灵宠在她膝头撒欢。桩桩件件,
像寒潭里的冰棱,一点点刺穿我的心。如今想来,那些被我当作"意外"的疏忽,
其实都是他精心选择的结果——他永远选择清欢,永远放弃我。"凌越,"我抬起头,
直视着他的眼睛,那里面曾有过让我沉溺的温柔,如今只剩下对另一个人的牵挂,
"我们解契吧。"他终于愣住了,脸上的不耐褪去,换上错愕:"你说什么胡话?
不过是受了些伤,我让丹堂长老给你最好的丹药......""我不要丹药。"我打断他,
声音平静得可怕,"我要解契。"解契二字,像一道惊雷,在他脸上炸开。他猛地蹲下身,
抓住我的手腕,指尖冰凉,带着急切:"阿凝,你闹够了没有?就因为我没第一时间来看你?
清欢她......""她人淡如菊,她纯洁善良,她做什么都是无心之失,
"我一字一句地接话,声音里带着自嘲,"而我,就是那个善妒、刻薄、只会拖累你的累赘,
对吗?"这些话,是他在我抱怨清欢总是找借口支开他时,亲口对我说的。那时他坐在窗边,
月光落在他侧脸,语气里的厌烦像冰锥一样扎进我心里。凌越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
他张了张嘴,似乎想反驳,却最终只是低声道:"我不是那个意思......阿凝,
别任性。"任性?我笑了,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原来在他眼里,
我连提出结束这段早已腐朽的关系,都只是任性。他大概以为,我就该像条狗一样,
无论他怎么踢打,都会摇着尾巴等他回头。"凌越,"我用力抽回手,掌心被他捏出了红痕,
"三日前,你为了陪清欢去看新开的灵花,让我独自去对付那只千年冰蛟。
我为了活着回来见你,拼尽最后一丝灵力,才侥幸逃脱,却也中了这无药可解的寒毒。
""你知不知道,金丹碎了,我这辈子都再难精进?你知不知道,寒毒入骨,
我撑不过这个冬天?"他的脸色一点点变得苍白,
眼神里终于有了一丝慌乱:"我......我不知道你伤得这么重,
清欢说你只是受了点皮外伤......"又是清欢说。我闭上眼,再睁开时,
心底最后一点温度也消失殆尽。原来我的生死,在他那里,从来都需要清欢来转述。
"不必说了。"我从怀里掏出那枚早已失去光泽的契书,那是我们结契时,
用双方精血炼化的凭证,边角处已经被我的指温磨得发亮,"今日,我苏凝,与凌越解契,
从此男婚女嫁,各不相干。"指尖凝聚起最后一点灵力,我朝着契书拍去。只要灵力注入,
契书便会碎裂,我们之间的道侣羁绊,也会随之烟消云散。"不要!"凌越猛地扑过来,
死死按住我的手,眼里是前所未有的恐慌,"阿凝!不能解契!我不准!"他的力气很大,
我本就虚弱,根本挣脱不开。他看着我,眼神里混杂着慌乱、不解,
还有一丝被冒犯的怒意:"苏凝!你到底要怎样?我知道你对清欢有意见,
我以后少和她来往就是了!你别闹了,好不好?"少来往就是了?我看着他慌乱的眼睛,
忽然觉得无比荒谬。他以为我争的是这些吗?我争的是他的在意,是他的偏爱,
是他哪怕只有一次,能把我放在心上。可他不懂,或许从一开始就不想懂。"凌越,
"我看着他慌乱的眼睛,一字一句道,"你抓得住这张契书,抓不住我冷了的心。"说完,
我猛地撤回手,同时将所有残余灵力逆行,硬生生震碎了体内与他相连的契印。
剧烈的疼痛袭来,像是有无数把刀在体内搅动,识海翻涌,眼前一黑。
耳边传来契书落地的脆响,还有凌越惊恐的叫喊声。"阿凝——!"我坠入无边的黑暗前,
最后一个念头是:终于,解脱了。第二章无情再次醒来时,我躺在一间简陋的木屋。
窗外是连绵的竹海,竹叶上的露珠滴落,敲在石桌上,叮咚作响。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药香,
混着竹节的清苦。一个白发老者坐在床边,见我醒来,捋了捋胡须:"小姑娘,命够硬的啊,
金丹碎了,契印自毁,还能活下来。"我动了动手指,浑身骨头像散了架,
寒毒依旧在经脉里游走,只是被一种温和的力量压制着:"是前辈救了我?
""路过顺手罢了。"老者递过来一碗黑乎乎的药汤,药香更浓了,"喝了吧,
能吊着你的命。不过你这情况,修为是彻底废了,往后就是个普通人了。"我接过药碗,
一饮而尽。苦涩的药液滑入喉咙,熨贴着灼痛的经脉,心里却异常平静。废了也好,
从此与修仙界再无瓜葛,不必再为谁痛,为谁等。老者看着我,
忽然道:"我看你眉宇间怨气太重,怕是恨极了那个让你自毁契印的人?"我沉默片刻,
摇了摇头:"不恨了。"爱之深,才会恨之切。可当一颗心彻底死了,连恨都成了多余。
就像枯死的树,不会再为春风心动,也不会为冬雪悲戚。老者愣了一下,
随即笑了:"有意思。你这心境,倒是适合修我这一脉的功法。
"他从怀里掏出一本泛黄的古籍,封面上写着三个古朴的字——《无情道》。
"此道以无情为基,以断念为要,修到极致,可重塑道心,威力无穷,
但代价是......从此再无七情六欲。"老者看着我,眼神复杂,"你可想好了?
"无七情六欲。不会再爱,不会再痛,不会再为谁辗转反侧,不会再为谁心碎流泪。
我接过那本古籍,指尖抚过冰冷的封面,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那些被凌越碾碎的真心,被清欢践踏的尊严,或许都能在这无情道里,化为最锋利的剑。
"我修。"老者叹了口气:"也罢,或许这对你来说,才是最好的归宿。"接下来的三年,
我就在这竹屋里,跟着老者修习《无情道》。起初很难。夜里总会梦见凌越,
梦见我们初遇时他在桃花树下对我笑,白衣胜雪,桃花落在他发间;梦见他为我挡下风雨,
将我护在身后,说"阿凝别怕";梦见他在结契大典上执我的手,
说要与我共证长生......那些甜蜜的过往,像淬了毒的糖,在我心头反复灼烧,
逼得我夜夜惊醒,冷汗湿透衣背。每当这时,我便会运转《无情道》的心法,
用冰冷的灵力一遍遍冲刷识海,将那些画面冻结、碾碎,直到它们变得模糊,
直到心里再无波澜。老者说,无情道不是真的无情,而是将情化为道,不为情所困。
可我知道,我是在自毁,将那颗千疮百孔的心,一点点冰封,一点点碾碎,
直到再也拼凑不起来。这样很好,至少不会再疼了。三年后,老者羽化。临终前,他看着我,
眼里带着复杂的情绪:"你虽入了无情道,却终究是为了逃避。他日若遇旧人旧事,
切记守住本心,否则......万劫不复。"我送走了老者,独自留在竹屋。此时的我,
修为已重回金丹,甚至隐隐有突破元婴的迹象。《无情道》的威力远超想象,
灵力运转时带着彻骨的寒意,能冻结一切触碰到的东西。只是我的眼神,越来越冷,
越来越静,像深不见底的寒潭,倒映不出任何情绪。我离开了竹海,
给自己取了个新的名字——苏无情。第三章窃运我离开昆仑墟的第二年,
凌越在一次宗门秘境试炼中,栽了个前所未有的大跟头。那秘境本是低阶修士历练之地,
他作为首座陪同前往,原是万无一失。可就在他为弟子演示剑法时,丹田内的灵力突然逆行,
长剑脱手飞出,不仅斩断了自己的左手经脉,还震塌了秘境入口的封印,
放出了里面镇压百年的毒蛟。混乱中,三名弟子被毒蛟所伤,毒素蔓延,险些废了修为。
消息传回昆仑墟时,清欢正跪在凌越的床前,哭得泪眼婆娑:"凌越哥哥,都怪我不好,
若不是我非要跟着来,你也不会分心......"凌越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如纸,
左手被厚厚的纱布包裹着,渗出的血渍将纱布染得暗红。他看着清欢,眼中虽有疲惫,
却依旧带着惯有的纵容:"与你无关,是我自己出了岔子。"可他没发现,
清欢垂在袖中的手,正悄悄捏着一枚乌黑的符咒,符咒上的纹路在灵力催动下,
泛着极淡的黑气——那是她昨夜趁他熟睡时,贴在他床榻下的"晦运符"。
这符咒能悄无声息地引动宿主的霉运,让他诸事不顺。真正让凌越心生疑窦的,
是三日后的掌门问诊。掌门指尖搭在他腕脉上,眉头越皱越紧,最后长长叹了口气:"凌越,
你的气运......在衰败。""衰败?"凌越皱眉,他自出生起便气运鼎盛,
修炼一路顺遂,从未有过瓶颈,"弟子修炼向来顺遂,何来衰败之说?"掌门摇头,
从袖中取出一面铜镜,镜面光滑如洗,映照出凌越的虚影。
虚影周身本该环绕着金色的气运光晕,那是昆仑墟历代天才的标志,
此刻却稀薄得几乎看不见,边缘处甚至有黑色的雾气在蚕食,像一群贪婪的虫蚁。"你看,
"掌门指着镜中虚影,语气凝重,"寻常修士气运偶有起伏,却绝不会像你这般,
短短数月内衰败至此。除非......""除非什么?"凌越的心跳漏了一拍,
一个荒谬却又挥之不去的念头浮了上来。"除非有人在暗中窃你的气运。
"掌门的声音凝重如铁,"而且用的是极为阴邪的术法,悄无声息,却能断你根基,
毁你道途。"凌越心头猛地一震。他想起我离开前,寒潭边那双冰冷的眼,
想起我自毁契印时决绝的背影,
来频频出现的修炼岔道、法器失灵、秘境遇险......那些被他归咎于"心魔"的变故,
此刻想来,竟都指向同一个可怕的可能。他踉跄着起身,不顾掌门的阻拦,直奔清欢的院落。
清欢正在梳妆,铜镜里映出她娇美的面容,嘴角噙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她刚用凌越的气运突破了金丹,浑身灵力充沛,连皮肤都透着莹润的光泽。听到脚步声,
她回头,看到凌越苍白的脸,眼中闪过一丝慌乱,随即又换上担忧的神情:"凌越哥哥,
你怎么来了?伤口还疼吗?"凌越没有回答,只是死死地盯着她。
他的目光扫过她发髻上的玉簪——那玉簪是他前几日送的,本是昆仑墟的暖玉,能温养灵力,
此刻却泛着一丝不属于暖玉的阴冷气息,与他腕脉中那股蚕食气运的黑气如出一辙。
他一步步逼近,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清欢,你老实告诉我,
你是不是修炼了什么邪术?"清欢脸色煞白,下意识后退:"凌越哥哥,
你......你在说什么?我怎么会修炼邪术......""那你告诉我,
"凌越指着她的玉簪,指尖因为愤怒而颤抖,"这玉簪为何会有蚀运之气?
还有我床榻下的符咒,秘境里的毒蛟封印松动,是不是都与你有关?"他的声音越来越高,
带着压抑的愤怒和不敢置信。那些被他刻意忽略的细节,
此刻像潮水般涌来:清欢总能在他气运鼎盛时"恰巧"出现,
总能得到他无意中遗落的、沾染了他气息的物件,
总能在他遭遇不顺时安然无恙......清欢的伪装在他连串的质问下彻底崩塌。
她看着凌越眼中的怀疑,忽然笑了,笑得癫狂而怨毒:"是又怎么样?凌越,
你真以为我喜欢你这副自以为是的模样?我喜欢的,是你昆仑墟首座的身份,
是你与生俱来的滔天气运!""苏凝那个蠢货,为你挡了那么多灾劫,耗了那么多自身气运,
却不知道,你这份气运,本就该有能者居之!"她猛地拔高声音,眼中闪烁着贪婪的光,
"我跟着你三年,用《窃运诀》吸你三成气运,才有了今日的修为。等我吸够了,
你以为你还能坐稳这个首座之位?"凌越如遭雷击,踉跄着后退。
他想起三年来的种种:——他修炼遇阻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