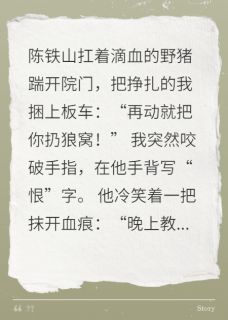
陈铁山扛着滴血的野猪踹开院门,把挣扎的我捆上板车:“再动就把你扔狼窝!
”我突然咬破手指,在他手背写“恨”字。
他冷笑着一把抹开血痕:“晚上教你写别的字。”1灶膛里的火快熄了,
我缩在柴堆旁搓洗全家人的脏衣服。腊月的井水像刀子,手指裂开的口子渗出血丝,
在结冰的木盆里晕开淡红色的涟漪。后妈王金凤的尖嗓子穿透门帘,
像只掐着脖子的老母鸡:“五十斤粮票加两丈布,这赔钱货就归你们!”“哑巴能值这个价?
”人牙子老刘的烟袋锅子磕得啪啪响,“卖去山西挖煤都没人要!”我盯着盆里漂浮的冰碴,
喉咙像被棉花堵着。十年前爹咽气那晚,后妈就是用这盆水洗掉他脸上的血,
转头就把我娘的梳妆盒锁进了炕柜。“哑巴!死哪去了?”王红艳掀帘子进来,
新做的红棉袄晃得人眼疼。她一脚踹翻木盆,冰水泼了我满身:“洗个衣裳磨蹭半天!
”突然揪住我头发往墙上撞,“听说货郎明天来?你敢勾搭他试试!”头皮炸开的疼里,
我摸到灶台边的火钳。还没抡起来,后妈就冲进来掐我大腿根:“反了你了!
”烧火棍雨点般砸在背上,旧伤叠着新伤,疼得眼前发黑。“嚎啊!怎么不嚎了?
”王红艳把玉米糊扣在我头上,“你不是会写字吗?写个‘贱’字给娘看看啊!
”滚烫的粥顺着领口往下淌,烫得胸口**辣的。院门突然被踹开。寒风卷着雪粒子扑进来,
我眯着眼看见个高大的黑影。军靴踩在结冰的地面上咯吱作响,左眼蒙着黑布,
右眼凶得像要吃人。“就她了。”男人的声音像砂纸磨铁。他单手拎起王红艳扔到一边,
牛皮靴踩住我泡在冰水里的手:“五十斤粮票,今晚跟我走。
”王金凤的瓜子撒了一地:“陈铁山!说好是娶我们家红艳——”“改主意了。
”陈铁山从怀里掏出粮票砸在炕桌上,震翻了搪瓷缸。他弯腰掐住我下巴,
独眼里映着我满脸的玉米糊,“这哑巴眼里有火,烧炕带劲。
”王红艳尖叫着扑上来扯我头发:“她连**都不会!姐夫你——”“砰!
”陈铁山反手甩出个东西,王红艳捂着手腕惨叫。地上滚着颗带血的狼牙,
在煤油灯下泛着森白的光。“聘礼。”他扯开旧军大衣裹住我,血腥味混着硝烟气扑面而来,
“咬人的狗,老子亲自教。”我被拽上板车时,王红艳正用剪刀划烂我唯一的棉袄。
陈铁山头都不回,从后腰摸出把剥皮刀甩过去——“啊!”剪刀应声断成两截,
刀尖颤巍巍钉在门框上。“嫁妆。”他甩鞭子抽在驴**上,“少一针一线,老子剁人抵账。
”板车碾过村口的积雪,我看见老槐树下货郎张建国缩着脖子张望。
陈铁山突然掐着我后颈逼我转头,独眼里跳着火苗:“再看?眼珠子给你泡酒。
”天黑透时才到陈家。土坯房孤零零杵在山脚下,檐下挂着风干的狼尸。
陈铁山踹开门把我扔在炕上,炕头堆着的兽夹闪着冷光。“会写字?”他扯开我领口,
粗粝的指腹擦过锁骨下的烫伤——是去年王红艳用火钳烙的。
我蘸着唾沫在炕桌上写:【会算账】“嗬。”陈铁山突然扯开裤腰,露出小腹狰狞的疤,
“会算这个不?”煤油灯爆了个灯花。我摸出藏在袖口的顶针砸向他独眼,
却被他反剪双手按在炕上。粗重的呼吸喷在耳后:“王金凤没告诉你?老子就稀罕带刺的。
”后半夜我发起高烧。恍惚有人撬开我牙关灌药,苦得舌根发麻。
陈铁山的声音忽远忽近:“咽下去。”他掐着我喉结的手像烙铁,“敢吐就办了你。
”月光从窗缝漏进来,照见墙上挂着的**。枪管上刻着歪歪扭扭的“陈”字,
和当年爹那把一模一样。2天刚蒙蒙亮,我就被踹醒了。陈铁山的军靴抵在我腰眼上,
带着晨露的寒气。他单手拎着只还在蹬腿的野兔,血滴在炕席上洇出暗红的圆点。“做饭。
”他把兔子扔我怀里,皮毛上还带着夜露的湿气,“剥不干净皮,今晚就用你补窟窿。
”我摸着炕沿找鞋,却发现脚踝上套着根铁链子——锁扣磨得发亮,另一头钉死在房梁上。
“防贼。”陈铁山蹲在门槛上磨刀,独眼斜睨着我,“尤其是偷汉子的贼。
”灶膛里的火刚点着,院门就被人拍得山响。“哑巴!你给老娘滚出来!
”王金凤的嗓门像锈刀刮锅底。我从窗缝看见她带着三个本家兄弟堵在门口,
王红艳缩在后面哭哭啼啼,胳膊上缠着渗血的布条——是昨天被狼牙划伤的地方。
陈铁山头都不抬,猎刀在磨石上刮出刺耳的声响。“开门。”他突然说。
我拖着铁链子刚拔开门栓,王金凤就一耳光扇过来:“贱蹄子!
才过门就挑唆爷们儿打小姨子?”她指甲里带着泥,在我脸上挠出三道血痕。
“姐、姐夫……”王红艳突然扑向陈铁山,故意把衣领扯开露出半截胸脯,
“我娘听说你爱吃酸菜,特地……”“砰!”陈铁山一枪打飞了她手里的陶罐。
酸菜溅了王金凤满头满脸,他这才掀起眼皮:“说完了?
”王金凤的兄弟王金柱抡起扁担就砸:“敢欺负我们老王家人——”“咔嚓!
”陈铁山单手接住扁担,膝盖往上一顶。槐木棍子断成两截,
他反手就把尖头**王金柱大腿!“啊——”杀猪般的嚎叫声里,
陈铁山踩住他淌血的腿:“带着你家的酸菜滚。
”王金凤突然从兜里掏出个红布包:“陈铁山!你真当我们要饭的?”她抖开包袱皮,
里面赫然是半块玉佩——我娘临终前挂在我脖子上的那块!“想要?拿五十块钱来赎!
”我扑上去抢,却被铁链拽得踉跄倒地。陈铁山一把揪住我后领,独眼里翻着凶光:“哑巴,
这玩意儿值多少?”我蘸着脸上的血在地上写:【我娘的嫁妆】“操。”陈铁山突然笑了。
他从炕席底下抽出沓大团结甩在王金凤脸上:“钱给你。”突然拔枪顶住她太阳穴,
“玉佩留下,舌头也留下。”王金凤的尿骚味弥漫开来。她哆嗦着放下玉佩,
突然指着我尖叫:“这贱种克死亲爹又克亲娘!你等着被她克——”“嗖!
”剥皮刀擦着她耳朵钉在门板上。陈铁山拎起瘫软的王金凤扔出院门:“再登门,
老子用你闺女的天灵盖下酒。”人刚走远,陈铁山就扯开我衣领检查抓伤。
他沾着烈酒的指头按在我伤口上,疼得我直抽气。“哑巴。”他突然掐住我下巴,
“你娘怎么死的?”我盯着地上那半块玉佩——缺口处还沾着黑褐色的陈年血迹。“砰!
”院外突然传来枪响。陈铁山一把将我按在身下,**已经抵在窗框上。透过破洞的窗纸,
我看见货郎张建国鬼鬼祟祟趴在墙头,手里攥着把和王金凤一模一样的烟袋锅子。“瞧见没?
”陈铁山咬着我的耳垂冷笑,“你后妈连姘头都派来了。”他突然扯断我脚上的铁链,
“今晚老子带你看场好戏。”3后半夜的月亮被云啃得只剩个牙印。我趴在陈铁山背上,
闻着他颈间的火药味。他军靴踩在雪上的动静比猫还轻,
腰间别的剥皮刀时不时硌着我大腿根。“瞧见没?”他突然掐了把我**,
指着王金凤家亮灯的西屋,“你后妈在给野男人暖被窝。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纸窗上分明映着两个交叠的人影!
货郎张建国那顶破毡帽就挂在窗棂上,和王金凤的花棉袄挨得极近。
陈铁山从怀里掏出个麻绳套,独眼里闪着狼似的幽光:“待会儿老子捆人,
你负责——”“吱呀——”门开的声音打断了他。王红艳裹着件男人的旧棉袄溜出来,
做贼似的往后山摸。陈铁山猛地按住我后颈:“有意思。
”他粗糙的拇指摩挲着我突突跳的血管,“买一送一。”我们尾随到后山草垛时,
王红艳已经扑进个黑影怀里。月光照出那人满脸麻子——是村里有名的二流子赵三!
“三哥……”王红艳的声音腻得能榨出油,“陈铁山那个杀千刀的……”“嘘,
心肝儿……”赵三的手往她衣襟里钻,“等弄到哑巴她娘的玉佩,
咱就去广州……”我浑身血液瞬间结冰。腰间突然一紧,陈铁山滚烫的胸膛贴上来:“哑巴,
”他咬着我耳垂问,“想先抓哪对?”我还没比划完,他就扯着我往王金凤家冲。
陈铁山踹门的动静像炸了颗雷。炕上赤条条交缠的两人还没反应过来,
货郎就被麻绳套住了命根子!王金凤尖叫着去抓剪刀,
被我抡起顶针砸中太阳穴——这招还是跟陈铁山学的。“哎哟喂!”货郎捂着裤裆滚到地上,
“陈、陈哥饶命……是这娘们儿勾引我……”陈铁山一脚踩住他喉咙,
弯腰捡起炕头那杆烟袋锅子。和我后妈那根并排一比——连竹节上的刻痕都严丝合缝!
“姘头?”他冷笑着把烟袋锅捅进货郎嘴里,“抽啊,怎么不抽了?
”王金凤突然扑向我:“贱种!都是你——”“啪!”陈铁山反手抽得她撞翻尿桶。
黄浊的液体泼了货郎满头满脸,他这才掏出裤腰上别的玉佩——正是我娘那半块!“哑巴。
”陈铁山把玉佩塞进我手里,突然拔出猎刀,“剁手指还是割舌头,你选。
”我们拎着捆成粽子的货郎回家时,天边已泛起鱼肚白。陈铁山把货郎扔进猪圈,
转身就把我按在磨盘上。带着硝烟味的大手撕开我衣领,
他独眼里烧着我看不懂的火:“他摸你哪了?嗯?”我茫然摇头。“装!
”他突然扯下我裤子,粗糙的掌心重重拍在我**上,“昨儿个货郎往你手里塞糖,
当老子没看见?”**辣的疼窜上脊梁。我挣出一只手在地上写:【糖扔了】“扔哪了?
”【喂驴】陈铁山愣了两秒,突然大笑着把我扛上肩头。他踹开屋门把我扔进浴桶,
热水激得我浑身一颤。“洗干净。”他舀起一瓢水浇在我头顶,“待会儿老子亲自检查。
”我正搓着头发,突然听见猪圈传来惨叫。透过窗缝,
我看见陈铁山往货郎裤裆里倒了罐蜂蜜——猪圈里可有他养的十头饿狼似的公猪!“啊!
救命!陈爷饶命……”货郎的嚎叫惊飞了树上的乌鸦。陈铁山回屋时,手里多了个油纸包。
“张嘴。”他捏着我下巴塞进块东西,“老子的糖,敢吐试试。”甜味在舌尖炸开的瞬间,
我尝到了熟悉的陈皮香——是娘生前最爱的老字号。陈铁山突然咬住我肩膀,
声音哑得不成调:“再敢收别人的糖……”他扯开裤腰露出那道狰狞的疤,
“老子让你尝尝什么叫真·吃醋。”4王金凤是踩着晌午的日头来的。
她身后跟着五个本家兄弟,个个拎着锄头扁担,脸上横肉乱抖。王红艳一瘸一拐走在最后,
胳膊上缠着渗血的布条,眼神怨毒得像条毒蛇。“陈铁山!”王金凤一脚踹开院门,
手里举着个破布包,“你媳妇的卖身契还在我这儿!今天要么交人,要么交钱!
”我正蹲在井边洗衣裳,闻言手指一颤。那布包我认得——是爹死后,
后**我按手印的“抵债书”。陈铁山从屋里晃出来,军装敞着怀,露出腰间别着的剥皮刀。
他独眼扫过院门口那群人,突然笑了:“王婶儿,您这是要抢亲?”“少废话!
”王金凤的兄弟王金柱抡起扁担,“要么给一百块钱,要么把这哑巴交出来!
我们老王家的闺女,轮不到你糟蹋!”陈铁山慢悠悠蹲在门槛上,
摸出烟袋锅子点上:“行啊。”他吐了口烟圈,“钱我有,就看你们有没有命拿。
”王金凤使了个眼色,王红艳突然冲上来扯我头发:“**!你偷我嫁妆!”我早有防备,
反手一盆洗衣水泼她脸上!王红艳尖叫着后退,脚下一滑,整个人栽进猪圈——“啊!!!
”惨叫声刺破云霄。陈铁山养的十头公猪饿了一早上,见着活物就拱!
王红艳的花棉袄瞬间被撕成碎片,**上挨了好几口,疼得她哭爹喊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