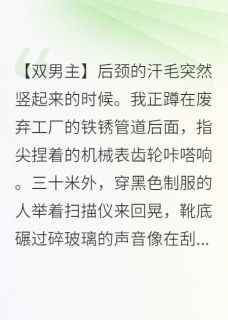
【双男主】后颈的汗毛突然竖起来的时候。我正蹲在废弃工厂的铁锈管道后面,
指尖捏着的机械表齿轮咔嗒响。三十米外,穿黑色制服的人举着扫描仪来回晃,
靴底碾过碎玻璃的声音像在刮我的耳膜。「编号739,确认在这片区域,搜!」
对讲机的电流声刺过来的瞬间,我按下了藏在袖口的按钮。世界突然哑了。
举着扫描仪的人保持着转身的姿势,半张脸埋在阴影里,睫毛上还沾着灰尘。
飞在空中的碎纸片定在离我鼻尖三厘米的地方,甚至能看清上面印着的「时空异常管理局」
徽记——那个把我追得像条丧家犬的鬼地方。这是我第146次用时间暂停术逃命。
喘着气往后退,后背撞在冰冷的铁架上。刚要松口气,鼻腔里突然钻进一股味道。
不是铁锈味,不是灰尘味。是种很淡的雪松香,混着点潮湿的水汽,
像暴雨过后劈开云层的第一缕光。我猛地转头。工厂尽头的破窗户漏进半轮月亮,
月光底下站着个人。白衬衫,黑裤子,袖口卷到手肘,
露出的小臂线条比我见过的任何雕塑都好看。他就那么站在那里,背对着月光,
脸藏在阴影里看不真切,但那双眼睛亮得吓人,正一眨不眨地盯着我。我的血瞬间冻住了。
时间明明还停着。扫描仪还举在半空,黑制服的人保持着迈步的姿势,
连空中的灰尘都没动过。只有他。那个男人抬起脚,一步一步朝我走过来。每走一步,
地上的碎石子就被踩出轻微的声响。在这片死寂里,这声音像重锤敲在我太阳穴上,咚,咚,
咚。我攥紧袖口的按钮,指节发白。这玩意儿的冷却时间还有三分钟,
现在的我跟个没牙的兔子没区别。他走到离我两米远的地方停下了。这时我才看清他的脸。
眉骨很高,鼻梁挺直,嘴唇的弧度有点往下撇,像总带着点不耐烦。但最要命的是眼睛,
瞳仁颜色很浅,盯着你的时候,像有什么东西要从里面漫出来,把你整个人都裹进去。
「时空异常管理局」的追捕名单上,没这号人物。他突然笑了一下。不是那种开怀的笑,
是嘴角轻轻往上挑了挑,眼神里的光却更亮了。然后他朝我倾过身。我下意识地往后缩,
后背死死抵住铁架,冰凉的寒意顺着脊椎爬上来。他离我越来越近。雪松香越来越浓,
几乎要把我整个人腌入味。能感觉到他的呼吸,很轻,像羽毛扫过我的耳廓,
带着点温热的水汽。我僵得像块石头,连呼吸都忘了。他停在离我半臂远的地方。
这个距离太近了。近到我能数清他睫毛的根数,
能看见他瞳孔里映出的我的影子——那个缩在铁架后面,头发乱糟糟,脸上还沾着灰的自己。
他的睫毛垂了垂,离我的脸颊只有两毫米。再近一点,就能扫到我的皮肤。
我的心跳突然炸了,震得肋骨生疼,喉咙发紧,连手心都冒出热汗。这感觉很奇怪,
不是怕的,是另一种更陌生的东西,像有团火在小腹里慢慢烧起来。他没碰我。
只是动了动嘴唇,没发出声音。但我看懂了。
那三个字清清楚楚地落在我眼里——「抓住你了。」我像被烫到一样猛地推开他,转身就跑。
鞋跟踩在地上发出的声音在静止的世界里格外刺耳。跑过那个举着扫描仪的黑制服时,
我甚至能看见他鼻孔里的毛。后面的脚步声跟着追上来了。不紧不慢,像猫捉老鼠。
我拼命往工厂深处冲,那里有个通往后街的排水管道,是我早就看好的逃生路线。
可就在我快要冲到管道口的时候,眼前突然一暗。他居然跑到我前面去了。
背靠着管道口的墙壁,双手插在裤袋里,还是那副懒洋洋的样子。月光从他身后照过来,
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正好铺在我脚边。「跑什么?」这次他开口了,声音跟他的人一样,
带着点冷冽的质感,却又裹着点说不清的温度。我攥着拳头喘气,盯着他的眼睛:「你是谁?
」他没回答,反而朝我伸出手。我的呼吸瞬间屏住。他的手指很长,骨节分明,
指甲修剪得干干净净。那只手停在离我胸口还有一厘米的地方,指尖微微蜷了蜷,
像是在描摹我心脏跳动的位置。雪松香突然变得很浓,浓得让人头晕。
我能感觉到自己的体温在往上飙,脸颊烫得能煎鸡蛋。明明是在逃命,
脑子里却像被什么东西搅乱了,全是他靠近时的眼神,他停在我面前的睫毛,
他带着笑意的嘴唇。「管理局的人?」我咬着牙问,声音有点抖。他突然收回手,
往后退了半步,拉开距离的动作让我莫名松了口气,却又有点空落落的。「你说呢?」
他歪了歪头,月光终于照全了他的脸。那一刻,
我突然想起三年前在管理局的档案库里偷看到的照片。那张被标着「最高机密」的纸上,
印着个跟眼前这人长得一模一样的少年,旁边写着——「时间锚点,状态:失踪」。
而我的机械表突然开始疯狂倒转。齿轮咔咔的转动声里,
那个举着扫描仪的黑制服肩膀动了一下。时间要恢复了。他朝我抬了抬下巴,
眼神里的笑意更深了:「下次见面,记得别跑那么快。」话音刚落,世界猛地活了过来。
扫描仪的滋滋声,脚步声,对讲机的喊叫,所有声音像潮水一样砸过来。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噪音掀得晃了晃,再抬头时,月光底下空荡荡的,
哪还有什么白衬衫的影子。「在那儿!」黑制服的吼声刺过来。我顾不上多想,
一头钻进排水管道。狭窄的空间里满是污水味,可我闻见的,全是那股挥之不去的雪松香。
袖口的按钮还在发烫。刚才他离我那么近的时候,为什么没动手?他说「抓住你了」的时候,
眼里的光到底是什么意思?还有管理局档案库里的那张照片——管道尽头透进微光的时候,
我摸了摸自己的后颈。那里好像还残留着他呼吸的温度,烫得我指尖发麻。原来时间暂停术,
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会用。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能在我暂停的时间里,一步步走向我的人。
而这感觉,比被管理局抓住还要让人害怕。因为我该死的发现,
刚才在他睫毛快要碰到我的时候,我居然没想着反抗,而是在想——他的眼睛真亮啊。
亮得像要把我这146次逃亡里所有的黑暗,都给烧干净。
我在废弃地铁站的长椅上蜷了三天。霉味顺着裤脚往骨头缝里钻,
怀里的压缩饼干只剩最后一块。管理局的搜查队像闻着血腥味的鲨鱼,
我在监控里看见赵秃子那张油光锃亮的脸,他正用靴底碾着我前晚扔掉的矿泉水瓶。
「挖地三尺也要把739找出来,」他对着对讲机狞笑,「找到他,
我让你们每个人都能多活半年。」这就是「新时区」
的规矩——普通人靠管理局发的「时间配额」活,像我这样的时间异常体,活着就是罪过。
地铁隧道深处传来滴水声,规律得像倒计时。我摸出藏在鞋底的刀片,
刚想刮掉胡子上的污垢,身后突然传来布料摩擦的窸窣声。心脏瞬间提到嗓子眼。
我翻身滚到长椅底下,握紧刀片抬头——月光从破洞的天花板漏下来,
正好照在那双擦得锃亮的黑皮鞋上。裤脚挽着,露出的脚踝线条比手术刀还利落。
是那个白衬衫。他居然找到这儿来了。「你就躲在这种地方?」他蹲下来,脸凑近长椅缝隙,
呼吸在冰冷的空气里凝成白雾,「管理局的狗鼻子明天就能嗅到这儿。」
我攥着刀片的手在抖。不是怕,是气。这人明明能在暂停时间里活动,
偏要等我快被抓的时候才出现,像逗弄笼子里的鸟。「滚。」我咬着牙说。他忽然笑了,
伸手往缝隙里探。我的后背瞬间贴紧地面,刀片划破掌心也没知觉。
他的指尖停在离我眼睛三厘米的地方,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指腹泛着淡粉色。「怕我?」
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像羽毛搔过耳膜,「那天在工厂,你可不是这个样子。」
那天在工厂——他睫毛扫过我脸颊的触感突然炸开,我猛地别过脸,后颈的皮肤又开始发烫。
「再靠近一步,我废了你。」我把刀片架在他手腕可能伸过来的方向。他收回手,
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赵秃子抓了老陈。」我的血一下子凉了。
老陈是巷口修表铺的老板,去年冬天我快冻死的时候,他塞给我一碗热汤。
就因为我在他铺子里修过那只装着时间控制器的机械表,现在成了赵秃子手里的筹码。
「他在电视里放了话,」白衬衫的声音沉下来,「今晚八点,你不去城西屠宰场,
老陈就会变成『时间标本』。」我猛地从长椅底下翻出来,刀片抵在他喉咙上。他没躲,
反而微微仰头,露出流畅的下颌线。月光在他锁骨窝里投下一小片阴影,呼吸拂过我的手腕,
带着雪松香的热气。「你怎么知道这些?」我的声音在抖,「你到底是谁?
是不是和他们一伙的?」他的喉结轻轻动了一下,离刀片只有半厘米。「你可以试试相信我。
」这时我的机械表突然开始逆时针转,指针咔嗒咔嗒撞着表壳。
这是时间紊乱的征兆——管理局的「时空雷达」正在靠近。「他们来了。」
他拽着我的手腕往隧道深处跑。他的手心很烫,我像被火燎到一样甩开,却被他反手扣住。
这次他抓得很用力,指骨硌得我生疼。「别松手!」他的声音带着前所未有的急切。
身后的探照灯光柱刺破黑暗,赵秃子的喊叫声顺着隧道滚过来:「抓住那两个异常体!
739和那个叛徒!」叛徒?我踉跄着被他拽进岔路,他突然按住我的后颈把我按在墙上。
阴影里,他的鼻尖离我只有一拳远,睫毛上沾着的灰尘看得清清楚楚。「屏住呼吸。」
他低声说。探照灯从我们头顶扫过,我能听见自己擂鼓般的心跳。他的呼吸洒在我锁骨上,
带着点若有若无的甜味,和那天在工厂的雪松香混在一起,搅得我五脏六腑都在发烫。
管理局的脚步声渐渐远了。他松开手时,我发现自己的指甲深深掐进了他的胳膊。
白衬衫被掐出褶皱,像朵被揉过的云。「为什么赵秃子叫你叛徒?」我盯着他胳膊上的红痕。
他低头笑了笑,突然伸手,指尖在我胸口悬了两秒,像是在确认什么。
「因为我偷了他们最重要的东西。」我的机械表又开始疯转,这次指针直接跳出了表盘,
在空气中划出金色的弧线。他突然抓住我的手腕,把我的手按在他胸口。隔着衬衫,
我能摸到他心脏的跳动。不是匀速的。快一下,慢一下,像个坏掉的钟。「感觉到了?」
他的声音有点哑,「我们是一样的,顾时砚。」这是他第一次叫我的名字。我猛地抽回手,
指尖还残留着他胸腔的温度。隧道深处的滴水声突然变快,像是有人在暗处拧开了水龙头。
「老陈怎么办?」我别过脸不去看他。他从口袋里摸出个青铜小玩意儿,
上面刻着我看不懂的花纹。「拿着这个,屠宰场的监控会在八点十五分失灵三分钟。」
我接过那东西,冰凉的金属硌得手心发疼。「你为什么要帮我?」他后退半步,
转身往隧道黑暗处走。白衬衫的衣角在风里飘了飘,像只断了线的风筝。「因为十年前,」
他的声音混着滴水声传过来,「是你先拉住我的手。」我愣在原地,后颈的皮肤又开始发烫。
十年前的事我早忘光了。管理局的「记忆清洗」技术很厉害,
他们说我是在孤儿院长大的野种,说我天生就该被销毁。可握着那枚青铜玩意儿的手心,
却烫得像揣了团火。当晚七点五十,我站在屠宰场锈迹斑斑的铁门外。
血腥味混着消毒水的味道扑面而来,赵秃子的笑声从里面传出来,像用指甲刮玻璃。
我摸出白衬衫给的青铜玩意儿,突然发现上面刻着的花纹,和我机械表背面的划痕一模一样。
八点整,铁门吱呀一声开了条缝。我握紧刀片钻进去,屠宰车间的灯忽明忽暗,
倒挂的猪肉在钩子上晃,像一个个晃荡的人影。老陈被绑在正中央的铁架上,嘴里塞着布条,
看见我就拼命摇头。赵秃子坐在旁边的不锈钢桌上,手里把玩着注射器,
里面的绿色液体晃得人眼晕。「739,你果然有种。」他把注射器往桌上一墩,「可惜啊,
你今天救不了他,也救不了你自己。」我刚要扑过去,他突然拍了拍手。
两个穿着黑制服的人押着个人从阴影里走出来。白衬衫被打得嘴角淌血,手腕被铁链锁着,
可那双浅色的眼睛还是亮得吓人,正一眨不眨地盯着我。「认识吗?」赵秃子笑得满脸横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