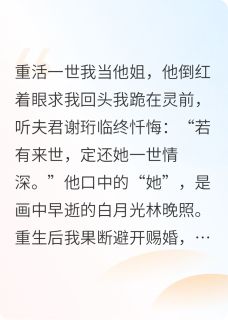
重活一世我当他姐,他倒红着眼求我回头我跪在灵前,听夫君谢珩临终忏悔:“若有来世,
定还她一世情深。”他口中的“她”,是画中早逝的白月光林晚照。重生后我果断避开赐婚,
转身嫁了清贫探花郎。谢珩却红着眼追到我院前:“阿姐,今生我只护你一人。
”他日日以弟弟名义送我最爱的点心,为我挡下所有明枪暗箭。直到暴雨夜,
他浑身湿透砸开我的门:“书房那幅画…你从未看过背面吗?”我嗤笑撕碎他珍藏的画卷,
却见残破绢帛上浮现小字:“重门深锁皆妄念,终悟朝夕即长生——给清晏。
”灵堂里静得可怕,浓重的沉水香也压不住死亡逼近的气息,丝丝缕缕,缠绕着每一寸空气。
我跪在冰冷的蒲团上,膝下寒气如针,直刺骨髓。眼前是紫檀木的棺椁,
厚重的轮廓在长明灯微弱摇曳的光里,沉沉地压着人的心口。谢珩躺在里面,
曾经名动京城的探花郎,后来权倾朝野的尚书令,如今不过是一具行将就木的枯骨。
他的声音从棺椁方向传来,嘶哑,破碎,像被砂纸磨过,
每一个字都耗尽了残存的力气:“清晏……我这一生,给了你……不悔。”他艰难地停顿,
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破风箱般的嗬嗬声,仿佛下一刻就要彻底断裂。“倘若……当年,
我应了陛下的赐婚……是不是……晚照就能活得……久一些?”晚照。林晚照。
这个名字像淬了毒的冰针,猝不及防地扎进我的耳朵,刺透耳膜,直抵心脏最深处。
冰寒瞬间冻结了四肢百骸。“若有来世……”他最后几个字,轻得如同叹息,
消散在令人窒息的香烛烟雾里,留下一个巨大的、令人绝望的空白。若有来世?
他想还谁的情深?灵堂里人影憧憧,低低的啜泣声和压抑的叹息交织成一片模糊的背景音。
我木然地跪着,灵魂像是被抽离了躯壳,悬在高处,冷冷地俯视着这棺椁,这人群,
以及棺椁里那个耗尽我一生情意、却在最后时刻将心彻底剜走的男人。
视线扫过角落肃立的仆从,扫过那些前来吊唁、神情哀戚的官员面孔……最后,鬼使神差地,
落在了灵堂后方通往书房的那扇紧闭的雕花木门上。那扇门,
在我与谢珩整整十年的夫妻岁月里,始终对我关闭着,挂着冰冷的铜锁,
像一个沉默而固执的拒绝。他总说,那里是处理机要重地,杂乱无章,怕我烦扰。此刻,
那紧闭的门扉,却像一只巨大的、嘲弄的眼睛,无声地注视着我这个彻头彻尾的笑话。
心底有个声音在疯狂叫嚣,撕裂了所有强装的平静。凭什么?凭什么我沈清晏十年陪伴,
相夫教子,贤良淑德,换来的却是一个至死都念着别人的夫君?
凭什么我连他书房里藏了什么都不能知晓?一股从未有过的蛮力冲垮了理智的堤坝。
我猛地站起身,膝盖的麻木和刺痛被巨大的愤怒与不甘彻底淹没。
无视周围人惊愕的目光和低声的劝阻,我踉跄着,几乎是扑向那扇门。没有钥匙?
那就用身体去撞!“夫人!使不得啊!”管家惊恐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我充耳不闻,
肩膀狠狠撞在坚硬的门板上,发出沉闷的响声。一下,两下……锁扣发出不堪重负的**。
终于,“哐当”一声巨响,门开了。巨大的惯性带着我向前扑去,我重重摔在冰冷的地砖上,
手掌蹭破,**辣地疼。我顾不上疼痛,挣扎着抬起头。书房里光线昏暗,
陈设一如谢珩生前般一丝不苟。而正对着门的,那面最显眼的墙壁上,
挂着一幅精心装裱的画卷。画中女子一身淡紫色宫装,立于灼灼盛开的桃花树下,回眸浅笑,
眼波流转间,是浑然天成的清贵与明媚。那张脸,曾出现在宫宴的角落里,
也曾出现在谢珩年少时珍藏的诗稿扉页上——已故的昭华公主,林晚照。我认得她,
更认得画上那熟悉的笔触,是谢珩的手笔。每一根线条,每一抹色彩,
都倾注着作画之人难以言喻的情思。目光艰难地挪到画卷的右下角,两行墨色小字,
笔锋遒劲,力透纸背,是谢珩的字迹:“我这一生,无愧于母亲、妻子、君主,
独独对不住你。”“惟愿来生,还你一世情深。”轰隆——仿佛九天惊雷在灵魂深处炸开,
震得我魂飞魄散。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所有的景象都模糊褪色,
只剩下那画上女子明媚的笑靥,和那两行冰冷刺骨的小字,在眼前无限放大、旋转,
最后化为一片吞噬一切的黑暗。“夫人!”“快!夫人晕倒了!”意识沉沦前,
只听到一片惊慌失措的呼喊。……“哗——哗——”瓢泼大雨疯狂地击打着屋顶的青瓦,
又急又密,像是无数只手在拼命捶打。这声音如此真实,如此喧嚣,
将我硬生生从那片令人窒息的黑暗和冰冷中拽了出来。眼皮沉重得像灌了铅,
我费力地睁开一条缝。视线先是模糊一片,只有昏暗的光线轮廓。
鼻尖嗅到的不是灵堂里浓得发腻的沉水香,
而是一种熟悉的、带着一点陈旧木头和干燥尘土气息的味道。这是……我的闺房?
我猛地彻底睁开眼,心脏在胸腔里狂跳,几乎要撞破肋骨。
映入眼帘的是熟悉的茜素红鲛绡纱帐顶,帐子一角垂下的流苏是我亲手打的平安结。
身下是柔软的锦被,触感细腻温暖。我难以置信地转动眼珠,看到熟悉的雕花梳妆台,
菱花铜镜,还有窗边小几上插着几枝半开玉兰的青瓷瓶……这不是梦!我回来了!
回到了十五岁那年,我尚未出阁,尚在闺中的时候!
巨大的震惊和一种近乎狂喜的荒谬感瞬间攫住了我。我挣扎着坐起身,
赤脚踩在冰凉的地板上,几步冲到梳妆台前。铜镜里映出一张脸,尚带着几分未褪尽的稚气,
肌肤光洁饱满,眉眼间是未经风霜摧折的清亮澄澈。
不再是灵堂里那个心如死灰、形销骨立的未亡人沈清晏。是沈清晏,十五岁的沈清晏!
“**!您怎么起来了?还光着脚!”丫鬟春桃端着热水推门进来,看到我站在镜子前,
吓了一跳,连忙放下铜盆跑过来,“您昨儿夜里着了凉,刚发了汗,可不能再受寒了!
快躺下!”她不由分说地把我往床上按,动作麻利地扯过被子把我裹紧。我顺从地躺下,
任由她摆布,脑子里却如同掀起了惊涛骇浪。春桃还在絮絮叨叨:“**您也是,
明知要下雨还去园子里看那几株牡丹,淋了雨可不是要受罪?
幸好夫人让厨房熬了浓浓的姜汤,您喝了发汗,瞧着气色好多了……”是了。我想起来了。
前世确有这一遭。我冒雨去园子里看新开的牡丹,回来就染了风寒,昏昏沉沉病了好几日。
而就在我病中,
改变我命运轨迹的大事发生了——陛下有意为刚刚金榜题名、前途无量的新科探花谢珩赐婚!
前世的我,对那个风姿卓绝、才名远播的探花郎早已心向往之,听闻赐婚的消息,
病中便羞红了脸。母亲试探时,我含羞带怯地默许了。不久后,圣旨降下,
我沈清晏便成了京中人人艳羡的谢家新妇。可如今……灵堂里那剜心刺骨的临终忏悔,
书房里那幅刺眼的画像,那两行冰冷的题字……一幕幕清晰地浮现,如同烧红的烙铁,
狠狠烫在我的心上。痛,尖锐而冰冷。随之而来的,是滔天的恨意,
以及一种前所未有的、冰冷的清醒。“春桃,”我的声音有些沙哑,带着病后的虚弱,
却异常平静,“外面……可是有什么大事发生?”春桃正拧着热毛巾要给我擦脸,
闻言动作一顿,脸上露出几分欲言又止的兴奋,压低了声音:“**您还不知道呢?
外面都传遍了!今儿一早,陛下在麟德殿召见了新科的前三甲,听说……听说陛下龙心大悦,
当场就要给那位风头最盛的谢探花郎赐婚呢!”来了!果然来了!
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又骤然松开。一股冰冷的决绝瞬间取代了所有翻腾的情绪。
前世那场看似风光无限、实则耗尽心血又满盘皆输的婚姻,
那十年小心翼翼却始终捂不热一颗心的卑微,那灵堂里彻底被碾碎的自尊……够了!这一世,
绝不再重蹈覆辙!“赐婚?”我垂下眼睫,遮住眼底翻涌的寒冰,声音平淡无波,
仿佛在谈论一件与己毫不相干的事情,“赐给谁家?”春桃没察觉我的异样,
只当我是病中精神不济,依旧兴致勃勃:“还能有谁?满京城都在猜呢!谢探花那般人才,
家世又好,能配得上他的,必然是顶顶尊贵的闺秀!有人说是安国公府的嫡**,
也有人猜是……”她掰着手指头数着京中适龄的贵女名字。“哦。”我淡淡地应了一声,
打断了她,“替我梳洗更衣吧。”春桃愣了一下:“**,您病还没好利索呢……”“无妨。
”我掀开被子,语气不容置疑,“我要去见母亲。”坐在梳妆台前,
看着铜镜里春桃熟练地为我绾发。乌黑的发丝缠绕在指尖,一如我此刻纷乱又坚定的心绪。
避开谢珩,是第一步。那么接下来呢?难道要再次听从父母之命,
嫁给另一个不知根底、或许同样心有所属的勋贵子弟?不。前世十年困守深宅,
如履薄冰的教训还不够吗?这一世,我要握住自己的命运,哪怕前路荆棘遍布。一个名字,
一个在前世记忆中一闪而过、并未掀起太**澜的名字,毫无征兆地浮现在脑海——许明修。
同样是今科进士,名次远在谢珩之后,二甲末尾,出身寒微,
据说是江南某个小地方的耕读之家。前世我嫁入谢家后,曾在一次宫宴上远远见过他一次。
彼时他刚入翰林院不久,在一众鲜衣怒马的勋贵子弟中显得格外沉默寡言,甚至有些局促,
只安静地坐在角落,与周遭的浮华格格不入。后来隐约听说他因不善钻营,又无背景,
在翰林院坐了几年冷板凳,最终被外放到了某个偏远的州府做通判,从此便再无声息。
一个家世寒微、前途未卜、甚至注定要远离权力中心的微末小官。这样的一个人,
对于一心想要攀附权贵、巩固家族地位的沈家来说,无疑是最差的选择。但对我沈清晏而言,
却可能是跳出前世樊笼、通向另一条道路的唯一契机。他无权无势,
便难以强行束缚于我;他注定外放,远离京城这潭浑水,或许反而能得一方清净。
一个大胆到近乎疯狂的念头,在我心中迅速成形。梳洗停当,我深吸一口气,推开房门。
雨势已稍歇,空气中弥漫着湿润泥土和草木的清新气息。我穿过回廊,
径直走向母亲所居的正院。刚走到门口,
便听到里面传来父亲沈崇山略显激动的声音:“……陛下金口玉言!这是天大的恩典!
谢家那孩子,我是看着长大的,人品才学,样样拔尖!与我们清晏,正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你还有什么可犹豫的?”“老爷,”母亲周氏的声音带着一贯的温和,却也有些迟疑,
“我自然是知道谢家哥儿的好。只是……清晏那孩子,前日淋了雨,病了一场,
我瞧着她精神头不太好。这毕竟是她的终身大事,总得问问她的意思……”“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问什么问?这等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亲事,难道她还能不愿意?
”父亲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不容置喙的权威,“我看你是慈母多败儿!这事就这么定了!
我这就去寻谢尚书商议!”我的心猛地一沉。前世母亲确实问了我的意思,
那时我满心欢喜地默许了。而这一世,我病着,父亲竟要越过我直接定下?
就在父亲话音落下,脚步声朝着门口而来的瞬间,我一步踏了进去,
声音清晰而平稳地响起:“父亲,母亲,女儿不愿意。”厅堂内霎时一静。
父亲沈崇山已经走到了门口,闻言猛地顿住脚步,愕然回头,
脸上那志得意满的笑容瞬间僵住,随即被难以置信的愠怒取代:“你说什么?不愿意?
”母亲周氏也从椅子上站起身,惊疑不定地看着我:“清晏?你……你说什么胡话?
”我挺直脊背,迎着父亲审视的、带着薄怒的目光,清晰地重复:“女儿说,
女儿不愿嫁与谢珩谢探花。”“放肆!”沈崇山脸色铁青,几步走回厅中,指着我,
“这等不知轻重的话也是你能说的?谢家门第显赫,谢珩前程似锦,陛下亲口赐婚!
这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福分!你竟敢说不愿意?你莫不是病糊涂了?”“女儿清醒得很。
”我垂下眼睫,掩去眸中翻涌的情绪,声音依旧平静,却带着一种不容动摇的决绝,
“女儿只是觉得,自己福薄,恐担不起谢家这般高门贵第,更配不上谢探花那般人中龙凤。
强扭的瓜不甜,与其日后……相看两厌,不如一开始便求个清净自在。
”“你懂什么强扭的瓜?!”沈崇山气得来回踱步,“自古婚姻大事,哪个不是父母之命?
讲究的是门当户对!谢家哪点不好?谢珩哪点配不上你?你倒是说说,你想嫁个什么样的?
难不成要嫁个贩夫走卒才叫清净自在?”空气凝滞得如同结了冰。母亲周氏担忧地看着我,
又看看暴怒的丈夫,欲言又止。我缓缓抬起头,目光掠过暴跳如雷的父亲,
落在他身后博古架上那个价值不菲的官窑瓷瓶上,仿佛在衡量什么。然后,我轻轻开口,
吐出一个让满室震惊的名字:“女儿听闻,今科进士中,有一位许明修许大人,
为人端方勤勉,学识亦是不凡。女儿……愿意。”“许明修?
”沈崇山像是听到了天底下最荒谬的笑话,先是愕然,随即爆发出一阵怒极的冷笑,“哈!
那个寒门出来的穷酸?二甲吊车尾?在翰林院连个泡都冒不出来的小角色?清晏!
你真是病得不轻!我看你是存心要气死我!”“父亲息怒。”我屈膝,深深一礼,
姿态放得极低,语气却寸步不让,“女儿并非意气用事。谢家固然显赫,然树大招风,
女儿性情愚钝,恐难应对其中复杂。许大人出身清寒,但品性高洁,女儿与他,
或可求得一份平实安稳。女儿心意已决,望父亲母亲成全。”我抬起头,
目光平静地迎上父亲几乎要喷火的眼睛,“若父亲执意要女儿嫁入谢家,女儿唯有一死,
以全父亲门楣颜面。”最后一句,我说得很轻,却带着玉石俱焚的寒意。“你!
”沈崇山被我最后那句决绝的话噎得一口气差点没上来,指着我,手指都在发抖,
脸色由红转白,胸膛剧烈起伏着。
他显然被我从未有过的强硬和这种“自甘堕落”的选择彻底激怒了。“老爷!老爷您消消气!
”母亲周氏吓得脸色发白,慌忙上前扶住他,一边拍抚他的胸口,一边焦急地看向我,
“清晏!快给你父亲认错!你这孩子,怎么尽说些糊涂话!
那许明修……如何能与谢家公子相提并论?”我没有认错,只是沉默地跪了下去,
脊背挺得笔直,无声地表达着绝不妥协的姿态。厅堂里只剩下父亲粗重的喘息声。
他死死瞪着我,那目光像是要将我生吞活剥。时间一点点流逝,空气沉重得几乎令人窒息。
不知过了多久,沈崇山猛地一甩袖子,发出一声怒极的冷哼:“好!好!好一个平实安稳!
好一个心意已决!我沈崇山就当没生过你这个不知好歹、自甘**的女儿!”他指着门外,
声音因为极致的愤怒而微微发颤:“滚!你给我滚回你的院子去!没有我的允许,
不准踏出房门一步!我倒要看看,你选的那条‘平实安稳’的路,能走到几时!”“老爷!
”母亲惊呼。我心中却是一松。父亲虽怒,但这话里的意思,已是默许了我的忤逆,
放弃了与谢家联姻的打算。至少,他不会再强逼我嫁入谢家。“女儿谢父亲成全。
”我对着他再次叩首,声音平静无波。然后站起身,
不再看父亲铁青的脸色和母亲担忧的眼神,转身,一步一步,
稳稳地走出了这令人窒息的厅堂。身后,传来父亲暴怒之下砸碎茶盏的刺耳声响。
接下来的日子,我如父亲所言,被禁足在自己的小院里。外面关于赐婚的风波如何喧嚣,
谢家如何反应,我一概不知,也不想去打听。春桃偶尔出去,回来时脸色总是怪怪的,
欲言又止,我只作不见。心既已死过一次,又有什么流言蜚语能再伤我分毫?半月后,
一个消息还是不可避免地传入了我的小院——陛下最终并未直接赐婚,
而是尊重了谢珩本人的意愿。而谢珩,竟婉拒了陛下的美意,只言“功业未立,不敢成家”,
此事便就此搁置了。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正在窗前临帖。笔尖悬在宣纸上方,
一滴浓墨无声坠落,迅速在雪白的纸面上晕染开一大团丑陋的墨迹。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那团墨迹,像看着自己前世那被彻底染污的人生。搁下笔,
将整张纸揉成一团,丢进了废纸篓。又过了几日,一个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消息传来,
像一块巨石投入看似平静的湖面——陛下金口玉言,为我沈清晏和那位寒门进士许明修,
赐婚了!据说,是父亲沈崇山在朝堂上,当着陛下的面,涕泪俱下地陈情。言道小女清晏,
自幼体弱,性情怯懦,难当高门宗妇之责,唯恐辜负圣恩,亦恐耽误谢探花前程。
小女心慕清流,感念寒门学子奋发之不易,尤其钦佩今科进士许明修之勤勉端方。
恳请陛下垂怜,全小女一份安于清贫、相守于微末的心愿。父亲这一招,堪称以退为进,
狠辣至极。他既全了谢家和陛下的颜面,
又坐实了我“体弱”、“怯懦”、“难当重任”的“事实”,
彻底绝了我攀附其他高门的可能。同时,将我与许明修绑在一起,
一个“心慕清流”、“安于清贫”的名声扣下来,既是成全,
更是将我推入了一个无法回头的境地。沈家嫡女,自甘下嫁寒门,从此,我与沈家,
某种程度上,算是被切割了。父亲这是在用最体面的方式,惩罚我的忤逆,
也彻底斩断我这颗“废棋”与家族更进一步的关联。当春桃带着哭腔告诉我这个消息时,
我只是淡淡地“嗯”了一声,继续修剪着窗台上那盆茉莉的枯枝。
指尖传来枝叶被剪断的细微脆响。也好。远离这泥潭般的富贵牢笼,去那清贫之地,
或许真能求一个“安稳”。至于许明修……一个陌生人罢了。这一世,情爱于我,
早已是穿肠毒药,不敢再碰。所求的,不过是一隅容身之地,一份不必看人脸色的自由。
婚期定在三个月后。父亲果然说到做到,虽未再苛责于我,
但沈府上下对我的态度明显冷淡疏离了许多,
连下人们的眼神都带着几分古怪的怜悯和隐隐的轻视。嫁妆单子送过来时,
春桃气得眼圈都红了。上面所列之物,远不及沈家嫡女应有的规制,寒酸得可怜。
几匹寻常绸缎,几套普通的金银头面,一些压箱底的银子,再无其他。
沈家这是明摆着要让我“安于清贫”了。我平静地收下单子,反倒安慰春桃:“够用就好。
多了,反而是累赘。”心里盘算着,等到了任上,或许可以凭自己前世打理中馈的手艺,
开个小铺子,赚些体己。靠人,终究不如靠己。日子在禁足的平静与暗涌的流言中滑过。
眼看婚期将近,沈府开始为这桩颇受议论的婚事做最后的准备,
府里上下透着一股说不出的沉闷。这日午后,难得阳光晴好。
我被允许在府中后花园的小范围内走动散心。沿着熟悉的九曲回廊慢慢踱步,
看着园中熟悉的景致,前世种种,恍如隔世。行至假山旁的凉亭附近,前方垂花门处,
一个熟悉得令我灵魂都为之战栗的身影,毫无预兆地闯入了视线。
他穿着一身雨过天青色的锦缎长袍,身姿挺拔如修竹。阳光落在他清俊的侧脸上,
勾勒出温润的轮廓。他正微微低头,与引路的管家说着什么,姿态是一贯的从容矜贵。
不是谢珩,又是谁?浑身的血液仿佛瞬间凝固,又在下一刻疯狂地逆流冲上头顶。
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狠狠攥住,几乎停止了跳动。前世的恩爱缠绵,临终的锥心之语,
书房里那幅刺目的画像……无数画面碎片般涌来,尖锐地切割着我的神经。几乎是本能地,
我猛地转身,想要逃离。动作太急,裙裾绊住了脚,身体不受控制地向前踉跄了一步。
“**小心!”身后的春桃惊呼。这一声,惊动了垂花门边的人。谢珩闻声抬起头,
目光穿过回廊,精准地落在我身上。四目相对的瞬间,我清晰地看到他眼中闪过极度的震惊,
随即是难以置信的狂喜,那光芒亮得惊人,几乎要灼伤我的眼睛。但只是一刹那,
那狂喜便被一种更深沉、更复杂的情绪所覆盖——浓烈的痛楚、深切的悔恨,
还有一种近乎绝望的……祈求?他几乎是下意识地向前迈了一步,似乎想朝我走来,
嘴唇微动,像是要唤我的名字。“清……”那熟悉的音节刚冒出一个模糊的气音,
便被他自己硬生生扼住了。他猛地停住脚步,像是被无形的鞭子抽打了一下,脸上血色褪尽,
只剩下一种近乎脆弱的苍白。他死死地看着我,那眼神复杂得如同暴风雨前的深海,
翻滚着惊涛骇浪,却又被他用尽全力压抑着,最终化为一片深不见底的沉寂。
他最终没有上前,也没有再发出任何声音。只是站在原地,隔着十几步的距离,
隔着回廊雕花的栏杆,隔着前世今生的爱恨纠葛,沉默而痛苦地注视着我。那目光沉甸甸的,
仿佛有千钧之重,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前世,他临终时看着画像的眼神,大概也是如此吧?
只是对象,换成了我。心底的冰层骤然加厚,将那瞬间涌起的复杂情绪彻底冻结。
我面无表情地转开视线,仿佛只是看到了一个无关紧要的陌生人。扶住春桃的手臂,
稳住身形,然后挺直脊背,头也不回地朝着与来时相反的方向,快步离去。
脚步踩在青石板上,发出清晰而急促的回响。我能感觉到,身后那道沉痛的目光,
一直如影随形,直到我转过回廊的拐角,彻底消失在他的视线里。那目光,
比前世灵堂的忏悔,更令人心寒。婚礼的日子终究还是到了。没有十里红妆,
没有喧天的锣鼓和满城的艳羡。沈府门前冷冷清清,只有几辆装饰着简单红绸的马车候着。
我的嫁妆被草草抬上车,显得寒酸而局促。前来迎亲的,只有许明修的几位同窗好友,
穿着半新不旧的长衫,脸上带着几分拘谨和好奇。母亲周氏在房内为我梳头,
动作缓慢而沉重,眼圈一直是红的。
她絮絮叨叨地说着保重身体、孝敬公婆、体贴夫君之类的叮嘱,声音哽咽。
父亲沈崇山自始至终没有露面。盖上红盖头的那一刻,眼前只剩下一片刺目的红。
春桃搀扶着我,一步步走出这个生活了十几年的闺阁,走出压抑的沈府大门。
没有兄弟背我上轿的环节,我踩着矮凳,
自己弯腰钻进了那顶半旧的、毫无喜庆可言的花轿里。轿帘落下,
隔绝了外面所有或好奇或怜悯的目光。轿子被抬起,晃晃悠悠地前行。
听着外面稀疏的鞭炮声和路人模糊的议论,我心中一片死寂的平静。没有对新婚的期待,
没有对未来的憧憬,只有一种尘埃落定、终于逃离樊笼的疲惫和解脱。许明修的家远在江南,
他此刻不过是个小小的翰林院编修,俸禄微薄,
在京城赁了一处极为偏僻简陋的小院作为婚房。花轿在七拐八绕的窄巷里行了许久,
才终于停下。没有热闹的迎亲仪式,没有喧嚣的宾客。
小院门口贴着两个小小的、略显歪斜的“囍”字,算是唯一的点缀。
许明修穿着一身崭新的靛蓝色长衫,站在门口。当轿帘掀开,我搭着春桃的手下轿时,
他迎了上来。盖头遮着视线,我只能看到他靛蓝的袍角和一双洗得发白的布鞋。他伸出手,
似乎想扶我,又有些犹豫地缩了回去,显得有些手足无措。“沈……沈**,请……请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