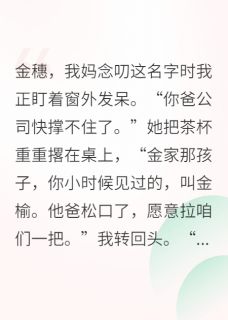
金穗,我妈念叨这名字时我正盯着窗外发呆。“你爸公司快撑不住了。
”她把茶杯重重撂在桌上,“金家那孩子,你小时候见过的,叫金榆。他爸松口了,
愿意拉咱们一把。”我转回头。“条件?”“联姻。”她吐出这两字,像吐掉一粒硌牙的沙,
“三年协议,白纸黑字,帮咱家渡过难关。三年后,各走各路。”“行。”我答得干脆。
感情?那玩意儿能当饭吃?能填上我爸公司那窟窿?不能。那就嫁。见金榆那天,
约在高尔夫球场旁边的咖啡馆。落地窗外绿茵茵一片,看着都贵。他推门进来,身高腿长,
穿着件简单的白T恤,袖子挽到胳膊肘,露出的手臂线条利落。脸是好看的,
但眼神像隔着一层磨砂玻璃,看不真切情绪。礼貌、周到,挑不出错,也感觉不到温度。
“金穗?”他拉开我对面的椅子坐下,声音低沉平稳。“金榆。”我点点头。名字是知道的,
脸……模模糊糊有点印象,像隔了很多层毛玻璃看旧照片。听我妈提过,小时候两家走得近,
后来他爸生意越做越大,搬去了城东,我们留在城西,十几年没正经来往。这“竹马”,
水分太大。“协议你看过了?”他开门见山,递过来一个薄薄的文件夹。我接过来,没翻开。
“大致清楚。三年,互不干涉私生活,对外扮演恩爱夫妻,帮我家度过眼前难关。时间一到,
好聚好散。”“嗯。”他指尖在桌面轻敲了一下,“婚后住我城西的公寓。地方够大,
有各自的独立空间。”“可以。”正合我意。“还有什么要求?”我想了想。“别带人回家。
我也不会。”他抬眼,那层磨砂玻璃似乎晃了一下。“当然。”“合作愉快。
”我端起面前的柠檬水,朝他举了举。他拿起他的水杯,轻轻碰了一下我的杯沿。
“合作愉快。”玻璃杯相撞,发出清脆的一声响。像某种契约落定的信号。没有婚礼,
没有戒指,只有两份签好字的协议。我和金榆,两个名字并排躺在纸上,
成了法律关系上的夫妻。搬进金榆的公寓,像住进一个设计精良的酒店套房。
黑白灰的主色调,干净得能照出人影的地板,巨大的落地窗映着城市冰冷的轮廓线。
我的房间在走廊另一头,和他的主卧遥遥相对。我们严格遵守协议。早上在餐厅碰见,
餐桌上摆着阿姨做好的早餐。“早。”他翻着财经报纸,头也不抬。“早。
”我拉开椅子坐下,端起牛奶。晚上他应酬回来,偶尔在客厅遇上。“还没睡?”“嗯,
看会儿剧。”“早点休息。”“你也是。”对话精简得像发电报。客气,疏离,
井水不犯河水。他忙他的商业帝国,我拿着他给的副卡,继续经营我那间小小的花艺工作室。
生活像两条平行线,只在必要的时候短暂交汇一下。
协议里最重要的一条:对外扮演恩爱夫妻。第一次陪他出席慈善晚宴,
我穿着租来的昂贵礼服,浑身不自在。水晶吊灯晃得人眼花,
空气里混杂着香水味和虚伪的寒暄。金榆的手臂自然地环过我的腰,掌心温热地贴在我腰侧。
我身体瞬间绷紧。“放松点。”他微微低头,气息拂过我耳廓,声音压得很低,
只有我能听见,“金太太。”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放松靠在他身侧,
脸上挂起练习了无数次的、温婉得体的笑容。他带着我穿梭在衣香鬓影里,
向这个总那个董介绍:“这是我太太,金穗。”他的手臂坚实有力,像一道安全的屏障,
又像一个温柔的囚笼。我挽着他,指甲几乎要掐进自己掌心,脸上却笑得无懈可击。
有人夸我们郎才女貌,他低头看我,眼神专注得几乎能溺死人,手指在我手背上轻轻摩挲。
“谢谢李总,能娶到穗穗,是我的福气。”他说得情真意切。我配合地垂下眼睫,
恰到好处地流露出一点羞涩。心里却在冷笑,奥斯卡真该给他颁个小金人。
应付完一波又一波的人,脸都快笑僵了。终于找了个空隙溜到露台透气。晚风吹在脸上,
才觉得活过来一点。刚松口气,旁边阴影里传来一声嗤笑。“演得挺累吧?
”一个穿着骚包酒红色西装的男人端着香槟晃过来,眼神轻佻地在我身上扫,
“金榆这‘恩爱夫妻’的戏码,也就骗骗外人。圈子里谁不知道是协议联姻?
”我认出他是某个地产商的儿子,出了名的纨绔。“这位先生,”我转过身,
脸上那点羞涩荡然无存,只剩一片冰凉的客气,“我们认识吗?”他一愣。
“不认识就对我太太品头论足,”金榆的声音从我身后响起,冷得像淬了冰的刀锋。
他几步走过来,高大的身影将我完全笼罩在他身后,隔绝了那道令人不适的目光。“周少,
管好自己的嘴。”金榆的语气平静,却带着无形的压迫感,“金太太不是你能议论的人。
”姓周的脸色变了变,挤出一个难看的笑:“开个玩笑,金总别介意。
”“这个玩笑一点也不好笑。”金榆没看他,直接揽住我的肩,带着我转身离开,
“以后这种场合,离这种人远点。”他低声对我说,语气不容置疑。回到灯火辉煌的大厅,
他环在我肩上的手没有松开,反而收得更紧了些。**着他,
能闻到他身上清冽的雪松气息混着淡淡的酒味。刚才那一刻他骤然爆发的气势,
和他平时那副冷静自持的样子判若两人。那天晚宴后,
公寓里的气氛似乎有了一点点微妙的变化。很细微,像平静湖面投入了一颗极小的石子,
涟漪几乎看不见,但确实存在。比如早上在餐厅。阿姨端上煎蛋和牛奶。我拿起杯子,
发现他面前的咖啡杯空了。“要咖啡吗?”我下意识地问了一句。问完自己都愣了一下。
这超出了“协议”里必要的交流范畴。他翻报纸的手顿了顿,抬眼看了我一下。“好,谢谢。
”我起身去厨房,给他重新倒了一杯。黑色的液体注入白瓷杯,热气氤氲。“谢谢。
”他把杯子接过去时,指尖不小心碰到了我的手背。很短的一瞬,温热的触感。
我们都若无其事地移开视线。餐桌上只有刀叉碰撞盘子的细微声响。又比如某个周末下午。
我在客厅地毯上摊开一堆花材,准备工作室下周的样品。玫瑰、郁金香、尤加利叶散落一地,
空气里弥漫着浓郁的花香。他难得没有去书房加班,坐在沙发上看一本很厚的原文书。
我正纠结一个花环的配色,拿着几支香槟色玫瑰和浅紫色桔梗比划。
“试试加一点白色的满天星。”他突然开口。我抬头看他。他依旧看着书,
好像刚才那句话不是他说的。我犹豫了一下,抽了几支细碎的白色满天星点缀进去。果然,
跳跃的白色瞬间点亮了整个花环,层次感立刻出来了。“……嗯,好看多了。”我小声说。
他翻过一页书,没抬头,唇角似乎极轻微地向上弯了一下。第一次爆发冲突,是因为我妈。
她老人家似乎完全代入了“丈母娘”的角色,三天两头打电话来“关心”我们的生活,
话里话外催促着抱外孙。我烦不胜烦,每次都敷衍过去。那天她又打来电话,
我在工作室忙着插一个大型花艺装置,手机开的外放。“穗穗啊,你跟小榆到底怎么回事?
这都结婚快一年了,一点动静都没有?是不是你太任性了,不懂得体贴老公?我跟你说,
女人啊……”“妈!”我打断她,声音带着压不住的火气,“我的事你别管行不行?
我们好得很!忙着呢,挂了!”我烦躁地按掉电话,看着眼前刚插好的花,
怎么看怎么不顺眼。晚上回到公寓,金榆难得比我早回来,坐在客厅看新闻。气压有点低。
“你跟你妈说什么了?”他放下遥控器,语气平静,但眼神有点沉。“什么说什么?
”我换了鞋,没好气地问。“她下午给我打电话,”他看着我,“声泪俱下,
说我是不是对你不好,让你受了委屈,所以才不愿意……要孩子。”我脑袋嗡的一声,
血全涌到脸上。是气的,也是难堪。“她怎么这样!我去跟她说清楚!”“你怎么说清楚?
”他站起身,走近几步,“告诉她我们是协议婚姻?告诉她三年一到就分道扬镳?金穗,
当初签协议的时候,明确写了不能让双方父母知情,以免节外生枝。你忘了?
”他站在我面前,离得很近。他身上那股清冽的气息此刻带着压迫感。“我没忘!
”我梗着脖子,心里的委屈和烦躁像野草一样疯长,“是我逼你签的吗?金榆!
是你自己答应的!现在倒怪起我来了?我妈她烦人,我有什么办法?
你以为我愿意被她这样追问?我愿意当个生孩子的工具人吗?”话一出口,我就有点后悔。
太难听了。可看着他没什么表情的脸,那股邪火怎么也压不下去。他沉默地看着我,
眼神深得像不见底的寒潭。客厅里只听到我们俩有些粗重的呼吸声。半晌,他才开口,
声音比刚才更低沉:“我从没把你当工具人。”他顿了顿,似乎在斟酌字句,
“协议是我签的,责任我担。但你妈那边,请你也处理好。我不想再接到这种电话,
更不想让老人家无谓担心。”他说完,没再看我,转身径直走向书房。“砰”的一声轻响,
书房门关上了。我一个人站在空旷的客厅里,巨大的落地窗外是璀璨的城市灯火,
却照得我心里一片冰凉。那股无名火泄了,只剩下疲惫和一种说不清的酸涩。他最后那句话,
像根细小的刺,扎进了肉里。冷战持续了几天。我们依旧维持着表面的客套,
但空气里像绷着一根看不见的弦。早上餐厅相遇,连最简单的“早”字都省了,
只剩下沉默的咀嚼声。晚上他回来得更晚,我则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对着电脑屏幕发呆,
或者一遍遍修剪那些无辜的花枝。工作室的订单也出了问题。一个合作很久的酒店突然通知,
下季度的所有宴会花艺换人了。负责人支支吾吾,只说上面换了喜好。我直觉不对劲,
托人打听了一圈,才隐约知道是有人“打了招呼”。
能在这个圈子里轻易掐断我这条小虾米生意的,还能有谁?怒火“腾”地一下烧起来。
协议归协议,生意归生意!他凭什么动我的工作室?就因为我跟他吵了一架?这算什么?
打压报复?我抓起车钥匙冲回公寓。阿姨说他在书房。我连门都没敲,直接推门进去。
他坐在宽大的书桌后,正在开视频会议,屏幕上好几个西装革履的头像。听到动静,
他抬眼看到是我,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对着麦克风说了句“稍等”,然后按了静音。
“有事?”他摘下眼镜,捏了捏眉心,语气带着被打断工作的不悦。“是你干的?
”我把包甩在旁边的沙发上,声音因为愤怒有点抖,“‘初语’酒店的单子,
是不是你搞的鬼?”他看着我,眼神里闪过一丝疑惑,随即是了然。“那个花艺单子?
”“对!除了你金大总裁,谁还有这个本事,一句话就让别人换掉合作方?”他靠在椅背上,
手指在光滑的桌面轻轻敲击着,那眼神像是在审视一个无理取闹的孩子。“金穗,在你心里,
我就这么闲?闲到要去插手你那间小花店的生意?”“不然呢?
”我被他这副置身事外的样子彻底激怒,“除了你还有谁?就因为我妈那通电话?
因为那天我跟你吵了架?金榆,生意场上的手段用在我身上,有意思吗?”他脸色沉了下来。
“首先,我没有那么无聊。其次,”他站起身,绕过书桌朝我走过来,步伐不快,
却带着一种无形的压力,“就算我要动你,也不会用这么低级的手段。直接断了你的资金流,
或者让你的房东不再续租,不是更干脆?”他的话像一盆冰水,兜头浇下。
我看着他近在咫尺的脸,那双深邃的眼睛里没有一丝玩笑的成分。一股寒意从脚底窜上来。
是啊,他真要动我,何必绕这么大弯子?“那……那是谁?”我的气势瞬间弱了下去,
声音也干涩起来。他没回答,只是深深地看着我,眼神复杂。有无奈,有探究,
似乎还有一丝……疲惫?他离我很近,我能看清他眼底细微的血丝,
和他身上淡淡的烟草味——他最近抽烟似乎变多了。“你工作室的事,我会让人去查清楚。
”他最终开口,声音缓和了一些,“但你记住,金穗,我金榆要对付谁,从来光明正大。
背地里使绊子,跌份儿。”他说完,没再看我,转身走回书桌后,重新戴上眼镜,
按开了静音键。“抱歉,继续。”他对着屏幕说,语气恢复了一贯的沉稳冷静,
仿佛刚才那场冲突从未发生。我站在原地,像个闯了祸又不知所措的傻子。
书房里只剩下他低沉流利的英文汇报声。巨大的落地窗映出我失魂落魄的影子。
我默默地退出书房,轻轻带上了门。心口堵得厉害,比刚才更难受。误会他了。而且,
好像……又搞砸了。几天后,金榆的助理小林,一个看起来就很干练的年轻男人,
亲自来我工作室送了一份文件。“金太太,这是酒店那边新负责人的联系方式,
还有一份补充协议。”小林笑容得体,“金总打过招呼了,
以后贵工作室是他们的优先合作方。”我翻开那份补充协议,条款对我非常有利,
近乎是保障性的合作。压在心头的石头一下子松动了,
随之而来的是更深的懊恼和一点点难言的感激。“麻烦你了林助理,也……替我谢谢金榆。
”我有点别扭地说出他的名字。小林笑笑:“金总说,举手之劳。另外,”他顿了顿,
“之前那件事,有点眉目了。是金总一个表叔那边的人做的,
大概是想通过给您制造点小麻烦,在金总那里讨点人情或者试探点什么。金总已经处理了,
请您放心。”果然。我捏着那份协议,指尖有点发凉。这个圈子,
真是一点风吹草动都能引来秃鹫。“我知道了,谢谢。”小林走后,我看着窗外车水马龙,
心情复杂。他帮我解决了麻烦,甚至没等我开口。而我,不仅误会他,
还像个刺猬一样扎了他一身。那晚在书房,他眼里的疲惫,是不是也有我的“功劳”?
晚上回到公寓,难得看到他在客厅,没看书,也没看新闻,只是站在落地窗前,
手里端着一杯水。听到我开门的声音,他转过身。客厅只开了几盏氛围灯,光线有些暗。
他穿着家居服,少了几分白天的凌厉,轮廓显得柔和了些。“回来了。”他开口,
声音很平常。“……嗯。”我换了鞋,把包放下,有点局促地站在那里。
道歉的话在喉咙里滚了几滚,却像卡了壳。“工作室的事,”他朝我这边走了两步,
停在沙发边,“解决了?”“解决了。”我点头,深吸一口气,终于抬起头看向他,
“那个……上次的事,对不起。”声音不大,但足够清晰,“我不该没弄清楚就冲你发火,
也不该……说那些难听的话。”他看着我,没说话。
窗外的霓虹灯在他侧脸上投下明明暗暗的光影,看不清他的表情。沉默在蔓延,
每一秒都像被拉长了。就在我以为他不会回应,准备灰溜溜回房间时,他开口了。
“我妈下午也给我打电话了。”他忽然说,语气有点无奈,“旁敲侧击,
问我们是不是吵架了,说你最近心情不太好。”我一怔。他抬手揉了揉眉心,
那个动作透露出一点真实的倦意。“所以,扯平了。”扯平了?我有点懵。他放下水杯,
朝我这边又走近一步。距离拉近,我能闻到他身上清爽的沐浴露味道。
“协议里没写要应付彼此父母的催生。”他看着我的眼睛,很认真地说,“但既然签了字,
演了这场戏,这些麻烦,就得一起担着。”他的目光沉静,像夜色下的深海。没有指责,
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一起担着。这四个字,像一颗小石子,
轻轻投进我心里那片因为协议而刻意冰封的湖面,漾开了一圈细微的涟漪。“嗯。
”我听见自己应了一声,声音有点哑,“知道了。”他没再多说什么,转身走向厨房。
“阿姨熬了汤,喝点?”“好。”那晚,我们一起坐在餐桌旁,沉默地喝着汤。
气氛不再像之前那样紧绷,空气里流动着一种奇异的、微妙的平静。汤的热气氤氲上升,
模糊了彼此的轮廓。那场争吵和误会过后,公寓里似乎进入了一种奇特的“休战期”。
我们不再刻意回避交流,但也绝不越界。像两个摸索着重新划定安全距离的陌生人,
带着点小心翼翼的试探。某个周六下午,我抱着一大箱刚到的进口花材吭哧吭哧进门。
箱子太重,一个没抱稳,眼看就要砸到脚上。斜刺里伸出一只手,稳稳地托住了箱子底部。
“我来。”金榆的声音在头顶响起。他不知何时从书房出来了,穿着简单的灰色卫衣,
袖子挽到手肘。“谢谢。”我松开手,松了口气。
他轻松地把箱子搬到我的工作台(客厅靠窗被我霸占的一角)放下。箱子有点大,
放在地上不稳当。“放这儿吧。”他环顾了一下,把旁边一个看起来不太重的矮几挪开一点,
腾出位置把箱子放稳。“这个矮几……”我刚想说那是阿姨喜欢的,平时上面摆着花瓶。
“先放旁边,待会儿挪回去。”他打断我,拍了拍手上的灰,“买的什么?这么沉。
”“厄瓜多尔的玫瑰,还有肯尼亚的绣球,杆子粗。”我蹲下去拆箱子。他也跟着蹲下来,
看我拆包装。保鲜纸和泡沫纸窸窸窣窣地响。“颜色不错。
”他看着露出来的深红玫瑰和蓝紫色绣球花苞,评价了一句。“嗯,这批品质好。
”我小心地把花拿出来检查。一支玫瑰的硬纸壳保护套有点松,花头歪了。
我下意识地“啧”了一声。“给我。”他伸出手。我疑惑地递给他。
只见他用手指捏住花茎下端,另一只手轻轻扶正花头,然后利落地把松掉的保护套重新裹紧,
卡好。动作居然挺熟练。“你……会弄花?”我有点惊讶。他站起身,把手插回卫衣口袋,
表情淡淡的:“以前在国外读书,打工的花店干过几个月。”他顿了顿,补充道,
“糊口而已。”说完,他转身朝书房走去,留下我蹲在一地鲜花和包装材料里,
看着他挺拔的背影消失在门后。糊口?金家大少爷需要去花店打工糊口?这信息量有点大。
心里那点好奇,像被羽毛轻轻搔了一下。又过了些日子,我爸打电话来,
语气是前所未有的轻松和喜悦,说公司最大的一个坎儿终于过去了,资金链续上了,
新项目也顺利启动。他在电话那头一个劲儿地说“多亏了小榆”,“这孩子有本事”。
挂了电话,我看着窗外明晃晃的阳光,有点恍惚。协议里最重要的一条,他完成了。
我们家的危机,解除了。晚上金榆回来,我破天荒地没窝在房间,坐在客厅沙发上。
茶几上放着一杯刚倒好的温水——给他倒的。他进门,看到我,脚步顿了一下。
目光扫过茶几上的水杯,又落回我脸上,带着询问。“我爸刚打电话,”我开口,
声音还算平静,“公司的事,他说谢谢你。”他换了鞋走过来,拿起那杯水喝了一口。“嗯,
应该的。”语气没什么波澜,仿佛只是处理了一件再普通不过的公事。
“协议……”我看着他放下水杯,斟酌着用词,“我爸那边……算是稳住了。你答应的事,
做到了。”他抬眼看我,眼神深邃。“协议还有一年半。”我心里咯噔一下。他是在提醒我,
时间还没到,戏还得继续演。“我知道。”我移开视线,手指无意识地抠着沙发边缘,
“就是……谢谢你。”他没再说什么,只是“嗯”了一声,转身去了餐厅。
阿姨已经摆好了饭菜。那顿饭吃得格外沉默。我脑子里乱糟糟的。危机解除,本应高兴。
可“协议还有一年半”这句话,像一根冰冷的针,
扎破了这些日子以来那层若有似无的、虚假的平静。提醒着我,这一切的底色,
终究是一场交易。日子不咸不淡地继续滑向第二年。金榆出差变得频繁起来,
每次时间都不短。偌大的公寓常常只剩下我一个人。起初觉得自由,久了,
竟生出点空落落的冷清。连阿姨都问:“先生这次出差好久了啊。”我窝在沙发里刷手机,
屏幕上是他助理小林朋友圈发的几张照片。某个高端行业论坛的现场,
金榆穿着挺括的黑色西装,站在演讲台上,聚光灯下,侧脸线条冷峻,气场强大,
是那种天生的掌控者姿态。台下是黑压压的听众和无数闪烁的镜头。
照片下面有人评论:“金总这气势,绝了!又帅又能打!”心里莫名有点堵。
我把手机扔到一边,盯着天花板发呆。那个在台上光芒万丈、冷静自持的男人,
和那个会帮我扶花箱、甚至熟练地裹花头保护套的男人,是同一个人吗?哪个才是真实的他?
又或者,哪个都跟我没什么关系。他这次出差回来,明显带着一身疲惫。眼底有浓重的青影,
下巴的线条也绷得很紧。阿姨炖了汤,他草草喝了几口就进了书房,门关了一晚上。
第二天是周末,他破天荒地睡到了中午。我起床时,他还在睡。
阿姨小声说:“先生好像累坏了,别去吵他。”下午,我正对着电脑处理工作室的订单,
书房门开了。金榆穿着睡袍走出来,头发有点乱,睡眼惺忪,少了几分平日的锋利,
看起来……有点难得的柔软。“有吃的吗?”他声音带着刚睡醒的沙哑,揉着太阳穴问阿姨。
“有有有,温着呢,我给您端出来。”阿姨忙不迭地去了厨房。他走到客厅,看到我,
脚步停住。目光扫过我摊在茶几上的设计稿和色卡。“在忙?”“嗯,
下周有个婚礼的场布设计,主家要求多。”我随口应道。他走到沙发另一头坐下,没说话,
只是安静地等着阿姨端吃的过来。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奇异的、不被打扰的宁静。
阳光透过落地窗洒进来,落在他身上,暖融融的。阿姨端来一碗热腾腾的鸡丝粥和几样小菜。
他拿起勺子,慢慢地吃着。我继续对着电脑屏幕纠结配色,用笔在纸上胡乱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