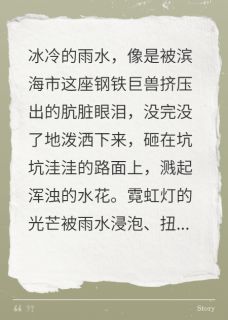
冰冷的雨水,像是被滨海市这座钢铁巨兽挤压出的肮脏眼泪,没完没了地泼洒下来,
砸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溅起浑浊的水花。霓虹灯的光芒被雨水浸泡、扭曲,
在湿漉漉的沥青上拉出破碎而诡异的色块,红的像血,绿的像脓,紫的像淤青。
陈风单薄的蓝色雨衣贴在身上,早已失去了最后一点遮蔽作用,雨水无孔不入,
顺着脖颈流进脊背,刺骨的寒意如同跗骨之蛆,啃噬着他早已疲惫不堪的神经。他佝偻着背,
几乎趴在电动车的塑料车把上,老旧的电驴在积水中发出不堪重负的**,
后座那个巨大的“闪电速达”保温箱,此刻重得像一座压在他命运之上的山。目的地,
紫金苑。滨海市顶尖的富人区,一个用金钱和冷漠堆砌出的堡垒,
与他破旧的外卖箱、锈迹斑斑的电驴格格不入。雨水模糊了视线,但他不敢慢,不敢停。
这一单超时,意味着他今晚的奔波可能颗粒无收,意味着下个月的泡面又要少几包。终于,
那巨大、冰冷的雕花铁门轮廓在瓢泼雨幕中显现。陈风紧绷的心弦刚想松动一丝,
一道刺目的白光如同地狱探出的獠牙,猛地撕裂了灰暗的雨帘!引擎的咆哮低沉而狂暴,
一辆磨砂黑的玛莎拉蒂如同一头嗜血的钢铁巨兽,毫无征兆地从侧面的岔路咆哮着蹿出!
它以一个蛮横到极致的姿态,几乎是贴着陈风的车头,轮胎在湿滑路面发出刺耳的尖叫,
伴随着“嘎吱”一声令人牙酸的金属摩擦,嚣张地横在了小区入口的正中央!
陈风的心脏瞬间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紧!他猛捏刹车,轮胎在积水中打滑,
车身剧烈地左右摇摆!巨大的惯性裹挟着冰冷的泥水,像一面肮脏的墙,
狠狠拍打在他的脸上、身上!他连人带车无法控制地向旁边歪倒,
沉重的保温箱如同被抛弃的沙袋,重重砸在冰冷湿滑的地上!“哐当!”箱盖弹开,
里面他小心翼翼护了一路、指望着好评的热腾腾麻辣香锅,此刻像被践踏的梦想,
红油、滚烫的汤汁、鲜嫩的食材,在浑浊的雨水中爆开、流淌、被无情地冲刷、稀释。
一股混合着辛辣香气和雨水腥气的、令人窒息的怪味弥漫开来。
剪刀门如同恶魔的翅膀向上旋开。一只锃亮的、纤尘不染的黑色手工皮鞋,
带着一种睥睨众生的傲慢,稳稳踩进浑浊的积水里。赵宇,滨海大学人尽皆知的顶级纨绔,
穿着一身价值不菲的休闲西装,头发精心打理得一丝不苟。他嘴角叼着半截烟,
青烟在雨幕中扭曲升腾。他下车,轻佻的目光扫过地上那一片狼藉,
如同欣赏一幅拙劣的涂鸦,最后,那目光才慢悠悠地、带着毫不掩饰的厌恶和戏谑,
定格在浑身湿透、泥浆满身、正挣扎着试图扶起电动车的陈风身上。“啧,
”赵宇的声音不大,却像冰冷的刀子刮过耳膜,“送个外卖都送不明白?
急着投胎往爷爷车上撞?”他身后的车窗降下,
露出几张妆容精致、此刻却写满鄙夷和幸灾乐祸的脸孔,
刺耳的嗤笑声毫不掩饰地穿透哗哗雨声。陈风抹了一把脸,泥水糊住了眼睛,又涩又痛。
赵宇那张脸,他认得。一股滚烫的岩浆般的屈辱猛地从心底炸开,直冲天灵盖!
他死死咬住后槽牙,口腔里瞬间弥漫开浓重的铁锈味。
胃里空荡荡的绞痛和手机里那条未读的、催命般的短信,像两副冰冷的镣铐,
瞬间锁死了他几乎要喷薄而出的怒火。“对不起,赵少。”声音干涩得如同砂纸摩擦着枯木,
“我…我赔。”“赔?”赵宇像是听到了本世纪最好笑的笑话,夸张地挑起眉毛,
嘴角咧开一个充满恶意的弧度。他慢悠悠地踱步过来,
昂贵的皮鞋踩在混着红油和食材残渣的污水里,发出“啪嗒、啪嗒”的轻响,
每一步都像踩在陈风的心上。他弯下腰,用一种极其嫌弃的姿势,
两根手指捻起地上那张同样被污水浸透、印着订单金额的外卖单——九十八块五毛。
一丝残忍的、猫捉老鼠般的笑容在他脸上漾开。
他慢条斯理地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一个鼓囊囊的鳄鱼皮钱夹,动作优雅得像在展示艺术品。
他抽出两张崭新的红色钞票,在陈风死死盯着的、几乎要喷出火的目光中,手腕随意地一松。
两张百元大钞,如同两片被唾弃的垃圾,飘飘荡荡,
精准无比地落在了那滩被雨水、红油和泥泞浸透的、最污秽不堪的狼藉中心。“穷狗,
”赵宇的声音带着一种施舍般的残忍,清晰地盖过雨声,钻进陈风每一个毛孔,“舔干净,
这两千块,就赏你了。”他下巴傲慢地一抬,
眼神里是**裸的、将人踩进泥里的侮辱和戏弄。车窗里的哄笑声瞬间拔高,尖锐刺耳,
如同魔音灌脑。冰冷的雨水冲刷着陈风滚烫的脸颊和脖颈,他垂在身侧的手,
指甲深深陷入掌心,鲜血混着泥水渗出。他猛地弯下腰,动作带着一种近乎自毁的决绝。
他没有去看那两张钞票,更没有去“舔”。他伸出沾满污泥的手,
一把抓住那两张湿透、污秽的纸片,将它们死死攥在掌心,仿佛要将其捏碎融入自己的骨血!
然后,他抬起头。雨水顺着他凌乱的额发、高挺的鼻梁、紧抿的嘴角不断流下,
模糊了他的面容。但那双眼睛!透过冰冷的雨幕,
像两把刚刚淬炼出炉、带着无尽寒气的匕首,
直直地、毫无畏惧地钉在赵宇那张写满优越感的脸上!那眼神里燃烧的,不再是单纯的屈辱,
而是沉淀下来的、冰冷的、刻骨的恨意,以及一种被逼至悬崖边缘后、野兽濒死般的凶戾!
赵宇脸上那猫戏老鼠的笑容骤然僵住了一瞬。那双眼睛里的东西太过冰冷锐利,像实质的针,
竟让他心底莫名地掠过一丝极其细微的不适。但旋即,
这丝不适就被更汹涌的轻蔑和怒火覆盖。“呵,贱骨头还挺硬?”他嗤笑一声,
像赶苍蝇般挥挥手,“赶紧滚!别脏了本少的地界!”玛莎拉蒂嚣张的引擎再次咆哮,
如同巨兽的怒吼,碾过地上的狼藉,卷起一片污浊的水帘,
冲进了那扇象征着另一个世界的雕花铁门。只留下陈风,
像一尊被遗弃在暴风雨中的残破石像,僵硬地站在那片被践踏的废墟之上。
雨水无情地冲刷着他,在地上汇成小小的、浑浊的水洼。他摊开手,
掌心那两张被攥得不成样子、沾满红油和污泥的钞票,黏腻、冰冷,像两块耻辱的烙印。
他深吸一口气,冰冷的空气裹挟着雨水和屈辱的气息呛入肺腑,带来一阵剧烈的咳嗽。
他蹲下身,开始沉默地、机械地收拾散落一地的保温箱碎片、变形的塑料盒。
每一个动作都牵扯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剧痛。就在他拾起一块碎裂的塑料盖时,
眼角的余光猛地瞥见旁边被车轮溅起的浑浊水洼边缘——一个小小的、瑟瑟发抖的毛团!
那是一只极其瘦弱的橘色小猫,可能才几个月大,浑身的毛被泥水和雨水完全打湿,
紧紧贴在嶙峋的骨架上,显得脑袋格外大。它蜷缩在冰冷的水洼边,一只后腿似乎受了伤,
以一种不自然的姿势拖在地上,身体因为寒冷和恐惧而剧烈地颤抖着。
一双湿漉漉的琥珀色大眼睛,此刻写满了无助和惊恐,正透过雨幕,
茫然地、又带着一丝微弱的求生渴望,望向陈风。那眼神,像一根最细的针,
猝不及防地刺中了陈风心底最深处那片早已被生活磨砺得近乎麻木的柔软。
他收拾残骸的动作顿住了。赵宇的羞辱,退学的威胁,生活的重压……所有尖锐的痛楚,
在这一刻,似乎都被这只弱小生命濒死的颤抖短暂地覆盖了。
一种源于本能、远早于任何算计的冲动,驱使着他。他甚至没有多想。
陈风放下手中的塑料碎片,没有丝毫犹豫,小心翼翼地伸出手,动作是那么轻柔,
仿佛怕惊扰了这缕随时会熄灭的生命之火。他避开小猫受伤的后腿,用沾满污泥的手掌,
极其温柔地将那个冰冷、颤抖的小小身体,整个托了起来。小家伙很轻,
轻得像一团没有重量的湿棉花。接触到陈风掌心传来的微薄暖意,它似乎受到了惊吓,
发出极其微弱、几乎被雨声淹没的“咪呜”声,本能地想挣扎,
但虚弱的身体只允许它象征性地动了一下爪子。“别怕……”陈风下意识地低声喃喃,
声音沙哑得厉害。他迅速脱下自己那件同样湿透、但内侧相对干净些的廉价T恤,
小心翼翼地将小猫包裹起来,只露出一个小小的、还在滴水的脑袋。他把它轻轻抱在怀里,
用体温试图为它驱散一点寒气。就在他做完这一切,抱着小猫准备起身离开这片屈辱之地时,
那辆已经驶入小区的玛莎拉蒂竟然又缓缓倒了出来。副驾驶的车窗降下,
露出一张妆容精致的脸,正是刚才嗤笑最响的那个女孩。她看着陈风怀里的泥团子,
夸张地捏住了鼻子,对着赵宇娇声道:“宇少快看!那穷鬼捡垃圾呢!啧啧,真是脏死了,
跟那猫一样,都是下水道里的玩意儿!”赵宇的目光扫过陈风怀里的猫,又落回陈风身上,
嘴角勾起一个极尽轻蔑的弧度:“呵,物以类聚。”他轻飘飘地吐出四个字,车窗升起,
玛莎拉蒂再次轰鸣着绝尘而去。冰冷的雨水浇在陈风头上、脸上,
也浇在他怀里那个微弱颤抖的小生命身上。他抱紧了怀里的小东西,
用自己的身体尽可能为它遮挡风雨。没有再看那消失的车尾灯一眼,
他沉默地扶起倒地的电动车,将捆扎得歪歪扭扭的保温箱重新固定,
然后把裹着小猫的T恤小心翼翼塞进自己湿透的夹克内侧,紧贴着胸口。拧动电门,
老旧的电瓶发出濒死般的**,载着他和一份突如其来的、沉重的温暖,
以及满身的屈辱与冰冷,缓慢地、艰难地驶离这片不属于他的、金碧辉煌的牢笼。雨,
似乎永无休止。城市的霓虹在无边的水幕中扭曲、变形,
像一个巨大的、冰冷的、光怪陆离的梦魇。“哗啦——哐当!
”陈风将电动车几乎是摔在“筒子楼”狭窄幽暗的楼梯口,
车轮蹭过旁边堆放的、散发着浓重霉味的废旧家具。
这栋老楼如同城市肌体上一块流脓的疮疤,拥挤、破败、摇摇欲坠。
里常年弥漫着劣质油烟、潮湿的霉味、腐烂垃圾和若有若无尿臊气混合的、令人作呕的气息。
他摘下湿透的雨衣头盔,甩了甩头发上不断淌下的水珠,冰冷的雨水顺着脖子流进衣领,
激得他连打了几个寒颤。他下意识地按了按胸口,隔着湿冷的夹克,
能感觉到里面那个小生命微弱的起伏和颤抖。他拖着灌了铅似的双腿,抱着怀里的小东西,
一步步爬上那陡峭、油腻、仿佛永无尽头的楼梯。腐朽的木板在脚下发出痛苦的**,
每一次抬脚都异常艰难。楼道里唯一那盏昏黄的灯泡,钨丝在垂死挣扎,
光线微弱得只能勉强照亮脚下方寸之地,
墙壁上剥落的墙皮和蜿蜒的水渍在昏暗中如同鬼魅的爪痕。顶楼,最角落的一间。
门板薄得仿佛一拳就能击穿,边缘的漆皮卷曲剥落。陈风掏出钥匙,
冰冷的金属触感冻得他指尖发麻。钥匙**锁孔,转动时发出干涩刺耳的摩擦声,
在这死寂的楼道里如同哀鸣。门开了。
一股混合着尘土、霉变木头、陈旧纸张和淡淡铁锈味的沉闷气息扑面而来,几乎令人窒息。
房间小得令人心酸,一张吱呀作响的木板床占据了大部分空间,一张掉漆的书桌紧挨着床沿,
上面堆满了旧课本和笔记,摇摇欲坠。
唯一的窗户对着隔壁楼那堵同样破败、长满青苔和污渍的墙壁,
此刻正顽强地抵抗着外面的风雨,但仍有冰冷的雨水,顺着窗框腐朽的缝隙,
滴滴答答地落在窗台下放着的一个搪瓷脸盆里,发出单调而冰冷的“嗒、嗒”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