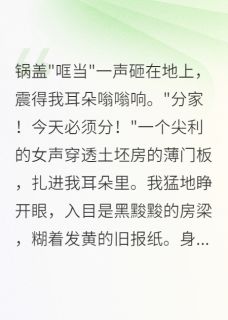
锅盖"哐当"一声砸在地上,震得我耳朵嗡嗡响。
"分家!今天必须分!"一个尖利的女声穿透土坯房的薄门板,扎进我耳朵里。我猛地睁开眼,入目是黑黢黢的房梁,糊着发黄的旧报纸。身下硬邦邦的土炕硌得骨头疼,盖在身上的薄被一股子陈年霉味。这不是我那个摆满绿植和小夜灯的出租屋。
脑子像被棍子搅过,一大团不属于我的记忆碎片涌进来。安遥,十八岁,刚死了爹娘,躺在炕上发高烧。外头吵嚷的是原主的奶奶钱金花和大伯安国庆两口子。爹娘刚下葬三天,尸骨未寒,他们就迫不及待要分家,或者说,是要把这孤女扫地出门。
我撑着酸软的身子坐起来。环顾这间屋子,家徒四壁,唯一的木箱敞开着,里头几件打着补丁的旧衣服被翻得乱七八糟。墙角堆着半口袋瘪瘪的粮食,大概就剩十几斤粗玉米面。这就是原主爹娘留下的全部家当?不,不对。记忆里有个模糊的点。我下意识抬手摸了摸颈间挂着的那个东西——一个灰扑扑、比指甲盖大不了多少、形状不规则的小石头坠子,用根褪色的红绳拴着。这是原主娘临死前死死塞进她手里的,嘴里念叨着"护身符"。
手指触碰到石头的瞬间,眼前猛地一花。再清晰时,我整个人站在一片灰蒙蒙的空间里。脚下是坚硬平整的地面,四周空荡荡,望不到边,像个巨大的空仓库。空气里带着点泥土和青草的湿润气息。角落孤零零地堆着几个破麻袋。我心念一动,意识探过去。
一袋是颗粒饱满、金灿灿的麦子,起码上百斤。一袋是晒干的红枣,个大肉厚。还有半袋风干得硬邦邦的腊肉,油汪汪的。旁边居然还有一小布袋白花花的细盐!最边上,一个小布包,打开一看,是卷在一起的钱!十块的"大团结"有三张,五块的"炼钢工人"两张,两块、一块的毛票子卷成一卷,还有不少分币。我飞快数了数,加起来有整整四十六块三毛五分!这对八十年代初的农村,尤其对一个刚死了爹娘、家底被掏空的孤女来说,简直是巨款!记忆里,原主娘偷偷攒了半辈子,就是怕有这一天。
外头的吵闹声更大了,夹杂着推搡和安国庆老婆王翠芬刻薄的叫骂:"死丫头片子还装病赖着?赶紧滚出来!这房子是安家的根!轮不到你个赔钱货占着!"
我深吸一口气,心念一动,意识退出了那个灰蒙蒙的空间。石头坠子贴着皮肤,冰凉一片,却让我心里有了底。空间,粮食,钱。这就是我在这陌生的八十年代活下去的本钱。我撑着炕沿下地,腿还有点软,但烧好像退了。走到门边,猛地拉开了那扇吱呀作响的破木门。
刺眼的阳光晃得我眯了下眼。院子里站着三个人。干瘦刻薄的老太太钱金花,叉着腰,三角眼吊着。她旁边是矮壮的大伯安国庆,一脸不耐烦。王翠芬正唾沫横飞地指着这间破屋子,看到我出来,声音陡然拔高:"哟!舍得出来了?还以为你要在里头挺尸呢!正好,今天就把家分了!"
钱金花眼皮都没抬,耷拉着嘴角:"你爹娘没了,这房子是老安家的根,得留给你大伯这一支的男丁。你一个丫头,早晚是别人家的人,不能占着祖屋。"她指了指墙角那半袋玉米面,"粮食不多,你拿走一半,够你吃一阵子。锅碗瓢盆,给你个豁口的瓦盆,一个碗。"
王翠芬立刻接腔,指着院子角落那个歪歪斜斜、用几根木棍和破塑料布搭的窝棚:"喏,那地方收拾收拾能住人!赶紧的,把你那堆破烂搬过去!别占着茅坑不拉屎!"她眼神瞟过我身后的屋子,显然是想看看还有没有什么能搜刮的油水。
安国庆抱着胳膊,瓮声瓮气地帮腔:"听你奶和你大娘的。赶紧收拾,下午队里还有活。"他压根没把我当回事,只想着赶紧把我扫地出门,霸占这三间虽然破但还算能住人的土坯房。
左邻右舍有几个人探头探脑,脸上有同情,但没人敢吱声。钱金花在村里是有名的泼辣不讲理,安国庆也是个混不吝。
我看着他们,没哭没闹。原主残留的那点委屈和愤怒在我心底翻腾,但更多的是冷静。哭没用,闹更没用。"分家,行。"我的声音有点哑,但很清晰,"房子我不要。"
钱金花和王翠芬脸上立刻露出得逞的喜色。
"但是,"我话锋一转,目光扫过他们,"我爹娘留下的东西,该我的那份,一分不能少。"
钱金花三角眼一瞪:"啥东西?家里就那点粮食,不是给你一半了吗?你还想要啥?"
"粮仓里的粮食,我爹娘辛苦挣的工分分的,不止这点。还有,我爹年前跟人进山,背回来半扇野猪肉,熏成了腊肉,挂在房梁上。我娘攒的鸡蛋钱,还有队里去年分的棉花……"我一样一样数着原主记忆里家里值点钱的东西。原主爹勤快,娘节俭,家里虽穷,但也不至于只剩半袋玉米面。显然,值钱的都被这三人趁她病倒时搬走了。
王翠芬脸色一变,尖声叫起来:"放屁!哪来的野猪肉?哪来的钱?你爹娘死得突然,看病吃药不花钱?办丧事不要钱?早就花光了!还倒欠着饥荒呢!没让你还债就是看你可怜!"
安国庆也沉下脸:"安遥,你小小年纪,别学得跟你娘似的斤斤计较!那些东西,早没了!"
钱金花更是拍着大腿干嚎起来:"哎哟喂!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儿子儿媳刚走,孙女就来逼我这老婆子啊!那些东西早填了你爹娘看病吃药的窟窿了!你这是要逼死我啊!"
他们一唱一和,颠倒黑白,仗着我一个小姑娘无依无靠,想把事情坐实。
邻居们议论声大了点,但钱金花眼睛一横,声音又小了下去。
我知道硬碰硬不行。我摸了摸颈间的石头坠子,心里有了主意。面上露出点犹豫和害怕,声音低了下去:"奶,大伯,大娘……我……我昨晚梦见我爹了。"
钱金花干嚎的声音顿了一下。
我低着头,声音带着点抖,像是被吓的:"我爹浑身湿漉漉的,说……说他在下面冷,吃不饱……他跟我说,房梁最东头那根椽子后面,他藏了块好肉,本来是留着给我补身子过生日的……他说,他死得冤,要是连这点东西都保不住给我,他……他闭不上眼……"我越说声音越小,带着哭腔,还适时地打了个哆嗦,像是真被噩梦魇着了。
农村人,尤其老一辈,对鬼神托梦这种事,多少有点忌讳。钱金花和安国庆的脸色都变了变。王翠芬还想嚷嚷,被安国庆一把扯住。
"你……你瞎说啥呢!哪有什么肉!"安国庆眼神有点虚,声音也没刚才那么硬气了。
"爹说……就藏在椽子后面,用油纸包着……"我怯生生地抬头,飞快地瞥了一眼正房屋顶那根最粗的椽子。
钱金花三角眼滴溜溜转,狐疑地看看我,又看看那根椽子。安国庆也下意识抬头看过去。王翠芬想说什么,被安国庆狠狠瞪了一眼。
"去!搬梯子!看看去!"钱金花咬咬牙,指使安国庆。她心里也犯嘀咕,老二(原主爹)生前确实是个有心眼的,真藏了东西也说不定。要是真有块好肉……她可不能便宜了这死丫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