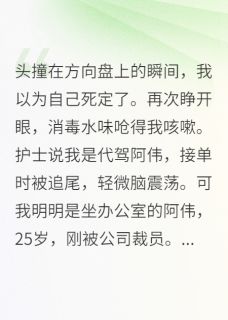
头撞在方向盘上的瞬间,我以为自己死定了。再次睁开眼,消毒水味呛得我咳嗽。
护士说我是代驾阿伟,接单时被追尾,轻微脑震荡。可我明明是坐办公室的阿伟,25岁,
刚被公司裁员。镜子里的脸陌生又熟悉,口袋里的手机弹出代驾平台提示:“您有新订单,
请前往星辉酒店接驾。”我浑浑噩噩开着平台分配的电动车赶到时,
一辆豪车的车门突然打开。女人跌出来,酒气能熏醉一头牛。“去……去云顶别墅。
”她说话舌头打结,却不忘把大牌包往我怀里塞。我扶她坐进副驾,
她突然拽住我胳膊哭:“那个**,骗我钱就算了,还敢找小三!”我没接话,
代驾这行见多了酒后吐真言的。车开到半路,她突然凑过来,
呼吸喷在我脖子上:“你长得……挺顺眼。”我心一慌,差点闯红灯。到了别墅门口,
她站不稳,我只好架着她往里走。刚把她扶到沙发上,她突然反手把我摁在地毯上。
口红蹭到我衬衫上,她眼神迷离:“放纵一次……就一次。”香水味混着酒气钻进鼻子,
我看着她泛红的眼角,脑子一热就从了。第二天醒在客房,阳光透过落地窗晃眼。
她系着围裙站在厨房,煎蛋的香味飘过来。“醒了?”她把餐盘推给我,“考虑下,
做我专职司机?”我盯着煎成心形的溏心蛋,听见自己说:“多少钱?”“月薪三万,
包吃住。”她递来一份打印好的协议,“但得签这个,只干活,不动感情。
”我扫了眼末尾的签名处,林晚,这名字和她的人一样,带着点冷傲。我签了字,心里清楚,
这不过是各取所需。搬进别墅的第一周,我活得像个隐形人。她的卧室在二楼,
我住一楼佣人房。她吃饭时,我得等她放下筷子才能上桌。她朋友来做客,
我要站在门口换鞋,被当成服务生也只能赔笑。第三周周末,门被踹开时,我正在擦她的车。
一个染着黄毛的男人闯进来,看见我就啐了口:“哪来的穷鬼?”“我是林**的司机。
”我攥紧手里的抹布。他突然笑了,掏出手机对着我拍:“我姐就是心善,
捡个流浪汉回来当宝。”这人是林强,林晚的亲弟弟。我后来才知道,他是个无业游民,
靠啃姐活着。他径直闯进客厅,把脚翘在茶几上:“姐,给我两万,昨晚输惨了。
”林晚从书房出来,手里拿着文件:“上周不是刚给过你一万?”“那点钱够干什么的?
”林强眼睛瞟向我,“别是给外人花了吧?”他突然冲过来,一把推开我:“滚出去,
这没你说话的份!”我踉跄着撞在墙上,后腰磕得生疼。林晚皱了皱眉,却不是对着林强。
“阿伟,你先去车库待着。”她头也没抬。我盯着她手里的协议,
突然觉得那三万块像烧手的烙铁。那天晚上,我听见二楼传来摔东西的声音。
林晚的书房灯亮到后半夜。我起夜时经过书房,门缝里漏出她的哭声,很轻,像只受伤的猫。
书桌上摆着个旧相框,里面是她和一个老太太的合影。老太太笑得慈祥,林晚靠在她肩上,
眼睛弯成了月牙。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对林强那么纵容。更不知道,这份看似简单的雇佣关系,
会把我拖进怎样的泥沼里。只是那晚的月光太凉,照在空荡荡的客厅里,像谁没擦干的眼泪。
林强再来的时候,是周三下午。我刚把林晚送到公司。他带着个染绿毛的朋友,
堵在别墅门口。“五万。”他开门见山,手里把玩着把弹簧刀,刀光晃得人眼晕。
“林**不在。”我往旁边站了站,想关上门。他伸手抵住门框,
绿毛朋友突然笑了:“强哥,你姐这司机挺横啊。”林强一脚踹在我小腿上。“废什么话?
我姐的钱就是我的钱。”他径直往里闯,“我自己拿。”他们直奔林晚的卧室,
翻箱倒柜的声音从二楼传来。我冲上去想拦,被绿毛按在楼梯口。“你算哪根葱?
”他掐着我脖子,“强哥说了,你就是我姐养的一条狗。”我挣开他,
听见卧室里传来玻璃破碎的声音。是林晚床头柜上的花瓶,里面插着她每天换的白玫瑰。
那是她母亲生前最喜欢的花。我血往上涌,一拳砸在绿毛脸上。林强从卧室冲出来,
手里攥着一沓现金。“行啊你,敢打我兄弟?”他把钱塞给绿毛,转身就来踹我。我没躲,
硬生生受了一脚,后腰撞在楼梯扶手上,疼得直抽气。他突然躺在地上,掏出手机录视频,
嘴里喊着“打人了!家暴啊!”我愣住的功夫,门开了。林晚站在门口,脸色白得像纸。
“姐!他打我!”林强立刻哭嚎起来,“你看我这脸!”林晚的目光扫过满地狼藉,
落在我渗血的嘴角。“够了。”她声音发紧。我以为她要替我说话。她却从包里掏出一张卡,
扔给林强:“里面有十万,滚。”林强瞬间爬起来,搂着绿毛笑:“还是我姐疼我。
”两人走的时候,故意撞了我一下。门关上的瞬间,林晚才开口。“别跟他一般见识。
”她背对着我,声音很轻。我看着地上的玫瑰花瓣,突然觉得那三万块工资像烧红的烙铁,
烫得我攥不住。日子还得往下过。我开始留意林强的动静。那天帮林晚整理副驾时,
掉出来一张贷款合同。借款人是林晚,签字处却歪歪扭扭,像极了林强的笔迹。
我拿着合同冲进书房时,正看见她对着母亲的相框发呆。“妈,我是不是太纵容他了?
”她手指摩挲着相框边缘,“可他是我唯一的弟弟啊。”我把合同往桌上一放。她抬头看我,
眼里的红血丝吓了我一跳。“他用你的身份证贷了三十万。”我声音发颤,“再这样下去,
他会把你拖垮的。”她拿起合同,指尖抖得厉害,却没说话。那天晚上,她没去应酬。
坐在客厅沙发上,一杯接一杯地喝酒。我泡了杯蜂蜜水递过去,她没接,
却突然问:“你妈还在吗?”“走了三年了。”我挠挠头,“生病走的,
临走前让我好好过日子。”她盯着酒杯里的涟漪:“我妈走的时候,让我照顾好弟弟。
”“可照顾不是纵容。”我脱口而出。她猛地抬头看我,眼神里有什么东西碎了。
没等我再说什么,她起身回了卧室。她生日那天,我跑了三条街,
才找到一家卖老式奶油蛋糕的店。蛋糕上的花纹,和她书桌上那个相框的边框一模一样。
那是她之前跟阿姨聊天时提过的,她妈最拿手的款式。她回来时,看见餐桌上的蛋糕,
愣了很久。“谁让你买的?”她语气还是冷的。“今天是你生日。”我搓着手,
“听说阿姨以前……”“放着吧。”她打断我,却破天荒地坐下,把第一块蛋糕推到我面前。
奶油有点化了,甜得发腻。我却吃出了点酸味儿。林强的胆子越来越大。上周六,
他带了五六个狐朋狗友来别墅开派对。音响震得地板都在抖。
一个穿吊带裙的女人故意撞了我一下,红酒全泼在我衬衫上。“不好意思啊,手滑。
”她笑得不怀好意。林强拿着手机对着我拍:“看,我姐雇的司机多敬业,
被泼了还站着不动。”他把照片发进家族群,配文:“新佣人,听话,就是穷了点。
”群里立刻炸开了锅。林晚的堂哥直接打电话过来,我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
“林晚你是不是疯了?找个这种货色,丢我们林家的脸!”“他就是个司机。
”林晚的声音很平静。“司机?我看是小白脸吧!你前夫再渣,好歹是个老板,
你现在……”林晚挂了电话,客厅里瞬间安静下来。她走到我面前,递来一件新衬衫。
“换上吧。”她说。我接过衬衫,料子很软,是我从没穿过的牌子。“别往心里去。
”她突然说。这四个字像羽毛,轻轻扫过我心上那块最硬的地方。我没说话,
只是把脏衬衫脱下来时,动作轻了很多。昨天半夜,我起夜时,听见林强在阳台打电话。
五十万……再给我三天……不然我就把她妈那个破柜子撬了……”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
那个黑色的保险柜,她每天都会擦一遍。我冲回房间,翻来覆去睡不着。天快亮时,
我听见书房有动静。悄悄走过去,看见林晚正把一把黄铜钥匙塞进一个绒布袋里。
她转身时撞见我,吓了一跳。钥匙掉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她没捡,只是看着我。
眼睛在晨光里亮得吓人。我弯腰捡起钥匙,想还给她。她却突然抓住我的手,
把钥匙按进我手心。“放好。”她的指尖冰凉,“别让任何人找到。”我愣在原地。
她转身回了卧室,没说为什么。我攥着那把钥匙,手心全是汗。这钥匙,分明是保险柜上的。
她有那么多隐蔽的地方可以藏。却偏偏,塞给了我这个“外人”。窗外的天慢慢亮了。
我看着手里的钥匙,突然明白。这场看似荒唐的雇佣关系里,早就有人动了不该动的心思。
而那个撬保险柜的威胁,像一把悬着的刀。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落下来。周五晚上十点,
门被撞开时。我正在给林晚发消息,说她要的文件放在书房了。三个纹身男先冲进来,
手里都拎着钢管。林强跟在后面,脸上带着狞笑:“阿伟,好久不见啊。
”我立刻挡在通往书房的门口。“林晚不在家。”“我知道。”他挥了挥手,“我今天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