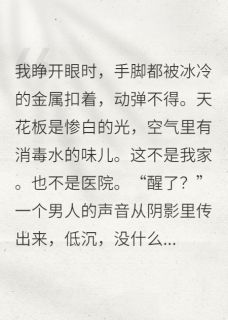
我睁开眼时,手脚都被冰冷的金属扣着,动弹不得。天花板是惨白的光,
空气里有消毒水的味儿。这不是我家。也不是医院。“醒了?
”一个男人的声音从阴影里传出来,低沉,没什么温度。我的心猛地一沉。完了,绑架?
仇家?我最近没得罪谁啊?银行卡里那点余额也不值得绑吧?脚步声靠近。
阴影里走出一个人。个子很高,黑色大衣裹着颀长的身形,脸色有些病态的苍白,薄唇抿着,
看人的眼神像冰渣子。长得是真好看,但那股子阴鸷劲儿,让人后背发凉。我认识这张脸。
财经杂志上常客。沉舟。
沉氏集团那个年纪轻轻就把家族产业搅得天翻地覆、逼得几个叔伯锒铛入狱的狠角色。
商场上出了名的心狠手辣,睚眦必报,标准的反派模板。
我这种刚毕业、为了房租发愁的小透明,怎么会惹上他?“沉…沉先生?”我声音有点抖,
努力想把手腕从冰冷的束缚里抽出来,“您是不是抓错人了?我不认识您,
我也没钱…”沉舟没说话,只是走到我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他眼神在我脸上扫了一圈,
像是在确认什么。我被他看得头皮发麻。然后,他做了一个让我大脑彻底宕机的动作。他,
沉舟,那个传说中跺跺脚商界都要震三震的大反派,突然膝盖一弯,“噗通”一声,
直挺挺地跪在了我面前!冰凉坚硬的地面,他跪得结结实实。我吓得差点从椅子上弹起来,
可惜被绑着,只能拼命往后缩脖子。“你…你干嘛?!”我声音都劈叉了。
这什么新型的折磨手段?精神攻击?沉舟抬起头,那张一向没什么表情的俊脸上,
此刻竟然清晰地写着一种…脆弱?还有一丝破罐子破摔的决绝?“安幸。”他叫我的名字,
声音干涩,“帮我。”我彻底懵了。“帮…帮你什么?”“抱紧你的大腿。”他说,
眼神直勾勾的,带着一种孤注一掷的疯狂,“求你。”时间倒回三天前。我,安幸,
一个刚拿到转正通知、正盘算着下个月房租能不能少喝几杯奶茶省下来的社畜。
生活最大的波澜是楼下早餐店肉包涨价五毛钱。唯一称得上不平凡的是,
我偶尔会做一些稀奇古怪的梦。梦里总有个模糊的影子,追着我不放,
嘴里喊着什么“本源”、“钥匙”。醒来就忘得差不多。直到那天加班到深夜,
回家路上被一辆失控的电动车剐蹭,摔了一跤,擦破点皮。当晚,
那个模糊的影子在梦里变得无比清晰——就是沉舟那张苍白阴郁的脸。他掐着我的脖子,
眼神狠戾:“把‘源种’交出来!”我吓醒了,一身冷汗。
只当是白天被财经新闻推送里沉舟那张反派脸**到了,没多想。结果第二天,
我就被“请”到了这个鬼地方。此刻,这个在梦里掐我脖子的男人,正跪在我面前,
求我让他抱大腿。荒谬感像潮水一样把我淹没。“沉先生,”我强迫自己冷静,
声音还是有点颤,“您是不是…认错人了?或者…压力太大了?要不,您先起来?
”沉舟没动,反而往前挪了半步,离我更近。
他身上那股清冽又带着点苦味的雪松气息扑面而来。“我没认错。”他盯着我,
眼神执拗得像钉子,“安幸,只有你能帮我。我快死了。”我:“……”信息量太大,
CPU烧了。“死…死了?您看着…挺健康的啊?”除了脸色白了点。“中毒。
”他言简意赅,撩起了左手的袖子。手腕内侧,皮肤下隐隐透出一种诡异的青紫色,
像蛛网一样向上蔓延,已经快到手肘。看得我倒吸一口冷气。“一种很特殊的神经毒素,
无解。”沉舟放下袖子,语气平淡得像在说别人的事,“我最多还有三个月。
”“那…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下意识问。沉舟的目光再次落在我脸上,
带着一种奇异的穿透力。“我查了所有线索,最后指向你。我的‘生机’,在你身上。
”他顿了顿,似乎在斟酌措辞,“靠近你,我体内的毒素活性会降低,痛苦会减轻。
那天在酒店大堂,我们擦肩而过,我手腕上的青色就淡了一瞬。”我想起来了。
是有那么一次,我去送文件,和一个浑身低气压的高大男人在旋转门那里差点撞上。
当时只觉得那人气场太强太冷,冻得我一哆嗦,赶紧低头跑了。原来那就是沉舟?“所以,
”我艰难地消化着他的话,“你觉得我是你的…解药?”“或者说,‘中和剂’更准确。
”沉舟纠正,“我试过各种方法,只有在你身边,毒素才会被压制。我需要待在你身边,
安幸。这是唯一的活路。”他看着我,眼神不再是商场上的杀伐决断,
而是溺水之人抓住最后一根浮木的绝望与渴求。“条件你开。钱,资源,地位,
只要我能给的。”他声音低哑,“或者,你希望我怎么做?求你?”他又想往前凑。
我被他这“抱大腿”的执着劲儿弄得浑身不自在。“停!打住!”我赶紧喊,“你先起来!
跪着像什么样子!”沉舟动作顿住,抬眼看我,眼神里带着询问。“起来说话!
”我加重语气。他抿了抿唇,似乎权衡了一下,终于撑着膝盖,慢慢地站了起来。
高大的身影重新笼罩下来,压迫感又回来了,但至少不是跪着的了。“解开我。
”我晃了晃被铐住的手腕。沉舟没动,眼神里带着警惕和审视。“沉先生,
”我努力让自己显得镇定,“你看,我手无缚鸡之力,你一个大男人还怕我跑了不成?
你把我绑着,我怎么…怎么让你‘抱大腿’?这姿势也不方便吧?”这话说得我自己都脸红。
沉舟沉默了几秒,似乎在评估风险。最终,他还是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把精巧的钥匙,俯身,
解开了我手腕和脚踝上的束缚。冰冷的金属离开皮肤,血液回流,带来一阵麻痒。
我活动了一下僵硬的四肢,戒备地看着他。“好,就算你说的都是真的。”我深吸一口气,
“你需要待在我身边保命。那我呢?我有什么好处?总不能白给你当‘人形解毒剂’吧?
而且,我怎么知道你解毒之后会不会翻脸不认人,甚至…”我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灭口?
”沉舟替我说了出来,他扯了下嘴角,露出一丝没什么温度的笑意,“如果我想,
你现在就不会醒着跟我说话。”他走到旁边的桌子旁,拿起一份文件,递给我。“签了它。
”我狐疑地接过。是一份股权**协议。沉氏集团旗下某个核心科技子公司,5%的股份。
后面跟着一串让我眼晕的零。“这是定金。”沉舟声音没什么起伏,“签了,就是你的。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都不会收回。”我捏着那份轻飘飘又重逾千斤的纸,手指有点抖。
“签了字,我就是你的‘雇主’。”他补充,“在协议期间,
我会尽我所能保障你的安全和利益。你需要做的,就是允许我待在你身边。日常范围,
三米之内。”“三米?”我愕然,“上厕所呢?洗澡呢?”沉舟表情空白了一瞬,
随即恢复冷硬:“我会保持距离,并且…非礼勿视。”“那睡觉呢?”我追问。“我睡沙发,
或者隔壁房间。”他回答得很快,显然早就想过,“不会打扰你。
”我看着他那张写着“我很正经”的冷脸,又低头看看那份天价协议。贫穷,
让我可耻地心动了。“我还有个问题。”我抬头,直视他的眼睛,“是谁给你下的毒?
如果对方知道我能帮你,会不会也冲我来?”这是最大的隐患。
沉舟的眼神骤然变得极其锐利,像淬了毒的冰刃。“是‘那边’的人。”他吐出几个字,
带着刻骨的寒意,“他们想要我死,或者,想把我变成听话的傀儡。
他们暂时不知道你的存在。我会处理干净,不会让他们动你。”“那边?”我皱眉。
“一个藏在暗处的组织。”沉舟没有细说,显然不想让我知道太多,“你只需要知道,
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我活着,你才能安全地拿着你的股份。我死了,
那份协议会立刻生效,钱一样是你的。但‘那边’的人,
未必会放过一个和我有过密切接触的‘普通人’。”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不愧是反派大佬。
我捏着协议,指尖冰凉。签,还是不签?签了,等于把自己和一个定时炸弹绑在一起,
还是自带追杀属性的那种。不签…我瞄了一眼沉舟手腕的方向。他活不下去,
那个什么“那边”组织,真的会放过我这个可能知情的人吗?而且,
眼前这份泼天的富贵…脑子里两个小人疯狂打架。一个说:安幸,快跑!远离麻烦!命重要!
另一个小人挥舞着钞票:签!签了就是富婆!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反派的大腿也是大腿!
最终,钞票小人以压倒性优势胜出。我拿起笔,在乙方签名的位置,
歪歪扭扭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安幸”。希望这个名字,真能带来平安幸运。
沉舟看着我签完,紧绷的下颌线似乎微不可查地放松了一瞬。他接过协议,仔细收好。
“合作愉快,安**。”他伸出手。我看着他那双骨节分明、曾经在梦里掐过我脖子的手,
犹豫了一秒,还是握了上去。冰冷,有力。“沉先生,”我扯出一个假笑,
“希望我们都能…活到愉快的那天。”签下那份“卖身契”后,
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
我搬离了那个月租一千五、没有电梯、蟑螂到处跑的老破小出租屋。沉舟的助理,
一个叫林恪的精英眼镜男,
效率极高地在市中心顶级安保的豪华公寓楼里给我安排了一套大平层。美其名曰:环境安全,
利于“雇主”身心健康。沉舟自己也搬了进来,就住在我隔壁的主卧。
三米距离的“日常范围”开始了。第一天上班。我像往常一样挤地铁?不存在的。
楼下停着沉舟那辆低调奢华的黑色轿车,司机穿着笔挺的制服。
沉舟一身剪裁完美的黑色西装,面无表情地坐在后座。我拉开车门坐进去,
宽敞的后座因为他的存在而显得格外逼仄,空气都冷了几度。“沉先生早。
”**巴巴地打招呼。“早。”他眼皮都没抬,膝盖上放着平板,手指飞快地滑动,
处理邮件。一路无话。车子停在我公司楼下。我刚要推门下车,沉舟终于抬眼:“下班时间?
”“六点…不加班的话。”我老实回答。“嗯。”他应了一声,又低头看平板,
“司机会准时在楼下等你。”“哦。”我推门下车,感觉后背快被他的目光盯穿了。
走进写字楼大厅,我才松了口气。回头,那辆黑色的车还停在原地,车窗降下一半,
沉舟侧脸的线条冷硬,正透过车窗看着我走进电梯间。压迫感如影随形。进了公司,
同事们看我的眼神都变了。“安幸,楼下那车…是沉氏集团总裁的吧?
”隔壁工位的八卦女王凑过来,压低声音,眼神里闪着兴奋的光,“你跟沉总…什么情况啊?
”“没什么情况,”我故作镇定地打开电脑,“就…顺路,搭个便车。”“顺路?
”她显然不信,“沉总住西郊山顶别墅区,咱们公司在东边CBD,这路顺得可够远的!
”我:“……”“哎呀,大家都是姐妹,别藏着掖着嘛!”她撞撞我肩膀,“是不是…嗯?
”她做了个暧昧的表情。我头皮发麻:“真不是!就是…远房亲戚!对,远房亲戚!
他正好来这边办事,捎我一段!”这个借口我自己都不信。果然,一整天,
我都感觉各种探究的、羡慕的、嫉妒的目光在我身上扫来扫去。好不容易熬到下班,
电梯下到一楼。刚走出大门,就看到那辆熟悉的车已经等在了门口最显眼的位置。
沉舟没在车里。他就站在车边。傍晚的霞光给他冷硬的轮廓镀上了一层暖金色,
但他周身的气场依旧生人勿近。路过的行人都不自觉地绕开他走。看到我出来,他迈开长腿,
径直朝我走来。周围下班的人流瞬间安静了不少,无数道目光聚焦在我们身上。
我尴尬得脚趾抠地。他走到我面前,距离刚好卡在三米线内。“可以走了。
”他声音没什么起伏,替我拉开了后车门。我顶着无数道灼热的视线,硬着头皮钻进了车里。
车门关上,隔绝了外面的世界。沉舟坐进来,吩咐司机开车。车厢里一片沉默。
我忍不住吐槽:“沉先生,您其实…不用下车等的。在车里等我就行。”“三米距离。
”他目视前方,语气平淡,“车内空间不足三米。”我:“……”行吧,您严谨。回到家,
更不自在。吃饭。沉舟坐在我对面,慢条斯理地切着牛排,动作优雅得像在拍广告。
我埋头扒饭,尽量降低存在感。“不合胃口?”他突然问。“啊?没有没有,很好吃!
”我连忙摇头。顶级大厨的手艺,能不好吃吗?就是压力太大。“多吃点。
”他把自己面前那盘切好的、几乎没动过的牛排,推到了我面前。我:“……谢谢?
”看电视。我瘫在沙发上,抱着薯片看无脑综艺乐得哈哈笑。沉舟坐在沙发另一头,
捧着一本厚厚的英文原版书,眉头微蹙,仿佛在听什么学术报告。我的笑声戛然而止。
“你随意。”他头也不抬地说。我:“……”更笑不出来了。睡觉。主卧和次卧门对门。
我关门,反锁。竖起耳朵听外面的动静。听到隔壁门开关的声音,然后是浴室隐约的水声。
过了很久,外面彻底安静了。我才敢松口气,把自己摔进柔软的大床里。这日子,
真是富贵险中求,憋屈又**。沉舟倒是严格遵守协议。保持距离,非礼勿视。
除了必要的“三米”接触,他几乎像个幽灵,存在感极强,却又尽量不打扰我。
他的脸色似乎确实好了一点点,虽然依旧苍白,但眼底那种疲惫的死气淡了些。
手腕上的青紫蛛网,蔓延的速度似乎也减缓了。看来我这个“人形解毒剂”效果不错。
平静(且诡异)的日子过了小半个月。爆点来了。那天是周末,沉舟有个推不掉的商业晚宴,
需要女伴。林恪把一套价值不菲的礼服和高跟鞋送到我面前。“安**,
沉总希望您能陪同出席。”我头皮一麻:“我能不去吗?”那种场合,想想就窒息。
林恪推了推眼镜:“沉总说,三米距离。晚宴地点不在协议规定的‘日常安全范围’内,
您单独留在家中,他不放心。”又是该死的三米!我认命地去换衣服。镜子里的女孩,
一身香槟色长裙,剪裁完美,衬得皮肤白皙,身段窈窕。平时扎着的马尾放了下来,
做了个简单的造型,露出光洁的额头和脖颈。我有点认不出自己。沉舟看到我时,
眼神似乎顿了一下,随即恢复如常。“走吧。”他伸出手臂。我犹豫了一下,挽了上去。
第一次如此近距离接触。隔着薄薄的衣料,能感受到他手臂肌肉的紧绷和偏低的体温。
晚宴在城中最贵的酒店顶层。水晶吊灯,衣香鬓影,觥筹交错。沉舟一出现,
立刻成为全场的焦点。恭维声、攀谈声不绝于耳。他游刃有余地应对着,
脸上挂着恰到好处的、疏离的淡笑。我像个挂件一样被他带着,脸上保持着僵硬的微笑,
感觉脸都要笑僵了。“沉总,这位是?”一个脑满肠肥的中年男人端着酒杯过来,
目光毫不掩饰地在我身上打量。“安幸,我的助理。”沉舟语气平淡,
不动声色地把我往他身后带了半步,隔开了那令人不适的目光。“哦?
沉总什么时候换了这么漂亮的助理?”另一个打扮得珠光宝气的女人掩嘴轻笑,
眼神里带着探究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嫉妒,“安**真是好福气。”沉舟没接话,
只是微微颔首,带着我走向另一边。我松了口气,低声道:“谢谢。”他侧头看了我一眼,
没说话。就在这时,一个侍应生端着酒水走过来,脚步似乎有些不稳,
直直地朝着我撞了过来!“小心!”沉舟反应极快,猛地将我往他怀里一拉!
哗啦——托盘上的几杯香槟全泼在了沉舟的背上和手臂上。
冰凉的液体瞬间浸透了他昂贵的西装。“对不起!对不起先生!我不是故意的!
”侍应生惊慌失措地道歉。周围的人都看了过来。沉舟眉头紧锁,脸色阴沉得可怕。
他第一时间不是看自己湿透的衣服,而是低头问我:“有没有溅到?”我被他护在怀里,
一点事没有,只是吓了一跳:“我没事,你…”“沉总!您没事吧?
”晚宴主办方的人急匆匆跑过来,对着侍应生怒斥,“你怎么搞的!”场面有点混乱。
沉舟松开我,脱下了湿透的西装外套递给林恪,只穿着里面的白衬衫。
被打湿的布料贴在手臂上,隐隐透出皮肤下那诡异的青紫色蛛网!虽然只是一闪而过,
但我看得清清楚楚。旁边也有人看到了,发出低低的惊呼。沉舟眼神一厉,
锐利的目光扫过四周。那些探究的视线立刻缩了回去。“没事,意外。
”沉舟对主办方的人说,声音冷得掉冰渣,“失陪一下,我去处理。”他拉着我的手腕,
快步走向休息室的方向。手腕被他攥得有点疼,我能感受到他压抑的怒火。进了休息室,
他反手锁上门。“在这里等我。”他语气生硬,径直走进了里面的洗手间。很快,
里面传来哗哗的水声。他是在冲洗被酒水弄湿的手臂?还是在压抑怒火?我坐立不安。
刚才那个侍应生…真的是意外吗?那个侍应生被带走了,调查结果很快出来:确实是意外,
新来的,太紧张,脚滑了。晚宴继续。沉舟换了一件备用西装出来,神色如常,
仿佛刚才的插曲从未发生。但我能感觉到,他周身的气压更低了。回去的车上,
气氛凝重得能拧出水。“刚才…谢谢你。”我小声说。沉舟闭着眼靠在椅背上,没应声。
他脸色在昏暗的车厢里显得更加苍白,额角似乎有细密的冷汗。“你…是不是不舒服?
”我有点担心。他依旧没说话,只是放在膝盖上的手,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
车开到公寓楼下。司机拉开车门。沉舟先下车,脚步却微不可查地踉跄了一下。
我下意识伸手扶住他的胳膊。入手一片冰凉,还在微微颤抖。“沉舟?
”我第一次叫他的名字。他猛地甩开我的手,力道很大,声音嘶哑:“别碰我!进去!
”我被他吼得一愣。他不再看我,几乎是咬着牙,步伐不稳地快步走进公寓楼。
我赶紧跟上去。电梯里,他背对着我,肩膀紧绷。我能听到他极力压抑的、粗重的喘息声。
叮——电梯门开,他几乎是冲出去的,直奔他的房间。门被重重关上,反锁。我站在走廊里,
听着里面传来压抑的、痛苦的闷哼声,还有东西被扫落在地的碎裂声。是毒素发作了吗?
因为刚才的惊吓?还是因为…那个侍应生的“意外”?我心里沉甸甸的。
原来他平时看似平静,承受的是这样的痛苦。第二天,沉舟没出现。林恪来了,脸色很凝重。
“沉总情况不太好,昨天的意外**到了他体内的毒素。”林恪推了推眼镜,“安**,
沉总吩咐,您今天照常上班,我会负责您的安全。”“他…很严重?”我问。
林恪沉默了一下:“老毛病了,需要静养。安**不必担心,做好您分内的事即可。
”分内的事?就是待在三米范围内当人形解毒剂?可他现在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我连他面都见不着。这一天我过得心不在焉。下班回来,沉舟的房门依旧紧闭。我犹豫再三,
还是热了一杯牛奶,走到他房门前,轻轻敲了敲。“沉先生?你…还好吗?
我热了杯牛奶…”里面一片死寂。过了好一会儿,
才传来他沙哑得不成样子的声音:“…拿走。”“你一天没吃东西了…”“我说,拿走!
”他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暴躁和痛苦,“别管我!”我端着牛奶杯,站在门口,有点无措。
又过了一会儿,里面传来他压抑着喘息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和…自嘲?“安幸,
看到了?这就是你要面对的‘雇主’。一个随时可能失控的怪物。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我握着温热的杯子,沉默了几秒。然后,我蹲下身,把牛奶杯轻轻放在他门口的地毯上。
“牛奶放门口了。”我说,“趁热喝。还有,协议签了,定金我也拿了。现在后悔,
违约金我可赔不起。”说完,我转身回了自己房间。关门。背靠着门板,
我长长地吐出一口气。门外,一片寂静。过了很久,我听到隔壁房门被轻轻打开的声音。
然后是杯子被拿进去,门又轻轻关上的声音。沉舟把自己关了两天。第三天早上,他出来了。
脸色苍白得像纸,眼下有浓重的阴影,但眼神恢复了那种冰冷的锐利,甚至更甚。
他穿着家居服,坐在餐桌旁,安静地吃早餐。看到我,他点了点头,算是打过招呼。
仿佛之前那个失控的、痛苦的夜晚从未发生过。但我注意到,他拿勺子的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