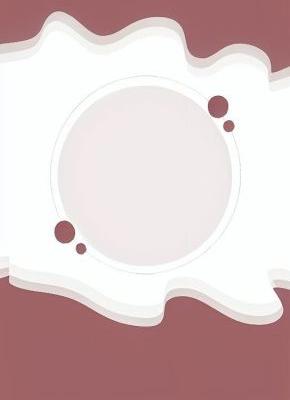
01清晨,薄雾还未被日头彻底驱散,像一层湿冷的纱巾笼罩着连绵的苍翠山峦。
陈默蹲在一处背阴的坡地,手指拂过地面一道浅浅的痕迹,眼神专注而平静。他动作很轻,
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仿佛与这片山林本就一体。很快,
一个利用韧性藤蔓和削尖硬木制成的简易陷阱便在他手中成型,
巧妙地隐藏在枯叶与灌木之下。做完这一切,他目光扫向旁边,
一块百十来斤、长满青苔的巨石不偏不倚地压住了几处可能的兽道。陈默走过去,
腰腹微微下沉,双手扣住巨石底部,臂膀上的肌肉瞬间绷紧,勾勒出硬朗的线条。“起。
”一声几乎听不见的低喝。那巨石竟被他生生搬离地面,稳稳地挪到一旁。
露出下面湿润的泥土和几条惊慌失措的蜈蚣。他拍了拍手上的泥土,气息均匀,
仿佛刚才搬开的不是一块顽石,而是一捆蓬松的干草。这就是陈默,一个被这方山水养育,
却仿佛被抽走了所有喧嚣的年轻人。只有在这深山老林里,
他脸上才偶尔会流露出一丝属于他这个年纪应有的鲜活。这里是他的世界,他的避难所。
城市的喧嚣,人情的冷暖,似乎都被这层层叠叠的绿意隔绝在外。
……记忆像是不请自来的潮水,猛地撞开脑海的闸门。那年他九岁,秋收,
家里的顶梁柱——父亲**在往谷场扛粮袋时闪了腰,瘫坐在金灿灿的谷堆旁,
疼得满脸煞白。“这可咋办啊!这满场的谷子……”母亲王秀娟急得直跺脚,声音带着哭腔。
她看了一眼瘦小的陈亮,当时才六岁的弟弟,正怯生生地抓着她的衣角。最终,
她的目光落在了角落里沉默得像块石头的陈默身上。“小默……你,你去试试。
”王秀娟的语气带着不确定和一丝被逼无奈的指望。陈默没说话,
他走到那比他矮不了多少的粮袋前。那袋子,父亲扛起来都吃力。他学着父亲的样子,弯腰,
双手死死抓住袋口,小脸憋得通红。“嘿!”出乎所有人意料,那沉甸甸的粮袋,
竟真的被他晃晃悠悠地抱离了地面!他脚步踉跄,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
幼小的身体因为极度用力而剧烈颤抖,但他没有停下,咬着牙,一步一步,
硬是将那袋粮食挪到了几十米外的谷场上。“砰!”粮袋落地,扬起一片灰尘。
陈默脱力地坐在地上,大口喘着气,汗水顺着鬓角往下淌,小手被粗糙的麻袋磨出了血痕。
短暂的寂静后,是母亲王秀娟又惊又喜的声音:“老天爷!这娃……这娃力气真大!建国,
你看见没?以后咱家重活可算有人干了!”父亲**捂着腰,龇牙咧嘴地凑过来,
上下打量着儿子,浑浊的眼睛里终于有了点光亮,他用力拍了拍陈默尚且单薄的肩膀,
语气带着一种如释重负的肯定:“好小子!是块干农活的好料!像咱老陈家的人!
”没有人问他累不累,手疼不疼。九岁的陈默,只是抬起脏兮兮的脸,
看着父母脸上久违的、因为“有用”而带来的赞许笑容,他抿了抿嘴,
把那份渴望关怀的心思,和喉咙里的腥甜气息,一起咽回了肚子里。从那天起,
“天生天生神力”这四个字,不再是偶尔被邻里称奇的谈资,成了烙印在他身上的诅咒。
他肩上的担子,一天比一天重。……太阳西沉,将天边染成一片橘红。
陈默提着那只肥硕的野兔,踩着夕阳的余晖回到了坐落在村尾的家。院子里静悄悄的,
灶台冰冷,父母不出意料地不在家。这个时间,
他们应该是去镇上的中学接放假回来的弟弟陈亮了。陈默早已习惯。
他沉默地生火、烧水、处理猎物,动作熟练得像一套演练过千百遍的程序。
当锅里炖肉的香气开始弥漫开来时,院门外传来了说笑声。是父母和弟弟回来了。
母亲王秀娟一脸宠溺地搂着陈亮的肩膀,嘴里不住地问:“小亮,学习累不累?
妈看你都瘦了!晚上想吃什么,妈给你做!”父亲**跟在后面,手里提着弟弟的书包,
脸上是掩不住的骄傲。陈亮穿着干净的蓝白色校服,脸上带着些许舟车劳顿的疲惫,
但眼神清亮,与这个灰扑扑的农家小院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妈,我不累。学校伙食挺好的。
”陈亮笑着回答,声音清朗。王秀娟一进门,就吸了吸鼻子:“哟,炖肉了?
”她自然地走到灶台边,掀开锅盖,浓郁的香气扑面而来。她拿起勺子,
看也没看站在灶膛前的陈默一眼,径自舀起一大块最肥美的兔腿肉,盛到碗里,
塞到陈亮手里。“快,小亮,先吃点垫垫,坐一天车肯定饿坏了。”语气里的热切,
与平时对陈默说话时那种命令式的、理所当然的口吻,判若两人。陈默往灶膛里添了根柴火,
跳跃的火光映着他没什么表情的侧脸。他看着碗里剩下的那些零零碎碎的肉和汤,
又看了看被父母簇拥着、嘘寒问暖的弟弟。他默默地站起身,走到院子的水井边,
打上来一桶冰凉的井水,将那双沾了油污和柴灰的手,浸了进去。井水的寒意,顺着指尖,
一点点蔓延开来。屋里,是温暖的灯光和一家三口的笑语。院里,
是渐浓的夜色和一个少年被拉得长长的、孤独的影子。这,就是他的家。02晚饭时的气氛,
是陈家少有的热烈。桌上那盆兔肉,大半都进了陈亮的碗里。父母不停地给他夹菜,
询问着县中学的新鲜事,询问着考试的排名。陈亮侃侃而谈,什么物理竞赛,什么英语演讲,
那些词汇对陈默来说遥远又陌生,他只是埋头扒拉着自己碗里掺杂着薯块的米饭,
偶尔夹一筷子面前的咸菜。“爸,妈,”陈亮放下筷子,脸上带着压抑不住的兴奋,
从随身带回的书包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厚厚的、印着英文的信封,“我收到了这个。
”“啥东西?”**凑过头,他虽然认不得几个字,但那信封的质感就透着不寻常。
“是国外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梅因斯大学,很有名的!”陈亮的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发颤。
“国外的大学?”王秀娟的声音瞬间拔高,带着难以置信的狂喜,“我的老天爷!
我们家小亮出息了!要出国留洋了!”一瞬间,饭桌上像是炸开了锅。
父母两人围着那张薄薄的纸,反复摩挲,仿佛那是什么稀世珍宝。**咧着嘴,
笑得脸上的皱纹都深了几分。王秀娟更是激动得眼眶发红,一遍遍念叨着“祖坟冒青烟了”。
然而,这股热烈的气氛并没有持续太久。当陈亮犹豫着,
说出每年需要将近十万块的学费和生活费时,空气仿佛瞬间被抽空了。
刚才还洋溢着喜悦和骄傲的堂屋,霎时间落针可闻。“十……十万?
”王秀娟的声音尖利起来,带着破音,“一年?这……这把我们俩这把老骨头砸碎了卖肉,
也凑不出来啊!”**脸上的笑容彻底僵住,慢慢褪去,变成了一种沉重的灰败。
他猛吸了一口廉价的烟卷,烟雾缭绕,遮住了他愁苦的眉眼。他沉默着,一言不发,
只有那紧锁的眉头,诉说着内心的惊涛骇浪。希望有多大,绝望就有多深。
陈亮眼中的光彩也黯淡下去,低着头,手指无意识地抠着桌角的木刺。
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在蔓延。突然,王秀娟像是想起了什么,猛地转过头,
目光灼灼地盯向一直像背景板一样沉默吃饭的陈默。那眼神,带着一种被逼到绝境后的急切,
甚至是一丝不容置疑的索取。“小默……”王秀娟的声音带着刻意的缓和,
却又透着一股难以言喻的压力,“你弟这事……你也看到了,这是天大的好事,
是咱老陈家祖辈都不敢想的光荣!可这钱……”她顿了顿,观察着陈默的反应,
见他依旧低着头,便继续道:“你看,你力气大,身子骨壮实,
现在外面工地挣钱也多……听说一天能挣好几百呢!你弟的前程,
可就……”后面的话她没有明说,但那意思,已经**裸地摊在了桌面上。**也抬起头,
烟雾后的目光复杂地落在长子身上,带着一丝愧疚,但更多的是一种默认的期盼。
陈亮猛地抬头,想说什么:“妈,哥他……”“你闭嘴!”王秀娟打断他,
目光依旧死死锁在陈默身上,“小默,你说句话啊!这可是你亲弟弟!
”陈默扒完了最后一口饭,碗底刮得干干净净。他放下筷子,动作很慢。
他依旧没有抬头看任何人,只是沉默地站起身,椅子腿在粗糙的水泥地上划出刺耳的声响。
他没有回应母亲的话,甚至没有看弟弟一眼,只是转身,
默默地走回了自己那间狭窄、昏暗的偏房。堂屋里,父母对视一眼,
王秀娟的脸上闪过一丝失望和不满,低声嘟囔:“真是个闷葫芦,
一点都不知道为家里着想……”……偏房里,没有开灯。月光透过小小的窗户,
在地上投下一片清冷的光斑。陈默蹲在墙角,伸手在床底摸索着,很快,
他抠开了一块松动的墙砖,从里面取出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盒子很沉。
他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没有别的,只有钱。密密麻麻,皱皱巴巴的钱。有一百的,五十的,
更多的是二十、十块,甚至还有不少一块五毛的硬币。它们被叠得整整齐齐,按照面额分开,
塞满了整个铁盒。这些,是他从十四岁开始,就偷偷攒下的。
农闲时去镇上工地搬水泥、扛钢筋,汗珠子摔八瓣挣来的;上山挖草药、套野味,
走几十里山路去集市上换来的;过年时亲戚给的三块五块压岁钱,他一分也舍不得花,
全都塞进了这里。每一张纸币,都浸透着他的汗水,
承载着他微末而可怜的希望——他曾幻想用这笔钱,去县里学个开车的手艺,或者,
仅仅是给自己买一身像样的、不是捡弟弟剩下的新衣服。冰凉的硬币在他粗糙的指腹间摩挲,
发出细微的声响。黑暗中,他看不清那些钱的颜色,却能清晰地闻到那上面混杂的,
泥土、汗水和钢铁的味道。他就这样蹲在墙角,像一尊凝固的雕像,很久,很久。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一家人坐在桌前吃早饭,气氛依旧沉闷。稀饭冒着热气,
却驱不散每个人心头的阴霾。陈默吃得很快,一如既往。吃完后,
他没有像往常一样立刻起身去下地,而是放下了碗筷。在父母有些疑惑的目光中,
他默默地起身,走回偏房,然后,捧着那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走了出来。他走到饭桌前,
将沉甸甸的铁盒“咚”的一声,放在了父母面前的桌子上。盒盖因为震动弹开,
露出了里面满满当当、码放整齐的钞票。王秀娟和**瞬间瞪大了眼睛,嘴巴微张,
脸上写满了震惊。“给……给我弟。”陈默终于开口,声音低沉沙哑,只有简短的三个字。
说完,他不再看那盒子一眼,也不再看父母那瞬间由惊转喜,甚至带着狂热的脸色,
转身就向院外走去,拿起靠在墙角的锄头,扛在肩上。在他身后,
是父母迫不及待数钱的声音,和压抑不住的、带着颤抖的兴奋低语:“这么多……老天,
这得有多少……”“够了!第一年的肯定够了!小亮,你的学费有了!”“我就说嘛!
小默他还是懂事的!还是知道心疼他弟的!”**数着钱,连说了几个“好”字。
王秀娟更是第一次,用如此温和,甚至带着一丝讨好和释然的语气,
对着陈默的背影喊道:“小默,这个家,多亏有你了!”陈默的脚步没有停顿,
仿佛没有听见。只有陈亮,他看着哥哥沉默扛着锄头走出家门的背影,
又看了看桌上那盒代表着哥哥全部青春和血汗的“学费”,眼圈蓦地红了。他猛地站起身,
冲出院门,朝着陈默的背影大声喊道:“哥!这钱算我借你的!我陈亮对天发誓!
以后出息了,一定百倍千倍还你!!”清晨的薄雾尚未散尽,
陈默扛着锄头的背影在田埂上微微顿了一下,却没有回头,只是继续向前,一步步,
融入了那片灰蒙蒙的晨光里。百倍千倍?他在心里无声地笑了笑。他还不起的。
他拿走的是钱,可他被拿走的,是整整一个少年时代,和所有关于未来的,微末的光。
03省城国际机场,灯火通明,人声鼎沸。陈默第一次来到这种地方,光滑如镜的地板,
高耸得望不到顶的穹窿,还有那些穿着光鲜、步履匆匆的陌生人,
都让他感到一种格格不入的拘谨。他下意识地离那些明亮的玻璃和反光的金属远一些,
生怕自己身上沾染的泥土气息,会玷污了这片过于干净的地界。
父母则完全沉浸在一种混杂着骄傲、不舍与巨大期待的激动情绪中。他们一左一右围着陈亮,
仿佛护着一件稀世易碎的珍宝。“小亮,到了那边,吃的喝的还习惯不?
听说外国人都吃生肉,你可别把肚子吃坏了!
”王秀娟一遍遍地整理着陈亮本就笔挺的衬衫衣领,嘴里絮叨着重复了无数遍的叮嘱,
眼圈泛红。“妈,那是牛排,不是生肉,我知道了,您都说多少遍了。”陈亮有些无奈,
但脸上依旧带着温顺的笑容。**则用力拍着儿子的肩膀,声音洪亮,
带着一种向周围人宣告般的自豪:“好小子!给我老陈家争光了!到了那边,好好学!
别给咱中国人丢脸!钱不够了就跟家里说!”他说这话时,腰杆挺得笔直,仿佛儿子出国,
连带着他的脊梁也硬气了几分。陈默远远地站在一旁,靠在一根冰冷的柱子上,
像一个误入此地的旁观者。他看着那一家三口其乐融融、难舍难分的画面,眼神平静无波。
没有人跟他说话,也没有人看他一眼。他存在的意义,
似乎就是那个装满弟弟行李、此刻被他默默扶着的旧行李箱。广播里响起登机的提示,
催促着前往国际航班的旅客。最后的时刻到了。王秀娟终于忍不住,抽泣起来,
紧紧抱了抱陈亮。**也用力抱了儿子一下,喉头滚动,千言万语只化作一句:“保重。
”陈亮一一回应着,然后,他的目光越过父母,落在了角落里的陈默身上。他顿了顿,
拖着登机箱,穿过熙攘的人群,走到了陈默面前。兄弟俩对视着。一个穿着崭新的行头,
即将奔赴万里之外的锦绣前程;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外套,身后是望不到头的黄土与劳作。
陈亮看着哥哥沉默坚毅却难掩风霜的脸,
看着他扶着自己行李箱的那双布满老茧和细小伤痕的大手,鼻腔猛地一酸。出国留学的喜悦,
在这一刻,被一种沉甸甸的、名为愧疚的情绪压了下去。他忽然张开手臂,
用力地抱住了陈默。陈默的身体瞬间僵住。他不习惯这样的接触,
尤其是这样充满情感的拥抱。他浑身肌肉都绷紧了,像一块硬邦邦的木头。
“哥……”陈亮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带着不易察觉的哽咽,“家里……就拜托你了。
”他抱得很紧,仿佛想通过这个拥抱,传递所有的感激与亏欠。停顿了一下,
他用更低、更真诚的声音,几乎是耳语般说道:“等我站稳脚跟,一定接你出来看看。
”陈默僵硬的身体,微微颤动了一下。他垂在身侧的手,抬了抬,最终,只是很轻、很快地,
在弟弟的背上拍了两下。依旧是什么都没说。陈亮松开了他,深深看了他一眼,拖着行李箱,
转身汇入了安检的人流,背影最终消失在通道的尽头。王秀娟还在抹着眼泪,
**长长舒了口气,像是完成了一件人生大事。他们互相搀扶着,开始往外走,
甚至忘记了站在原地的陈默。陈默看着弟弟消失的方向,看了很久,直到机场广播再次响起,
他才默默地转身,跟上父母的脚步。……弟弟走后,陈家像是被抽走了所有的声音和色彩,
只剩下灰扑扑的劳作。陈默彻底成为了这个家的影子和支柱。天不亮,
他就要起床挑水、喂猪、准备一家人的早饭。日头升起,他便扛着锄头下地,
面对那仿佛永远也锄不完的草,翻不完的地。烈日当空,
他在田埂上啃着冰冷的窝头;夕阳西下,他拖着灌了铅般的双腿回家,
还要劈好第二天用的柴火。而父母的话题,永远围绕着远在重洋的“小亮”。“小亮来信了,
说那边实验室可先进了!”王秀娟拿着信,能反反复复看一整天,逢人便说。
“小亮又拿奖学金了!哎哟,我儿子就是厉害!”**听着电话,
脸上的皱纹笑成了一朵菊花。电话机的旁边,永远摊着一张世界地图,
父母会用手指在上面笨拙地寻找儿子所在的那个点,仿佛那样就能离他近一些。
至于陈默今天累不累,田里的收成怎么样,他们很少过问。
他就像一个无声的、不知疲倦的机器,维持着这个家的运转,而所有的荣耀与期待,
都早已随着飞机,飞到了那个他无法想象的地方。有一次,酷暑难当,
陈默在玉米地里中暑昏倒了,不知过了多久才被路过的人发现,抬回了家。他醒来时,
只觉得头晕目眩,浑身无力。母亲王秀娟端了碗水过来,看着他苍白的脸色,眉头皱着,
说的第一句话却是:“你可算醒了,后山那堆柴还没劈呢,明天万一下雨就麻烦了。
”陈默躺在硬邦邦的板床上,望着黝黑的屋顶,默默地接过那碗水,一饮而尽。水的冰凉,
从喉咙一直滑到胃里,却压不住心底那片早已荒芜的寒意。他撑起依旧虚软的身体,
拿起墙角的斧头,走向后山。“砰!砰!砰!”沉闷的劈柴声,在寂静的山脚下回荡,
一声声,像是在敲打着他早已麻木的青春。04那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黄昏,
夕阳把天边烧成一片凄艳的血红。陈默刚从地里回来,
正蹲在院子的水井边冲洗着腿上的泥点,冰凉的井水**着皮肤,带来一丝短暂的清明。
堂屋里的老式电话机,突然尖锐地响了起来,打破了小院的宁静。王秀娟在围裙上擦了擦手,
嘴里念叨着“谁啊这个时候”,走过去接起了电话。“喂?哪位?”陈默没有在意,
继续冲洗着。然而,母亲接下来的声音,却让他动作猛地一顿。“什么?……大使馆?
……你、你说什么?!小亮他……不可能!你胡说!!”王秀娟的声音陡然拔高,
带着一种撕裂般的惊恐和难以置信。电话听筒从她手中滑落,吊在半空,晃荡着,
里面隐约传来陌生的、公式化的声音。她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骨头,软软地瘫倒在地,
脸色瞬间惨白如纸,嘴唇哆嗦着,却发不出任何完整的声音。“怎么了?!出啥事了?!
”**从里屋冲出来,看到妻子这副模样,心里咯噔一下,急忙捡起听筒。“……您好,
我们很遗憾地通知您,您的儿子陈亮,在梅因斯市遭遇街头抢劫,
不幸……身亡……后续事宜……”“哐当!”**手里的听筒也掉了下去,
重重砸在桌子上。他高大的身躯晃了晃,猛地向后踉跄一步,撞在墙上,才勉强没有倒下。
他张着嘴,眼睛瞪得滚圆,里面全是空洞和茫然,仿佛听不懂那些词语组合在一起的意思。
死了?小亮……死了?那个他们全家人的骄傲,那个光宗耀祖的未来,
那个他们倾尽所有、寄予厚望的儿子……没了?院子里死寂一片,只有那晃荡的听筒里,
还传出细微的、冷漠的声音。陈默维持着蹲着的姿势,手里的水瓢歪了,
剩余的井水泼了一地,浸湿了他的裤脚。他缓缓抬起头,
看向堂屋里那两张瞬间失去所有生气的脸,
看向那悬在半空、仿佛吊着这个家最后一丝希望的听筒。他没有动,也没有说话,
就那么蹲着,像一尊瞬间风化的石雕。夜色,如同浓稠的墨汁,
迅速吞噬了天边最后那抹血色,将整个小院,连同里面所有的悲伤和绝望,一同吞没。
……接下来的几天,陈家像是在办一场无声的丧事。没有遗体,没有棺椁,
只有大使馆寄回来的一些遗物和一个冰冷的骨灰盒。王秀娟抱着那个小小的盒子,
哭晕过去好几次,醒来就又接着哭,声音已经嘶哑得不成样子。
**仿佛一夜之间老了二十岁,头发白了大半,整日坐在门槛上,对着空荡荡的院子抽烟,
眼神浑浊,没有焦点。陈默沉默地处理着所有后续的事情,联系,确认,
接收骨灰……他像一个没有感情的傀儡,机械地完成着一切程序。他瘦了很多,眼窝深陷,
但脊梁依旧挺得笔直,撑着他,也撑着这个即将彻底倾塌的家。所有的悲伤、愤怒和不解,
都被一种巨大的、不真实的空洞感取代。直到那天傍晚。夕阳再次落下,屋里没有开灯,
昏暗得如同墓穴。王秀娟呆呆地坐在椅子上,怀里紧紧抱着陈亮的遗照,
照片上的年轻人笑容灿烂,与现实形成残酷的对比。
陈默正默默地收拾着晚饭后几乎没有动过的碗筷,动作轻缓,尽量不发出声音。突然,
王秀娟抬起头,她的目光从照片上移开,落在了陈默的背影上。那目光,起初是空洞的,
然后,一点点凝聚起一种令人心悸的寒意,掺杂着无尽的悲痛和一种扭曲的怨毒。
“为什么……”她开口了,声音嘶哑得像砂纸摩擦,在寂静的屋里异常清晰。
陈默收拾碗筷的动作,骤然停顿。他的背脊,微不可查地绷紧了。王秀娟猛地站了起来,
椅子腿在地上刮出刺耳的噪音。她死死盯着陈默,眼神像淬了毒的刀子。
“为什么死的不是你?!”她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种歇斯底里的疯狂,
“你除了有一身傻力气,你还会什么?啊?!”陈默僵硬地站在原地,背对着母亲,
一动不动。他能感受到那目光,如同实质,要将他的背脊灼穿。
“你为什么就不能像你弟一样会读书!你为什么不能跟他一起去!!
”王秀娟像是找到了悲伤的宣泄口,所有的绝望和失去理智的怨恨,如同决堤的洪水,
朝着眼前这个沉默的儿子倾泻而去,“你要是也跟着去了,
说不定……说不定就能替他挡了那刀!死的就是你了!!”她冲上前,用尽全身力气,
拳头如同雨点般捶打在陈默坚硬的后背上,发出沉闷的“砰砰”声。“为什么我的小亮死了,
你却还好好地站在这里!为什么!!!”嘶吼声在昏暗的堂屋里回荡,每一个字,
都像一把烧红的铁锥,狠狠凿进陈默的心脏。角落里,父亲**双手死死捂着脸,
肩膀剧烈地颤抖着,他没有阻止,没有反驳,只有压抑的、痛苦的呜咽声从指缝里漏出来。
他的沉默,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陈默缓缓地,缓缓地转过身。
他没有看状若疯魔的母亲,也没有看崩溃沉默的父亲。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没有愤怒,
没有悲伤,甚至没有一丝波澜。只有一片死寂的、彻骨的冰冷。他就用这样一双空洞的眼睛,
看着王秀娟因为激动和怨恨而扭曲的面容。那些诛心之言,仿佛不是打在他身上,
而是打在一块早已失去知觉的木头上。他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从母亲身边走过,
无视了她依旧在挥舞的拳头和尖锐的哭嚎,一步一步,走出了这个令人窒息的家门。屋外,
夜色浓重。他走到屋后那个熟悉的小山坡上,面向着弟弟飞机离开的方向,慢慢地坐了下来。
夜风吹拂着他粗硬的头发,带来远处田野里泥土的气息。他就那样坐着,像一座沉默的山。
脸上干干的,一滴眼泪都没有。只是那双在黑暗中依旧亮得惊人的眼睛里,
最后一点属于“家”的微光,啪嗒一声,彻底熄灭了。05天光撕破云层,
将冰冷的光芒洒向沉寂一夜的大地。陈默从屋后的山坡上站起身,
露水打湿了他的肩头和发梢,带来浸骨的寒意。他活动了一下因为久坐而有些僵硬的身体,
关节发出细微的咔哒声。脸上没有任何彻夜未眠的疲惫,只有一种近乎残忍的平静。
他走下山坡,回到那个刚刚经历了一场情感风暴的家。母亲王秀娟大概是哭累了,
歪在里屋的床上,发出不均匀的鼾声,脸上还带着泪痕。父亲**依旧坐在堂屋的门槛上,
脚边散落着一地烟头,眼神空洞地望着院子,对陈默的进出毫无反应。这个家,
像是被抽走了灵魂,只剩下悲伤和怨恨的空壳。陈默没有看他们,径直走向偏房,
拿起靠在墙角的锄头和柴刀,像过去的千百个清晨一样,沉默地走出了家门。
他没有去常去的那几块地,而是走向了离家更远、土质也更贫瘠的坡地。
那里还有最后一点晚玉米,稀稀拉拉地立在干硬的黄土地上。他挥舞起锄头,
动作依旧精准有力,刨开板结的土块,清理着杂草。汗水很快从额角渗出,
顺着坚毅的脸颊轮廓滑落,滴在干涸的土地上,瞬间消失无踪。他干得极其认真,极其专注,
仿佛在进行一场庄严的仪式。每一锄头落下,
都像是在与这片生养他、也禁锢了他的土地做最后的告别。接下来的几天,都是如此。
他不再与父母同桌吃饭,总是在他们吃完后,才默默地去厨房吃点剩饭。
他不再与他们有任何眼神交流,甚至不再发出任何不必要的声响。他像一个幽灵,
一个只知道劳作的机器,在这个家里,在自己的生命中,彻底隐形。
他将地里所有能收获的庄稼都收了回来,仔细地脱粒、晾晒。然后,他独自拉着板车,
走了几十里山路,去到镇上的粮站,将所有的粮食都卖掉了。当他将那一叠不算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