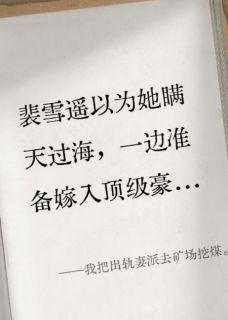
寒风。像无数把裹着冰碴的钝刀,刮骨剔髓。每一次呼吸,都像吸进一肺的碎玻璃,
从喉咙一直割到胸腔深处。空气稀薄而冰冷,
每一次喘息都在眼前凝成一小团转瞬即逝的白雾。伊尔库茨克州,第17号矿场。
这里没有季节,只有永恒的酷寒和灰暗。铅灰色的天空低低地压着,仿佛永远不会放晴。
广袤的冻土荒原被厚厚的、肮脏的积雪覆盖,
只有矿坑巨大的、狰狞的裂口像大地丑陋的伤疤,吞噬着一切。矿坑边缘,
简陋的木质工棚歪歪斜斜地立着,在呼啸的狂风中发出不堪重负的**。
穿着厚重、沾满油污和煤灰的破旧棉衣的矿工们,像一群被驱赶的、麻木的牲口,
排着歪歪扭扭的队伍,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没过小腿的积雪,走向那个深不见底的矿坑入口。
沉重的铁镐和矿筐压弯了他们的脊背。裴雪遥就在队伍的最后面。
她裹在一件比她身形大了不止两号、散发着浓重汗臭和霉味的破棉袄里,臃肿不堪。
曾经精心养护的长发被胡乱地剪短,参差不齐地贴在冻得通红的耳朵和脸颊上,
沾满了黑色的煤灰。脸上没有任何妆容,皮肤粗糙皲裂,布满了被寒风吹出的血口子,
嘴唇干裂发紫。那双曾经漂亮的杏眼,如今只剩下两个空洞,
里面盛满了死寂的麻木和挥之不去的恐惧。
她的脖子上套着一个沉重的、用粗铁链连接的生铁项圈,
项圈的另一端锁在一个同样穿着破烂棉衣、眼神凶狠的监工手里。
她的双手被一副粗糙的铁铐铐着,手腕早已被磨破,结了厚厚的血痂,又被冻裂,
露出里面鲜红的嫩肉。每走一步,脚踝上沉重的脚镣就拖在雪地里,
发出哗啦哗啦的刺耳声响。寒风像鞭子一样抽打在她**的皮肤上,刺骨的疼痛。
但她感觉不到。或者说,身体上的一切痛苦,
都比不上心底那片早已冰封的、名为绝望的荒原。“快点!磨蹭什么!找打是不是!
”身后的监工猛地一拽手里的铁链!“呃!”项圈勒紧喉咙的剧痛让裴雪遥一个踉跄,
差点扑倒在冰冷的雪地里。她赶紧稳住身体,麻木地加快了一点脚步,
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脚上的冻疮早已溃烂流脓,和破烂的、塞着乌拉草的鞋子黏在一起,
每一次移动都带来钻心的疼痛。但她只是咬紧了牙关,连闷哼都没有发出一声。眼泪?
早就流干了。从她被像货物一样塞进那架冰冷的运输机,被剥掉所有华服首饰,
被套上这身肮脏的囚服和镣铐,被丢进这个连地狱都不如的冰窟窿开始,
她的眼泪就已经流干了。父亲倒在血泊中的脸,母亲被拖走时撕心裂肺的哭喊,
教堂里那些刺目的闪光灯和鄙夷的目光,
厉堇寒那双冰冷得如同看死物的眼睛……这些画面像噩梦一样日夜纠缠着她,
啃噬着她残存的意识。悔恨?有。恨?滔天的恨!但在这无边的寒冷和永无止境的苦役面前,
所有的情绪都被冻僵了,只剩下求生的本能和深入骨髓的恐惧。队伍终于挪到了矿坑入口。
一股混杂着劣质**硝烟味、粉尘和腐烂木头气味的、更加阴冷潮湿的空气扑面而来,
像巨兽的呼吸。监工粗暴地解开裴雪遥项圈上的铁链,把她往前一推:“滚下去!
今天完不成定额,别想吃饭!也别想从那个冰窟窿里出来!”裴雪遥被推得向前踉跄几步,
差点滚下陡峭的矿道。她扶住冰冷的、滴着水的岩壁站稳。矿道深处一片漆黑,
只有远处矿工头盔上微弱的矿灯像鬼火一样摇曳。深处传来沉闷的凿击声和模糊的咳嗽声。
她麻木地弯下腰,用戴着沉重铁铐的手,
艰难地拖起一个几乎到她腰部那么高的、沾满煤灰和冰碴的巨大藤条筐。
筐的重量压得她本就冻僵的双腿一阵发软。她深吸了一口混杂着粉尘的冰冷空气,
肺部传来撕裂般的疼痛。她咬紧牙关,拖着沉重的筐,一步一步,
艰难地挪向那深不见底的黑暗。矿道崎岖湿滑,头顶不断有冰冷的滴水落下,砸在脖颈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