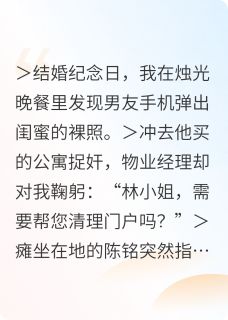
>结婚纪念日,我在烛光晚餐里发现男友手机弹出闺蜜的**。>冲去他买的公寓捉奸,
物业经理却对我鞠躬:“林**,需要帮您清理门户吗?
”>瘫坐在地的陈铭突然指着我尖叫:“她哪有钱买这里的房子!
”>婚礼上太子爷当众吻我:“介绍一下,我家晚晚三年前就是业主。”>前男友破产那天,
我摸着孕肚看闺蜜在街边发传单。>手机亮起银行入账提示:顾太太,
您名下房产本月租金已到账。---烛光在昂贵的骨瓷碟子边缘跳着舞,
把盘子里五分熟的牛排染成一种暖融融的、近乎虚假的金色。
空气里漂浮着黑胡椒酱汁的醇厚香气,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玫瑰香氛味道——是我特意挑的,
和陈铭当初追我时送的第一束玫瑰一个牌子。三周年纪念日。
我甚至穿了那条他夸过“像仙女下凡”的雾霾蓝长裙,
后背镂空的设计让我**的皮肤在冷气里起了一层细小的鸡皮疙瘩。
指尖捏着冰凉的香槟杯脚,杯壁上凝结的水珠慢慢滑下来,洇湿了铺在膝盖上的餐巾。
陈铭坐在我对面,手机屏幕的光时不时映亮他的下巴。他手指在屏幕上划得飞快,
嘴角偶尔抽动一下,那弧度我很熟悉,通常只出现在他和苏晴发消息的时候。“晚晚,
尝尝这个鹅肝,新换的厨师,听说不错。”他终于放下手机,拿起刀叉,
动作带着点刻意表演出来的优雅,银质餐刀切下去,鹅肝软糯的质感被破坏,
露出内里细腻的纹理。“嗯。”我把一小块鹅肝送进嘴里。
顶级食材特有的丰腴油脂感在舌尖化开,本该是极致享受,此刻却味同嚼蜡。我的视线,
总是不受控制地瞟向他放在桌边、屏幕朝下的手机。刚才他起身去洗手间,
手机就那样随意地搁着,像个无声的潘多拉魔盒。“怎么了?心不在焉的。”陈铭抬起头,
灯光落在他精心打理过的头发上,衬得他今天格外英俊。他伸出手,越过桌子想握住我的手。
我下意识地缩了一下,指尖划过冰冷的酒杯。他的动作顿在半空,
眼里飞快地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不耐烦,随即又被温存的笑意覆盖。
“还在生我上个月没陪你过生日的气?项目太赶了,宝贝,你也知道,
我这么拼不就是为了早点给你一个家?看,这地方多好。
”他环顾着这间人均消费四位数的高档餐厅,语气里带着一种施舍般的满足感。
为了早点给我一个家。这句话像根淬了毒的针,扎得我心脏猛地一缩。我扯了扯嘴角,
露出一个大概比哭还难看的笑:“没有,就是……有点累。”就在这时,
他那该死的手机屏幕猝然亮起,刺眼的白光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们之间伪装的温情。
一条新消息提示,毫无遮挡地跳在锁屏界面上。发件人:晴晴宝贝。内容预览只有一行字,
却像烧红的烙铁,狠狠烫在我的视网膜上:【照片收到了吗?
你上次说喜欢我穿那套黑色的……在你买的公寓床上拍的,有感觉吗?
】嗡——世界瞬间失声,只剩下血液疯狂冲上头顶的轰鸣。我浑身的血液好像瞬间冻住了,
又在下一秒轰然燃烧,烧得我指尖都在颤抖。照片?黑色?公寓床?苏晴?晴晴宝贝?
每一个词都像一把淬了毒的匕首,精准地捅进我的心窝。
那张被陈铭夸赞过无数次、显得温柔又无害的脸,此刻在我脑海里扭曲变形,
只剩下**裸的、带着嘲讽的背叛。陈铭显然也看到了那条消息。
他脸上的血色“唰”地褪尽,比餐厅惨白的桌布还要难看。他猛地伸手去抓手机,
动作快得带倒了手边的红酒杯。“晚晚!你听我解释!”他声音尖利,
带着一种走投无路的恐慌。猩红的酒液泼洒出来,如同淋漓的鲜血,瞬间染红了洁白的桌布,
蜿蜒着向边缘滴落。刺目的红,像极了此刻我心口裂开淌出的东西。解释?
我看着他那张写满慌乱和心虚的脸,胃里一阵翻江倒海的恶心。所有的深情,所有的承诺,
所有为了“我们的家”而拼搏的借口,都在这条**裸的消息面前碎成了齑粉,
成了最恶心的笑话。“啪!”我扬手,狠狠甩了他一记耳光。
清脆响亮的声音在安静的餐厅里炸开,旁边几桌的窃窃私语瞬间停滞。掌心**辣地疼,
却远不及心口万分之一。陈铭被我打得偏过头去,脸上迅速浮起一个清晰的掌印。他捂着脸,
眼神里充满了难以置信和怨毒。我没再看他一眼。抓起自己放在椅背上的包,
指甲深深掐进柔软的皮革里。转身,高跟鞋踩在光洁的大理石地面上,
发出急促而清脆的“哒、哒、哒”声,每一步都像是踩在自己碎裂的心上。
眼泪在眼眶里疯狂打转,视线一片模糊,但我死死咬着下唇,
硬生生把那股灭顶的酸楚和软弱憋了回去。哭?为这种垃圾?他不配!冲出餐厅大门,
夏夜温热的晚风扑面而来,却吹不散我胸腔里那团冰冷的火焰。我抖着手在路边拦车,
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一个疯狂燃烧、足以焚毁一切的念头:去那个公寓!
去亲眼看看这对狗男女精心布置的“爱巢”!去把他们的遮羞布彻底撕烂!“师傅,
”我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报出那个地址时,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金茂府,
A栋,麻烦快点!”司机大概是被我惨白的脸色和浑身散发的戾气吓到了,一脚油门,
车子猛地窜了出去。窗外的霓虹飞速倒退,流光溢彩,却照不进我此刻一片漆黑的心底。
金茂府……那是本市最顶级的公寓之一,寸土寸金。陈铭不止一次在我面前,
带着一种隐秘的炫耀提起他租了那里的房子,说是为了“离客户近”、“谈生意方便”。
现在想来,每一个字都裹着精心伪装的糖衣,里面全是砒霜。原来他所谓的“拼搏”,
所谓的“给我们的家”,就是用我这些年省吃俭用、甚至偷偷接私活攒下的钱,
去租下金碧辉煌的牢笼,和苏晴在里面颠鸾倒凤!车子猛地刹住,
司机小心翼翼地提醒:“**,金茂府A栋到了。”我甩下一张钞票,甚至没等找零,
推开车门就冲了下去。眼前是熟悉的、灯火通明的入户大堂,
巨大的落地玻璃映出我此刻狼狈的身影——精心打理的头发有些凌乱,
昂贵的裙子沾染了点点红酒渍,脸色惨白,眼睛却烧得通红,像一头被逼到绝境的困兽。
深吸一口气,那冰冷的、带着昂贵香薰味的空气涌入肺腑,
反而让我胸腔里的怒火燃烧得更加炽烈。我挺直背脊,踩着七厘米的高跟鞋,
像个奔赴战场的士兵,径直走向那扇需要刷卡或业主确认才能进入的玻璃门。
保安是个生面孔,年轻小伙,见我气势汹汹地冲过来,下意识地拦了一下:“女士,
请问您……”“我找人!A栋2801!陈铭!”我几乎是用吼的,声音嘶哑,
带着一种豁出去的决绝。保安被我的样子震慑住,犹豫了一下,
还是拿起内线电话准备联系住户确认。就在这时,
旁边穿着深色西装、胸前别着经理铭牌的中年男人快步走了过来。他先是疑惑地看了我一眼,
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几秒,随即眼神猛地一亮,
脸上瞬间堆满了无比热情、甚至带着点恭敬的笑容。“林**?”他微微欠身,
语气熟稔又带着明显的讨好,“是您啊!您怎么亲自过来了?这大晚上的,
是有什么东西需要处理吗?还是……?”他的目光在我身后的方向扫了一眼,
似乎在寻找什么,随即又落回我脸上,带着询问和十二分的殷勤。林**?
这个称呼像一道惊雷,劈得我浑身一僵,满腔的怒火和悲愤都凝固了一瞬。
我茫然地看着眼前这张堆笑的脸,完全想不起在哪里见过他。物业经理?他认识我?
还叫我“林**”?保安也愣住了,拿着话筒的手僵在半空,看看经理,又看看我,一脸懵。
经理似乎没察觉我的异样,或者说,他把我此刻的僵硬理解成了别的情绪。他搓了搓手,
身体又放低了些,声音压得更低,带着一种心照不宣的体贴,
甚至做了个“请”的手势:“您别生气,消消火。需要我这边……嗯,帮您‘清理门户’吗?
您一句话的事!保证处理得干干净净,不脏了您的地方!”清理门户?不脏了我的地方?
这几个字像烧红的烙铁,狠狠烫在我混乱一片的脑海里。一股极其荒谬、极其冰冷的预感,
瞬间攫住了我。我的呼吸骤然停住,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擂鼓,几乎要撞碎肋骨。
一个连我自己都觉得疯狂的念头,不受控制地冒了出来。难道……?我张了张嘴,
喉咙干涩得发不出任何声音。只能死死地盯着物业经理那张殷勤备至的脸,
试图从他的表情里找到一丝一毫开玩笑的痕迹。没有。
只有绝对的恭敬和一丝“我懂您”的了然。电梯平稳上升的数字像在倒计时,
跳动着令人窒息的节奏。28楼到了。金属门无声滑开,铺着厚厚地毯的走廊寂静无声,
只有顶灯散发出柔和却冰冷的光。2801的门牌就在眼前。那扇深胡桃木色的门,
此刻像一张紧闭的、嘲笑着我的嘴。我所有的力气仿佛都在楼下被抽空了,
只剩下一种近乎麻木的冰冷,支撑着我抬起手,按响了门铃。一声,又一声,
急促得如同我濒临崩溃的心跳。门内传来窸窸窣窣的动静,
夹杂着女人压低的不耐烦:“谁呀?这么晚了……”门开了。
一股混合着廉价香薰、情欲和暧昧的味道扑面而来。
苏晴身上只裹着一条一看就是临时抓来的浴巾,湿漉漉的头发贴在颈侧,
**的肩膀和锁骨上还留着几处新鲜的暧昧红痕。她脸上那种被打扰好事的不悦,
在看到门外站着的我时,瞬间凝固,
然后扭曲成一种混合着震惊、慌乱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林……晚晚?
”她声音拔高了,带着难以置信的尖锐,“你怎么找到这里来的?!”我没理她,
视线越过她颤抖的肩膀,直直投向屋内。客厅里一片狼藉。昂贵的真皮沙发上,
凌乱地丢着男人的衬衫、女人的蕾丝内衣。空气中弥漫着情事过后的粘腻气息。
陈铭正手忙脚乱地套着裤子,皮带扣发出哗啦的脆响。他看到我,动作猛地僵住,
脸上血色尽失,嘴唇哆嗦着,眼神像见了鬼。“晚晚?!你……你怎么……”他语无伦次,
裤子拉链都没拉好,狼狈不堪地冲过来,试图把苏晴挡在身后,
好像这样就能遮住他们**裸的背叛。“你听我说,不是你看到的那样!
我们……”“不是什么?”我的声音平静得可怕,连我自己都感到陌生。
那是一种被极致的痛苦和荒谬冻结后的死寂。我一步一步走进这个奢华却肮脏的空间,
高跟鞋踩在光洁的地板上,发出清晰的叩响,每一步都像踩在冰面上。
目光缓缓扫过那些刺目的凌乱,最终定格在茶几上。那里,
随意扔着一个深蓝色的丝绒首饰盒,盖子打开着。里面躺着的,
赫然是上个月我在苏晴手腕上见过的那只卡地亚玫瑰金镶钻手镯!
当时她还一脸甜蜜地跟我说是“朋友送的”。朋友?呵。我的目光只在那手镯上停留了一瞬,
便移开了,像看着什么令人作呕的垃圾。最后,落在了陈铭那张因惊恐而扭曲的脸上。
“陈铭,”我的声音不大,却像淬了冰的刀子,清晰地割开室内的死寂,“你刚才在楼下,
是不是问我‘哪来的钱买这里的房子’?”陈铭猛地一颤,似乎没料到我会突然提起这个。
他下意识地张嘴,想说什么。我扯了扯嘴角,那弧度冰冷,毫无笑意。我抬起手,
没有指向任何具体的物件,只是对着这间装修奢华、此刻却弥漫着情欲和背叛气息的公寓,
轻轻划了一个圈。“忘了告诉你们,”我的声音很轻,
却带着一种足以碾碎他们所有骄傲的平静力量,“这里,是我的房子。
”时间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空气凝固了。苏晴脸上那点强装的镇定和隐隐的得意,
瞬间碎裂。她裹着浴巾的身体晃了一下,眼睛瞪得滚圆,死死地盯着我,
仿佛第一次认识我这个人。“什……什么?”她失声叫出来,声音尖利得变了调,
“你的房子?林晚你疯了吧!你知道这里多少钱一平吗?你知道……”陈铭的反应更直接。
他像是被一记无形的重锤狠狠砸在胸口,踉跄着后退一步,后背“砰”地撞在冰冷的墙壁上。
他脸色灰败,嘴唇剧烈地哆嗦着,眼神里充满了极度的震惊和一种被彻底打败认知的茫然。
他张着嘴,喉咙里发出嗬嗬的、无意义的声响,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苏晴像是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她猛地松开抓着浴巾的手,
任由那单薄的布料往下滑了几分也顾不上,激动地指着我的鼻子尖叫,
“林晚你少在这里装神弄鬼!陈铭都告诉我了,这房子是他租的!
是他辛苦赚钱租来准备和你结婚用的!你嫉妒!你就是嫉妒我和他……”“租?
”我轻轻打断她歇斯底里的尖叫,那声音里的冰寒让她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哆嗦。我的目光,
带着一种近乎悲悯的嘲讽,缓缓落在陈铭那张惨无人色的脸上。“陈铭,你告诉她,
你每个月那点可怜的工资,去掉吃喝玩乐、去掉给你爸妈寄的、去掉给她买包买首饰的,
”我的视线扫过苏晴手腕上那个刺眼的卡地亚手镯,“剩下的,够租这里一个厕所吗?
”陈铭的身体猛地一颤,像是被剥光了所有伪装,赤条条地暴露在刺眼的灯光下。
他眼神躲闪,不敢看我,也不敢看苏晴,只是死死地盯着地面,额头上渗出大颗大颗的冷汗。
“还有你,苏晴,”我转向她,声音冷得像西伯利亚的寒风,“你身上这件浴袍,
是爱马仕的吧?去年生日我送你的。你手上这个镯子,刷的我的副卡。甚至你刚才喷的香水,
也是去年圣诞节我让陈铭转交给你的。”我往前逼近一步,看着她血色尽褪的脸,
“用着我的东西,睡着我的人,在我的房子里,感觉如何?**吗?”每一个字,
都像一把烧红的锥子,狠狠扎进苏晴的心口。她脸上的血色褪得干干净净,
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裹在身上的浴巾摇摇欲坠。她下意识地捂住手腕上的镯子,
仿佛那是什么烫手的烙铁。她惊恐地看着我,嘴唇翕动着,却再也发不出任何声音,
只剩下牙齿打颤的咯咯声。巨大的羞辱和恐惧,像冰冷的潮水,瞬间将她淹没。
陈铭像是被我的话彻底抽走了骨头,顺着墙壁,整个人瘫软下去,
狼狈地跌坐在冰冷的地板上。他双手抱着头,发出压抑的、野兽般的呜咽。什么精英形象,
什么未来可期,此刻碎了一地,只剩下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和背叛者的狼狈。
我冷冷地看着地上那滩烂泥一样的男人,再看看旁边抖得如同风中落叶、满眼惊恐的苏晴。
胸腔里那股灭顶的愤怒和悲伤,奇异地沉淀了下去,只剩下一种冰冷的、近乎虚无的疲惫。
“物业的人马上上来。”我平静地开口,声音里听不出任何波澜,“请你们,立刻、马上,
带着你们这些……”我厌恶地扫了一眼沙发上那些刺目的衣物,“垃圾,滚出我的房子。
”说完,我甚至懒得再看他们一眼,转身走向门口。就在我手指触碰到冰冷的门把手时,
身后传来苏晴崩溃的尖叫:“林晚!你这个骗子!你一直在耍我们!你不得好死!
”脚步顿住。我缓缓转过身,走廊明亮的灯光勾勒出我挺直的背影。我微微侧头,
余光扫过那张因嫉妒和恨意而扭曲的脸。“不得好死?”我轻轻重复了一遍,
唇角勾起一个极淡、极冷的弧度,“比起用着闺蜜的钱,睡着她男人,
还在她买的房子里搞破鞋的人……我觉得,我至少能死得体面点。”门在我身后轻轻关上,
隔绝了里面歇斯底里的哭嚎和咒骂。走廊里一片死寂,只有我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
孤独而清晰地回荡。靠在冰冷的电梯轿厢壁上,全身的力气仿佛瞬间被抽空。
刚才强撑起来的坚硬外壳寸寸龟裂,露出里面血肉模糊的伤口。眼泪终于失控地涌了出来,
大颗大颗地砸在手背上,滚烫,又迅速变得冰凉。我死死咬住嘴唇,尝到一丝咸腥的铁锈味,
才勉强压住喉咙里翻涌的呜咽。电梯直达地下车库。我像个游魂一样,
凭着记忆走向我那辆低调的白色代步车。手抖得厉害,车钥匙几次都没**锁孔。
“滴——滴——”刺耳的汽车鸣笛声在空旷的车库里突兀地炸响。我茫然地抬起头,
刺目的车灯晃得我眼睛生疼。一辆线条冷硬、通体漆黑的宾利添越,
正以一种极其霸道的姿态,斜斜地插在我车头前面,几乎堵死了我出去的路。车窗缓缓降下。
驾驶座上的人微微侧过头。车库顶灯的光线落在他轮廓分明的侧脸上,
勾勒出高挺的鼻梁和线条清晰的下颌。他穿着一件质地精良的深灰色衬衫,
袖子随意地挽到小臂,露出一截结实的手腕和一块我认不出牌子但绝对价值不菲的腕表。
他的目光很平静,带着一种久居上位者特有的审视感,落在我泪痕狼藉的脸上,停留了两秒。
那眼神里没有同情,没有好奇,只有一种纯粹的、不带情绪的观察。“抱歉。”他开口,
声音低沉悦耳,像大提琴的弦音,在空旷的车库里带着奇异的回响。那道歉听起来毫无诚意,
反而更像是一种陈述。“司机技术不太好,挡你路了。稍等。”他推开车门,长腿迈出。
身高带来的压迫感瞬间扑面而来。他绕到车尾,对着后面跟着的一辆小型厢货摆了下手。
几个穿着统一制服的搬运工人立刻小跑着下来,开始小心翼翼地卸货——看包装,
像是一架昂贵的三角钢琴。他本人则径直走向我这边,步履沉稳,带着一种掌控一切的气场。
“需要帮忙?”他在距离我两步远的地方站定,目光扫过我还在微微发抖的手和车钥匙。
“不用。”我的声音沙哑得厉害,带着浓重的鼻音。我别开脸,不想让他看到我此刻的狼狈。
只想快点离开这个鬼地方,找个没人的角落,舔舐自己血淋淋的伤口。
他似乎并不在意我的拒绝,目光反而越过我,投向车库入口的方向。那里,
一个极其狼狈的身影正跌跌撞撞地冲进来,
怀里还抱着一大束……看起来已经有点蔫了的红玫瑰?是陈铭。他头发凌乱,眼眶红肿,
昂贵的衬衫皱巴巴的,扣子还扣错了一颗。他显然是一路追下来的,跑得气喘吁吁,
看到我的车,眼睛猛地一亮,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不管不顾地就冲了过来。“晚晚!
晚晚你听我说!”他声音嘶哑,带着哭腔,扑到我的车门前,
把那束蔫头耷脑的玫瑰胡乱往我怀里塞,“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是苏晴!
都是那个**勾引我!我一时糊涂……晚晚,你原谅我这一次!我们这么多年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