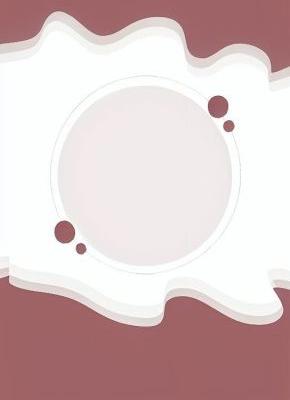
缴费单第三行写着自费六万八。塑料椅冰凉,硬得硌人。空气里消毒水味儿混着汗味,
还有股若有若无的过期面包的酸气。隔壁小孩在哭,声音尖利,像指甲刮铁皮。
沈确站在缴费窗口前,背影挺直,昂贵的羊绒大衣沾了点灰,格格不入。他的手机屏幕亮着,
停留在和鹿夭的聊天界面。最新一条语音,
“阿确…别管我了…我…我可能撑不过去了…你和皎皎好好的…”沈确的手指在屏幕上收紧,
骨节发白。他没回头看我,声音干涩:“皎皎,这笔钱…算我借你的。夭夭那边…等不起了。
”鹿夭。沈确心尖上那抹永恒的白月光。半个月前突然“病危”,查不出具体病因,
一天天虚弱下去,昂贵的进口药流水一样用。沈确的流动资金全砸了进去,
现在轮到动我们婚房的首付。我把手里揉得发皱的缴费单展开,盯着那个刺眼的数字。
六万八。够我买下看中很久的那台专业相机,够我妈半年理疗费,
够我付清下季度工作室的租金。现在,它要变成鹿夭病床边一瓶又一瓶的点滴,
流进她苍白的手背。“好。”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卡在我包里。
密码是你生日。”沈确猛地转过身,眼底有血丝,也有松了口气的感激。“皎皎,
你…你真是太好了!等夭夭好起来,我们…”“先去缴费吧。”我打断他,低头拉开包链。
金属卡扣冰凉的触感贴着指尖。鹿夭住VIP单人病房。推门进去的时候,
空气里飘着高级香氛的味道,掩盖了医院特有的气味。她靠坐在床上,长发散落肩头,
衬得一张小脸毫无血色,嘴唇淡得像褪了色的花瓣。看到沈确身后的我,长长的睫毛颤了颤,
掠过一丝几不可察的惊愕,随即化作更深的柔弱。“阿确…皎皎姐…”她声音细细的,
带着病中的沙哑,“你们怎么都来了…太麻烦你们了…”沈确几步上前,
心疼地握住她放在被子外的手。“说什么傻话。药费解决了,皎皎帮了大忙。”他看向我,
眼神复杂,“你看,皎皎多关心你。”鹿夭的目光落在我脸上,带着点怯生生的试探。
“谢谢皎皎姐…我…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她说着,眼圈一红,
别过脸轻轻咳嗽起来,瘦削的肩膀微微耸动,脆弱得仿佛一碰即碎。我扯了扯嘴角,没说话。
关心?是挺关心的。关心她什么时候演不下去。沈确忙着给她倒水,拍背。我走到窗边,
假装看楼下的车流。床头柜上,散乱地放着几本病历和检查报告。鹿夭的主治医生姓王,
是个头发花白、看起来很权威的老专家。据说,就是他一直坚持鹿夭情况特殊,
必须用进口药。“王医生今天查过房了吗?”我状似随意地问。沈确把水杯递到鹿夭唇边,
头也不抬:“查过了,刚走。说…情况还是不太乐观,药不能停。”鹿夭小口抿着水,
垂着眼,长长的睫毛在苍白的脸上投下阴影,像两片孱弱的蝶翼。她没看我,
只是更紧地抓住了沈确的衣袖。我点点头,没再问。目光扫过那些病历本,
最上面一张是血液检查单。日期是昨天。沈确公司有个紧急会议,他不得不走。
临走前千叮万嘱,让我多陪陪鹿夭。门一关上,
病房里那股紧绷的、刻意营造的悲情氛围似乎松动了些。鹿夭靠在枕头上,闭着眼,
长长的睫毛安静地覆着下眼睑,呼吸均匀。阳光透过百叶窗,在她脸上投下明暗交替的光影。
她看起来像个易碎的瓷娃娃。我起身,走到洗手间。关上门,拿出手机。屏幕上,
一个备注为“小七”的联系人发来一条信息:「姐,查到了。
鹿夭上个月10号、15号、20号,在‘悦己’美容院有消费记录。
项目:光子嫩肤、全身SPA。会员卡号:YD777。她常找的**叫Lily。」
上个月10号?我打开手机里一个不起眼的APP——一款记录女性生理周期的软件。
我习惯用它来管理自己的时间,同时,
我也“不小心”在沈确手机同步登录过我的账号(借口是怕自己忘记),而沈确的手机,
鹿夭能“偶尔”接触到。果然,鹿夭“病危”最厉害,沈确衣不解带守在床边的那几天,
APP上清晰地显示着“经期第2-3天”。
一个连床都下不了、需要昂贵药物维持生命的“危重病人”,
会有精力在经期跑去美容院做SPA?冰冷的瓷砖墙面贴着后背,带来一丝清醒。
愤怒像细小的冰针,密密麻麻扎进心脏。沈确的钱,我们的未来,我妈急需的治疗费,
都填进了这个无底洞,而洞的那头,是鹿夭躺在美容院的**床上享受!我深吸一口气,
压下翻涌的戾气。美容院记录只是侧面佐证,还不够。王医生是关键。
病历本上的签名、那些危言耸听的诊断……他是被蒙蔽,还是同伙?我点开另一个聊天窗口,
联系人显示“陈律师”。「陈律,我记得您有个大学同学,是市一医检验科的副主任?」
信息发出去,几乎是秒回。「对,老赵。怎么了文**?」「想麻烦您牵个线,
我有点‘医学问题’想私下请教赵主任,关于血液报告真伪鉴定方面的。有偿咨询,
费用按他平时出庭的标准加倍。」「明白。等我消息。」退出聊天框,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脸色平静,眼底却像结了冰。鹿夭,你喜欢演戏?我陪你演。舞台搭好了,灯光打足了,
就看你这“白月光”,怎么在聚光灯下碎成一地玻璃渣。回到病房,鹿夭已经“醒”了。
她歪着头看我,眼神无辜又带着点探究:“皎皎姐…你没事吧?脸色不太好。”“没事。
”我在刚才的椅子上坐下,拿起一个苹果,“有点累。给你削个苹果?”她连忙摆手,
柔弱地咳了两声:“不用了皎皎姐…我…我没什么胃口。”她顿了顿,目光盈盈地看向我,
“阿确他…最近压力很大吧?都是我拖累了他…还有你…害你们为我花钱…”“钱不重要。
”我低头,水果刀划过苹果皮,发出细微的沙沙声,红色的果皮连成长长的一条,垂落下来。
“重要的是人没事。对吧?”鹿夭的眼神闪烁了一下,避开了我的直视。
“嗯…谢谢皎皎姐…”她把被子往上拉了拉,盖住半张脸,只露出一双水汪汪的眼睛,
“我…我有点困了。”“睡吧。”我把削好的苹果放在床头柜上,果肉洁白。起身,
走到门边,“我出去透透气。”关上病房门,隔绝了里面那个精心布置的舞台。走廊尽头,
陈律师的消息跳出来:「搞定。老赵下午三点有空,他办公室在检验科三楼最东边309。
提我名字。」「收到。谢了陈律。」下午两点五十,我出现在市一医检验科309门外。
敲门进去,一个穿着白大褂、身材微胖、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抬起头,镜片后的眼神锐利。
“赵主任您好,我是文皎皎。陈律师介绍的。”“文**?坐。”赵主任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没什么寒暄,“老陈说你有些‘特殊’的血液报告想看看?”“是。”我从包里拿出手机,
点开相册。里面是我上午在鹿夭病房,“顺手”拍下的几张关键检查报告的照片,
包括昨天那张血液检查单。“您帮我看看这几份报告,特别是这张昨天的血常规和生化组合,
有没有问题。”赵主任接过手机,放大图片,仔细看着。手指在屏幕上滑动,眉头渐渐皱起。
他看了足足五分钟,然后拿起自己桌上的内线电话。“小李?你进来一下。
”一个年轻的女检验员很快进来。赵主任把手机递给她:“你看看这张报告单的打印格式,
还有这个参考值范围后缀的星号标记,是我们科最近半年的标准格式吗?
”小李凑近看了几秒,很肯定地摇头:“主任,这肯定不是我们科的。您看,
我们科的报告单,右下角有激光防伪编码,这张没有。还有,参考值后面的星号备注,
我们科从去年十一月开始就换成斜体了,这张是正体。
而且…”她指着报告单顶部的医院logo,“这个logo的蓝色,
比我们系统默认的深了两个色号。”赵主任点点头,示意小李出去。他看向我,
表情严肃:“文**,这张报告单,是伪造的。格式、细节都对不上我们科现行的标准。
造假的人…用了心思,但不够专业,或者拿到的可能是我们半年多前的旧模板。”伪造!
悬着的石头重重砸进冰湖,溅起的是彻骨的寒意,而非水花。果然。“那…这些诊断呢?
凤舞的签名和那些“疑似罕见免疫系统疾病”、“建议使用进口特效药XX素”的诊断说明。
赵主任推了推眼镜,眼神带着一种见惯不怪的冷峭:“单看字迹和签名章,
很难直接说是假的。王医生是我们院的老资格,签名很多医生都模仿不来。
但是…”他话锋一转,“医学诊断,尤其是涉及昂贵自费药,必须有充分的检查依据支撑。
如果关键的血液报告本身就是伪造的,那么这些诊断的合理性,就非常值得怀疑了。
你可以要求查看原始检验数据和图像,这是患者的权利。”他看着我,意有所指:“当然,
如果院方或者主治医生以各种理由推脱,
或者提供的原始数据看起来也有问题…那这里面的水,就深了。”走出检验科,
医院长廊的灯光白得刺眼。伪造报告。王医生可能知情,甚至参与。
一条清晰的、吸血的链条浮出水面。鹿夭装病,王医生开假报告和昂贵的药,
沈确和我(主要是沈确的钱)当冤大头。愤怒被一种更冷静、更尖锐的东西取代。收集证据,
一击致命。接下来的两天,我成了医院的常客。沈确忙着公司的事,
加上鹿夭“体贴”地表示有我这个“好姐妹”陪着,他来得少了些。这正好给了**作空间。
鹿夭的演技炉火纯青。在我面前,她虚弱得连喝粥都要喘气,
对沈确更是把“不想拖累你”的苦情戏码演到极致。她不知道,
她每一次“无意”中抱怨王医生开的药让她恶心难受,
每一次“心疼”沈确花钱时眼底掠过的精光,都像清晰的脚印,被我默默记录。
我“无意”间在王医生查房时,提起想看看鹿夭之前的CT影像。“毕竟这么多钱花了,
我们家属也想多了解了解病情。”我语气诚恳,带着点无助。王医生的笑容僵了一下,
随即板起脸:“这位家属,影像资料涉及患者隐私,而且专业性很强,你们看不懂,
容易引起不必要的恐慌。治疗方案是我们专家团队定的,要相信医生!”他语气严厉,
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感,目光锐利地扫过我,带着警告。“哦,
这样啊…”我适时地表现出怯懦和不安,低下头,“我就是…有点担心。”“担心是正常的,
但交给专业的人。”王医生语气缓和了一点,转向鹿夭时又换上了和蔼,“小鹿啊,放宽心,
按时吃药,会好起来的。”鹿夭配合地露出感激又脆弱的微笑。王医生走后,
我坐在鹿夭床边削水果,刀锋在果肉上留下整齐的切面。不经意的闲聊开始了。“夭夭,
王医生看着好严肃啊,你怕不怕他?
”鹿夭正拿着小镜子看自己苍白的脸(她床头永远放着一面小圆镜),闻言手指一顿,
扯出一个虚弱的笑:“王伯伯…人其实挺好的,就是…就是要求严格了点。他说我这病,
就得下猛药…”“猛药?”我皱眉,“我看那些药名都好复杂,进口的吧?是不是特别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