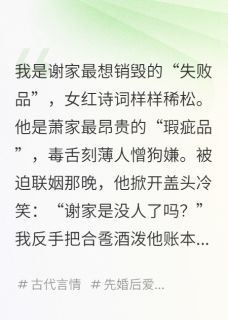
我是谢家最想销毁的“失败品”,女红诗词样样稀松。他是萧家最昂贵的“瑕疵品”,
毒舌刻薄人憎狗嫌。被迫联姻那晚,他掀开盖头冷笑:“谢家是没人了吗?
”我反手把合卺酒泼他账本上:“萧家派你来清库存?”1我是谢昭昭。谢家那个……嗯,
怎么说呢,用我娘恨铁不成钢的原话就是:“生块叉烧都好过生你!”女红?
上次给我爹缝个荷包,针脚歪得能爬出条蜈蚣,我爹戴着上朝,
同僚夸他“谢大人品味越发返璞归真了”,差点没把他老人家气背过去。诗词?
对着满园春色,憋了半天就一句“花好多啊开得真红”,夫子当场拂袖而去,
说教不了我这种“返璞归真”的奇才。总之,在人才济济、清贵满门的谢家,
我就是那块最想被销毁的“失败品”,摆哪儿都扎眼,还占地方。他是萧景澄。
萧家那位……呵,用京城贵女圈私下流传的话讲:“生得一副神仙样貌,
偏生一张淬了毒的嘴,可惜了那身好皮囊。”刻薄?那是他的看家本事。毒舌?
那是他的日常消遣。据说有贵女鼓起勇气赠他香囊,他瞥一眼,慢悠悠道:“姑娘这针线,
是打算勒死哪路仇家?配色也够独特,红配绿,赛狗屁?”姑娘当场哭晕。所以,
他萧小侯爷,就是萧家最昂贵也最让人牙痒痒的“瑕疵品”,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人憎狗嫌,偏偏家世显赫,无人敢当面招惹。然后谢家和萧家,
这两家朝堂上掐了几十年、私下里互相使绊子、连祖坟都恨不得隔条银河的老冤家,
突然被一道从天而降的赐婚圣旨给砸懵了。圣旨大意是:为了江山社稷,为了朝堂和谐,
你们两家,必须结个亲!谢家看看自家不成器的我,再看看对面那位活阎王,愁云惨淡,
觉得这婚结完,谢家的门楣怕是要矮上三尺。萧家瞅瞅自家那位嘴毒祖宗,
再看看我“声名远播”的“返璞归真”,也是唉声叹气,琢磨着这聘礼是不是该折算成现银,
好留着以后给儿子“续弦”用。于是乎,我这个“失败品”,和他那个“瑕疵品”,
就被硬生生捆一块儿,塞进了大红的花轿和骏马,
成了本朝开国以来最离谱、也最不被看好的联姻夫妻。2新婚夜。红烛高烧,
映得满室都是刺眼的红。头上的赤金累丝凤冠重得要命,脖子快断了。
身上层层叠叠的嫁衣裹得我像个待蒸的华丽包子。
我像个木头桩子似的杵在铺着大红鸳鸯锦被的拔步床边,耳朵竖得老高,
听着外面喧闹的喜宴声渐渐散了。脚步声由远及近,停在门口。吱呀——门开了。
一股淡淡的酒气混合着他身上那种清冽又疏离的味道涌了进来。盖头还蒙着,
我只能看见一双穿着簇新云纹黑缎靴的脚,一步一步,不疾不徐地朝我走过来。那脚步,
沉稳得很,听不出半点新郎官的喜气,倒像是来……验收什么残次品的。我的心,
也跟着那脚步声,一点一点往下沉。完了完了,谢昭昭,你的好日子到头了。想想他那张嘴,
想想那些被他气哭的贵女们……我捏紧了藏在宽大袖口里的拳头,手心全是冷汗。
脚步声停在我面前。很近。近得我能感觉到他身高的压迫感。他好像就那么站定,没动,
也没说话。时间像是凝固了,只有红烛燃烧时偶尔发出的轻微噼啪声。我屏住呼吸。然后,
眼前骤然一亮!遮天蔽日的红被猛地掀开。新鲜的空气涌进来,
带着他身上更清晰的酒气和一种冷冽的松木气息。我下意识地抬眼。撞进了一双眼睛里。
那眼睛生得极好,眼尾微微上挑,本该是多情的桃花眼型,可此刻里面淬着的,
全是冰冷的、毫不掩饰的审视和……嫌弃?
像在看一件摆在库房角落里、落满灰尘、还磕碰掉漆的旧瓷器。
他穿着一身同样刺目的大红喜服,衬得他面如冠玉,身姿挺拔如修竹。可惜,
那薄唇抿成一条冷淡的直线,破坏了一切美感。目光在我脸上逡巡了足足有三息。那眼神,
凉飕飕的,刮得我脸皮生疼。接着,一声极轻、极冷的嗤笑从他鼻腔里溢出来。「呵。」
他开口了,声音是意料之中的清越,却裹着冰碴子。「谢家……」他顿了顿,尾音拖长,
慢悠悠的,充满了刻意的疑惑和毫不留情的嘲讽,「是没人了吗?」那语气,
仿佛在说:就这?也配塞给我?轰的一下!一股热气猛地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什么紧张,
什么害怕,全被这盆冰水浇得渣都不剩!只剩下熊熊燃烧的怒火,烧得我脑子嗡嗡响!
好啊你个萧景澄!真当姑奶奶是泥捏的?我“返璞归真”怎么了?碍着你吃饭睡觉呼吸了?
我噌地一下从床边站起来——动作太猛,头上的珠钗一阵乱晃叮当作响。
我也不管什么大家闺秀仪态了,反正我在他眼里早就是个“没人了”的失败品。眼风一扫,
旁边喜桌上正好摆着合卺酒,两只小小的金杯,盛着琥珀色的液体。我两步跨过去,
抄起离我最近的那一杯。手腕一转!哗啦——清亮的酒液,
在空中划出一道完美的、带着我怒气的弧线,
精准无比地泼向了他……身后书案上摊开的一本厚厚的、墨迹簇新的账册!酒香四溢。
深色的酒渍迅速在账册雪白的纸页上晕染开来,墨迹瞬间模糊成了一团糟。整个新房,
死一般寂静。只有酒液滴落在书案上,发出轻微的“啪嗒”声。
萧景澄大概完全没料到我这手“釜底抽薪”,他脸上的冰冷和嘲讽瞬间凝固了,
那双漂亮的桃花眼罕见地睁大了一瞬,难以置信地看向我,
又低头看向他那本瞬间“阵亡”的宝贝账册。我用力把空酒杯往桌上一顿,
发出“咚”的一声脆响。抬着下巴,学着他刚才那种慢悠悠、气死人不偿命的腔调,
回敬道:「萧家……派你来清库存?」3我故意把“清库存”三个字咬得特别重,
目光意有所指地在他那张此刻精彩纷呈的俊脸上溜了一圈,又落回那本湿淋淋的账册。
「看来库存积压严重啊,」我扯出一个皮笑肉不笑的表情,
「连账本都这么迫不及待地要‘喝’合卺酒了?」空气仿佛被冻住了。
红烛的光在他脸上跳跃,明暗不定。他那双刚才还淬着冰的眼睛,
此刻像是被投入了滚烫的油锅,翻涌起压抑的、深不见底的怒火,死死地锁在我脸上。
我感觉自己像是被猛兽盯上的猎物,后背的汗毛都竖起来了。但输人不输阵!我梗着脖子,
毫不示弱地瞪回去。心里的小人却在疯狂呐喊:谢昭昭!你完了!你彻底把活阎王得罪死了!
你以后的日子怕是要在油锅里过了!他盯着我,牙关似乎咬紧了一瞬,腮边的线条绷得冷硬。
就在我以为他要暴起掐死我,或者至少用他那张毒嘴把我喷得体无完肤时,他却猛地一甩袖!
宽大的喜服袖子带起一阵冷风。「好,很好。」他声音低沉,
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一种风雨欲来的危险气息。
他甚至没再看那本惨遭“酒浴”的账册一眼,仿佛那东西已经不值得他分神。「谢昭昭,」
他念我的名字,带着一种奇异的、令人心头发毛的玩味,「我记住你了。」说完,他转身,
大步流星地朝门口走去,动作干脆利落,没有一丝一毫的留恋。“砰!
”新房的门被他用力甩上,发出震天响,连带着门框都似乎抖了三抖。震得我耳朵嗡嗡响,
也震得我心头一跳。偌大的新房,瞬间只剩下我一个人。还有满桌狼藉的杯盏,
以及那本在烛光下散发着浓郁酒气、墨迹糊成一团的账册。刚才那股子豁出去的泼辣劲儿,
随着他摔门而去,像被戳破的气球,一下子泄光了。腿一软,我跌坐回冰冷的床沿。
看着那扇紧闭的、仿佛隔绝了两个世界的门,再看看那本湿漉漉的账册……完了。谢昭昭,
你好像……闯大祸了。4新婚夜闹掰的后果,就是泾渭分明。偌大的侯府,
他住他的“澄心斋”,据说堆满了账册和算筹,活像个巨大的金库。我占我的“栖霞苑”,
位置有点偏,胜在安静,还有个小小的、阳光不错的院子。挺好,互不干涉,清净。
除了每日清晨雷打不动地去给那位据说常年礼佛、不问世事的太婆婆请安,
我和萧景澄基本处于“王不见王”的状态。偶尔在府中狭路相逢,
那场面……通常是这样的:回廊下。他一身墨色锦袍,身姿挺拔,手里可能还捏着几页纸,
步履匆匆,一副日理万机的铜臭商人模样。我可能正指挥着小丫鬟给我新得的一盆墨菊浇水,
或者蹲在墙角研究一株刚冒头的野草。远远看见他。空气瞬间凝固三秒。
然后——他目不斜视,眼神直接从我头顶飘过去,仿佛我只是一团无色无味的空气,
或者廊下一根碍眼的柱子。脚步不停,衣袂带风,刮起一阵冷飕飕的空气。而我?
我立刻挺直腰板,下巴抬得能戳破天,同样把视线投向遥远的天际,
或者专注地盯着廊檐下某个虚无的点,嘴里还要装作不经意地哼起荒腔走板的小调,
以示我心情愉悦,完全不受影响。「哼~今天天气好晴朗~处处好风光~」
等到他那道散发着“生人勿近”气息的背影彻底消失在回廊尽头。我立刻垮下肩膀,
长长吁一口气。「**,」我的陪嫁丫鬟春桃,小心翼翼地问,「您……还好吧?」
「好得很!」我拍拍手,声音拔高,故意朝着他消失的方向,「空气都清新了八百倍!」
我知道府里下人都在背后怎么嚼舌根。「侯爷和夫人?啧,一个赛一个的冷脸,
比咱们府门口那对石狮子还硬。」「新婚夜就闹掰了?啧啧,可怜了那么好的姻缘……」
「嘘!小声点!侯爷书房那本被夫人泼坏的账册,听说价值千金呢!
侯爷气得当晚就睡书房了,到现在都没搬回去!」听到“价值千金”时,
我正捏着一块刚出锅、香喷喷的栗子糕往嘴里送,手一抖,糕差点掉地上。千金?!
我泼掉了一本价值千金的账册?!心口一阵绞痛。谢昭昭啊谢昭昭,你泼的不是酒,
是泼出去的金山银山啊!败家!肉痛归肉痛,日子还得过。
在谢家我就不是个安分守己的主儿,到了这冷冰冰的侯府,
更不可能真的像大家闺秀一样绣花弹琴了。总得找点营生,
证明我这个“失败品”也有发光发热的地方吧?思来想去,
我瞄上了我最熟悉的东西——胭脂水粉。别误会,我对描眉画眼兴趣不大。
但我有个秘密武器:我娘留给我的一箱子旧书里,
夹着几张泛黄的、据说是前朝宫廷流出来的胭脂方子!用料稀奇古怪,
什么珍珠粉、玉屑、花露……听着就贵,但效果据说神乎其神。在谢家我没钱折腾,
现在嘛……顶着个侯府夫人的名头,月例银子总有几个吧?5说干就干!
我在自己偏僻的栖霞苑里腾出一间厢房当“工坊”,让春桃偷偷去外面采买原料。
珍珠粉太贵?买不起好的,那就用最细的贝壳粉代替!玉屑?开什么玩笑!
用点磨得极细的石英粉凑合!花露?自己采!我院子里那几丛开得正盛的月季和茉莉,
香气正浓!关起门来,我挽起袖子,对照着那古里古怪的方子,开始了我的“捣鼓”大业。
磨粉,蒸花露,调配,搅拌……弄得自己灰头土脸,手指头都染上了洗不掉的颜色。
失败了一次又一次,要么颜色诡异像中毒,要么气味呛人像馊饭,要么干得掉渣,
要么稀得像水。春桃看着一桌子五颜六色、形态各异的“失败品”,愁眉苦脸:「**,
要不……算了吧?您这手……」她看着我沾满各色粉末的手,欲言又止。「不行!」
我抹了把额头的汗,蹭上一道红痕,「我就不信了!那些贵女脸上抹的金贵东西,
还能比我娘这方子更厉害?」终于,在不知道浪费了多少贝壳粉和花瓣后,
我成功鼓捣出了三小罐勉强能看的东西。一罐是浅粉色的口脂,带着清甜的茉莉香。
一罐是细腻的珍珠白香粉,透着点月季的淡雅。还有一罐是淡红的胭脂膏,色泽自然。
我给自己薄薄试了一层。铜镜里,气色好像……真的好了那么一丢丢?皮肤看起来也细腻了?
「春桃!快看!」我兴奋地拉着她。春桃凑近仔细看了看,眼睛亮起来:「**!真的!
您这脸色,瞧着比前几日精神多了!这粉……好像也不浮!」成了!
巨大的成就感冲昏了我的头脑。下一步,就是怎么把这些“宝贝”换成钱!
在侯府里开铺子是不可能的,萧景澄知道了怕是会直接把我连人带罐子扔出去。
我瞄准了西市。那里铺面杂,人流多,三教九流都有,最适合我这种本钱少的“小买卖”。
用我攒下的月例,加上偷偷卖掉两件不大起眼的陪嫁首饰,我在西市最不起眼的角落里,
盘下了一个小小的、门脸窄得只能容一人通过的铺面。挂了个歪歪扭扭的招牌——「昭昭阁」
。开张第一天,门可罗雀。第二天,依旧冷清。第三天,我蹲在门口剥瓜子,
看着对面卖炊饼的大爷生意都比我的好。正当我怀疑人生时。
一个穿着粗布衣裳、脸上带着愁苦之色的年轻妇人,犹豫着走进来。
她脸颊上有几块明显的红疹,看起来有些日子了。「姑娘……哦不,夫人,」她怯生生地问,
「您这儿……可有能遮遮这红印子的东西?我、我明日要去大户人家帮工,怕主家嫌恶……」
我看着她脸上的红疹,又看看我罐子里那浅粉的香粉。这粉遮瑕力恐怕不够。灵光一闪!
我想起方子里提到过一种用特定药草汁液调和粉料的方法,据说能安抚肌肤。死马当活马医!
我让她稍等,跑回后面我的“工坊”,翻出之前试验失败留下的一些有镇定效果的草药粉,
本来是打算做药膏的,小心翼翼地掺了一点进那罐珍珠白贝壳粉里,
又滴了几滴新蒸的、温和的茉莉花露,快速搅匀。「试试这个!」我把新调好的粉递给她,
又给了她一点那淡红的胭脂膏,「薄薄一层粉盖一下,再用这个胭脂轻轻拍在没疹子的地方,
提提气色。」妇人半信半疑地试了。片刻后,她看着铜镜里的自己,眼睛一点点亮起来,
激动得声音都抖了:「遮、遮住了!真的淡了好多!夫人,您真是神仙手啊!」
她千恩万谢地买走了那罐特调粉和一点点胭脂膏。虽然只赚了十几个铜板,
但这“开门红”让我信心大增!6几天后,那妇人又来了,
还带来了两个同样脸上有点小瑕疵的同伴!她脸上的红疹居然也消褪了不少!
「夫人您那粉神了!用了两天,不光遮得好,脸也不那么痒了!」她喜滋滋地说。口碑,
就这么一点点从最底层传开了。我的“昭昭阁”开始有了回头客。
虽然都是些普通百姓、小门小户的姑娘媳妇,买的量也小,
但那种靠自己的双手赚到钱的感觉,简直比吃了蜜还甜!我每天忙得脚不沾地,研究新方子,
改良旧配方,去药铺淘换便宜又好用的材料,
跟顾客聊天了解她们的需求……脸上总是沾着各种粉末,衣裙也不再是绫罗绸缎,
而是方便干活的棉布衣裳。栖霞苑里,我的“工坊”规模也悄悄扩大了一点,
弥漫着各种花草药材混合的、奇奇怪怪却又生机勃勃的香气。连春桃都夸我:「**,
您捣鼓这些东西的时候,眼睛亮得跟星星似的!比在府里发呆强多了!」我当然得意。
直到某天,我去库房想找几个干净瓷罐装新做好的胭脂膏。侯府的库房大得吓人,分门别类,
井井有条。管库的是个姓钱的老管事,据说跟着萧家几十年了,精瘦干练,
看我的眼神带着点不易察觉的疏离。我说明来意。钱管事那张刻板的脸上没什么表情,
公事公办道:「回夫人,库房瓷罐倒是有,但都是登记造册的物件,
取用需得侯爷的手批条子。」批条子?找萧景澄?
我脑子里立刻浮现出他那张冷冰冰的、写着“生人勿近”的脸,
还有那句刻薄的“谢家没人了吗”。让我去求他?门都没有!「没有多余的?
或者……次一等的也行?」我不死心。钱管事眼皮都没抬:「库中无次品。夫人若急用,
可去外面采买。」得,又被堵回来了。我悻悻地转身准备离开。刚走出几步,
眼角余光瞥见库房深处一个半开的侧门,里面似乎堆放着一些……废弃的旧物?我脚步一顿,
装作不经意地溜达过去。果然!里面堆着不少破损的家具、褪色的帐幔,角落里,
竟真的摞着几个落满灰尘的大竹筐!
筐里全是各种大大小小的瓷器——豁口的碗、裂了缝的碟子、缺了盖的茶壶,
甚至还有几个颜色不匀、造型歪斜的……瓷罐!虽然品相不佳,但洗洗刷刷,
装我的胭脂膏完全没问题啊!还不要钱!我心头一喜,指着那筐:「钱管事,
那些……不能用了吧?」钱管事跟了过来,看了一眼,
眉头几不可察地皱了一下:「那些是历年淘汰下来的残次品,正准备清理出去。」
「清理出去多可惜!」我立刻接口,脸上堆起自认为最和善无害的笑容,「钱管事,您看,
我那小铺子正好缺些罐子装货,这些残次品给我废物利用,岂不是正好?
也省得府里费功夫清理了不是?」我努力让自己的眼神显得特别真诚,特别“勤俭持家”,
特别为侯府“开源节流”着想。钱管事沉默地看了我几秒,又看了看那筐破烂,
眼神在我“真诚”的笑脸和破烂之间来回扫视,似乎在评估我这侯府夫人捡破烂的行为,
到底是真穷疯了,还是脑子有问题。最终,
他大概是觉得为了这点破烂得罪名义上的主母不划算,也可能单纯觉得我脑子确实不太正常,
无奈地、极其轻微地点了下头。「夫人若是不嫌弃,自取便是。只是……」他顿了顿,
语气平板地提醒,「莫要说是从侯府库房拿的残次品。」「明白明白!」我如获至宝,
连连点头,「绝对不给侯府丢脸!就说是我从旧货市场淘换的宝贝!」
钱管事的嘴角似乎抽搐了一下。我欢天喜地,招呼春桃和另一个小丫鬟,
把那筐“宝贝”搬回了我的栖霞苑。清洗,消毒,晾干。
看着一排排虽然歪瓜裂枣、但洗刷干净后勉强能用的“新”罐子,我心里美滋滋的。
萧景澄库房里的“垃圾”,到了我手里,就是能生钱的宝贝!哼,看不起谁呢!
7我的“昭昭阁”生意渐渐有了起色,虽然赚的都是辛苦钱,但看着小钱匣子一点点满起来,
心里别提多踏实了。这天,
我刚指挥人把新做好的几罐茉莉香粉和海棠胭脂摆上我那窄小的货架,
铺子门口就传来一阵喧哗。几个穿着体面、一看就是大户人家管事妈妈模样的妇人,
簇拥着一个穿着鹅黄锦缎衣裙、妆容精致的年轻女子走了进来。那女子生得明艳,
只是眉眼间带着一股子骄纵之气。她手里捏着一方丝帕,姿态优雅地掩着鼻子,
挑剔地打量着我这简陋的小铺面,眼神里满是嫌弃。「就这儿?」她声音不大,
却足够让铺子里的人都听见,「能有什么好东西?一股子廉价的花粉味儿。」
她身后的一个管事妈妈立刻接话:「**,您身份尊贵,何必来这种地方?
‘玉颜斋’新到的南洋珍珠粉才配得上您呢!」「玉颜斋」?京城最大的脂粉铺子?
我心里咯噔一下。那黄衣女子没理会妈妈的话,目光扫过我的货架,
最后落在我那罐最贵的、用了上等贝壳粉和真正微量珍珠粉调和的“凝脂玉容粉”上。
她伸出涂着蔻丹的手指,虚虚一点:「那个,拿来看看。」春桃赶紧取下来,小心地递过去。
女子打开盖子,用指甲尖挑起一点点粉,凑到鼻尖闻了闻,又捻了捻。「粉质倒还算细,」
她挑剔地评价,「就是这珍珠粉的分量,啧啧,怕是掺了九成的贝壳粉吧?一股子腥气。」
我的心提了起来。她倒是识货!「还有这香味,」她放下粉盒,
又拿起旁边一盒胭脂膏闻了闻,「太俗,一股子市井气。」
她身后的妈妈们立刻附和:「就是就是,哪比得上‘玉颜斋’的贡品香。」
「一看就是小门小户弄出来糊弄人的玩意儿。」铺子里原本的几个顾客,被这阵仗吓住了,
悄悄放下手里的东西溜了出去。黄衣女子把胭脂膏往柜台上一丢,发出“啪”的一声轻响,
斜睨着我:「你就是这铺子的东家?一个妇道人家,抛头露面做这等营生,
也不怕丢了夫家的脸面?」她语气里的轻蔑和挑衅毫不掩饰。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掐进掌心。
这分明是来找茬的!什么“玉颜斋”的**,怕是同行派来砸场子的!我深吸一口气,
压下火气,脸上努力挤出一点职业假笑:「这位姑娘,东西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小店本小利薄,自然比不得‘玉颜斋’财大气粗用真金白银堆。但用料实在,价格公道,
自有一份心意在。您若看不上,不买便是,何必出口伤人,搅扰其他客人?」「哟,」
那黄衣女子挑眉,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还教训起我来了?你算什么东西?
一个靠捡破烂开铺子的……」
她意有所指地扫了一眼我铺子里那些洗刷干净、但依旧看得出瑕疵的罐子,
「也配跟我谈‘心意’?」捡破烂?!她怎么知道我用的是库房淘汰的罐子?!
一股寒意瞬间从脚底窜起!钱管事答应过不说出去的!难道……我猛地看向她,
她眼中闪过一丝得意和恶毒。8「听说你这些罐子,还是从侯府库房里捡来的残次品?」
她声音陡然拔高,故意让外面看热闹的人都听见,「萧家是穷得揭不开锅了,
还是你这新夫人实在上不得台面,连装胭脂的罐子都要捡破烂用?真是笑死人了!」
轰——铺子外围观的人群瞬间炸开了锅!「什么?捡侯府的破烂?」「天哪!
侯府夫人这么……这么落魄的吗?」「难怪开在这种地方,用这种罐子……」「啧啧啧,
萧小侯爷的脸怕是要丢尽了……」各种鄙夷、好奇、幸灾乐祸的目光像针一样扎在我身上。
春桃气得脸都白了,想冲上去理论,被我死死拉住。黄衣女子看着我的窘迫,
得意地扬着下巴,像只斗胜的孔雀。「我劝你啊,」她慢悠悠地,
用丝帕拂了拂根本不存在的灰尘,「趁早关了这丢人现眼的铺子,老老实实回侯府后院待着,
省得连累萧家被人戳脊梁骨!」铺子里死寂一片。外面议论纷纷的声音像苍蝇一样嗡嗡作响。
我看着她那张写满恶意的脸,只觉得一股冰冷的怒火从心底烧起来,烧得我浑身发抖,
却又异常清醒。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同行竞争了。这是要把我谢昭昭,连同萧景澄的脸面,
一起摁在地上踩!我盯着她,一字一句,清晰地问:「姑娘一口一个‘玉颜斋’,
又对我的罐子来源如此清楚。不知姑娘贵姓?与‘玉颜斋’的东家,是何关系?」
黄衣女子似乎没料到我这时候还敢反问,愣了一下,随即哼道:「我姓柳!
‘玉颜斋’是我舅舅家的产业!怎么?你还想攀扯不成?」柳?京城做脂粉生意的柳家?
我脑子里飞快地闪过之前打听过的信息。柳家,似乎和萧家在城外的几处田庄有些纠纷?
电光火石间,一个念头闪过!这恐怕不只是“玉颜斋”打压同行那么简单!
这是冲着萧景澄来的!是有人想借我这块“短板”,来打萧家的脸!「原来如此。」
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声音反而平静了,「柳姑娘是替‘玉颜斋’,
还是替柳家……来我这小铺子‘指点江山’的?」我刻意加重了“柳家”两个字。
柳**脸色微变,显然没想到我会直接点破:「你胡说什么!
我是看不惯你用破烂罐子装东西骗人!」「破烂?」我忽然笑了,
拿起柜台上一个洗得干干净净、虽然有点歪但釉色温润的旧罐子,手指摩挲着上面的冰裂纹,
「柳姑娘见识广博,可知这罐子,是什么来头?」她被我问得一怔,
狐疑地看着那罐子:「不就是个破罐子?」「这罐子,」我声音清亮,
确保外面的人也能听清,「釉色是前朝官窑特有的‘雨过天青’,虽因窑火不稳略有瑕疵,
瓶身微瑕,但这冰裂纹,是天然窑变,非人力可为,古拙质朴,别有意趣。
放在懂行的人眼里,未必不是一件有年头的雅物。」我顿了顿,
目光扫过她和她身后那些面露不屑的妈妈们。「我谢昭昭开这铺子,本钱微薄,
用不起金玉器皿。但‘废物利用’,化腐朽为神奇,靠自己的双手赚取干净的钱,一不偷,
二不抢,三不坑蒙拐骗。给街坊邻里的姑娘媳妇们,提供些物美价廉、实实在在能用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