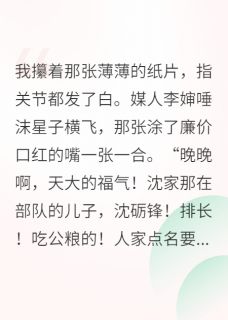
我攥着那张薄薄的纸片,指关节都发了白。媒人李婶唾沫星子横飞,
那张涂了廉价口红的嘴一张一合。“晚晚啊,天大的福气!沈家那在部队的儿子,沈砺锋!
排长!吃公粮的!人家点名要你!”我娘搓着围裙角,脸上又是喜又是愁。“李婶,
这…这太突然了,晚晚才十八,那沈排长听说都二十六七了?还一直在部队,
俩人面都没见过…”“哎哟我的老姐姐!”李婶一拍大腿,声音拔高八度,
“面都没见就相中你家晚晚,还不是图她模样好、性子软和?人家沈家什么条件?
沈排长那津贴,月月往家寄!嫁过去就是享福!穿的确良,吃白面馍!”她凑近我娘,
压低声音,却足够让我听清。“沈家老太太可说了,晚晚这身段,一看就好生养!
人家就图这个!过了这村没这店!”我站在灶屋门口,手里还拿着喂鸡的瓢。心跳得厉害,
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沈砺锋?那个名字,只在村里人偶尔的闲谈里听过。
遥远得像天边的云。现在,这朵云要砸到我头上了?“晚晚,你…”我娘看向我,
眼神复杂。我没吭声。转身把瓢里的谷子撒出去,鸡群扑腾着围上来。手心全是汗。我知道,
我没得选。家里五个孩子,我是老大。爹的腿去年修水渠砸伤了,干不了重活。
底下四个弟妹,张着嘴等饭吃。沈家给的彩礼,够家里缓好几年。李婶说得对,是福气。
三天后,我就成了沈砺锋法律上的妻子。结婚证是大队干部送到我家的。一张硬纸,
上面印着我和一个陌生男人的名字。照片栏空着。他人呢?李婶打着哈哈:“砺锋任务重!
保家卫国嘛!等得了空,肯定回来!沈家老太太说了,让你先过去,把家安顿好!”于是,
我揣着那张没有照片的结婚证,拎着一个小包袱,进了沈家的门。沈家在村东头,
三间青砖瓦房,气派。可我踏进门槛的第一步,心就凉了半截。堂屋里坐着个老太太。
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在脑后挽了个髻,穿着深蓝色的斜襟褂子,板着脸。眼皮耷拉着,
看人时从下往上撩。那眼神,像刀子刮过。这就是我婆婆,张金花。“来了?
”她嗓子有点哑,干巴巴的。“娘。”我低低叫了一声,把包袱放在脚边。“嗯。
”她鼻腔里哼出一个音,上下打量我,目光最后落在我腰胯上,停了很久。
看得我浑身不自在。“西屋归你。灶屋在后头。先把院子扫了,鸡喂了。
”她端起桌上的粗瓷碗,喝了口水,眼皮都没抬,“我们沈家,不养闲人。”没有欢迎,
没有寒暄。只有指派。我默默拿起靠在墙角的扫帚。院子不小,鸡屎随处可见。扫到一半,
一个穿着花布衫,梳两条油亮辫子的年轻女人扭着腰进来。“哟,这就是我新嫂子吧?
”声音又尖又脆,带着一股说不出的味道。她是我小姑子,沈玉兰。“长得是挺招人疼。
”她围着我转了一圈,眼神挑剔,“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个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
我哥可是排长,金贵着呢!”婆婆在屋里咳嗽一声。沈玉兰撇撇嘴,扭身进了堂屋,
声音不大不小飘出来:“娘,你看她那细胳膊细腿,能生养吗?别是个不下蛋的母鸡,
白费我哥的彩礼钱!”我的脸腾地烧起来。攥着扫帚的手,指甲掐进了掌心。原来,
福气是这样的。晚上,我躺在西屋冰凉的土炕上。身下是硬邦邦的旧褥子。窗户纸破了个洞,
冷风嗖嗖往里灌。我摸出那张结婚证。借着月光,一遍遍描摹那个陌生的名字。沈砺锋。
我的丈夫。你在哪儿?你知不知道,你家里给我准备的是这样的日子?眼泪无声地淌下来,
洇湿了枕头。第二天天不亮,我就被婆婆拍门的声音惊醒。“几点了还睡?
等着日头晒**呢?起来做饭!”我赶紧爬起来。灶屋冷得像冰窖。水缸里结了层薄冰。
我费力地砸开冰,舀水淘米。手冻得通红,几乎没了知觉。
早饭是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玉米糊糊,一碟咸得发苦的萝卜干。婆婆沉着脸,
把碗墩在桌上:“败家!米放这么多!”沈玉兰用筷子搅着糊糊,阴阳怪气:“就是,
当我们家粮食大风刮来的?嫂子,你在娘家也这么吃?”我低着头,
小口喝着没滋没味的糊糊。胃里空得发慌。饭后,婆婆丢给我一个沉甸甸的柳条筐。“去,
后山捡柴火。捡不满别回来。”后山风大。树枝刮在脸上生疼。我背着筐,
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林子里走。筐越来越沉,压得我直不起腰。汗水混着泪水流下来。
这就是我的“福气”?突然,脚下一滑!我整个人顺着一个陡坡滚了下去!天旋地转。
筐飞了出去,柴火散了一地。最后“咚”一声,我的头狠狠撞在一块凸起的石头上。
眼前一黑。彻底失去意识前,我好像听到急促的脚步声朝这边跑来。是谁?醒来时,
头疼得像要裂开。鼻尖萦绕着淡淡的消毒水味和…一丝若有若无的汗味?很干净的那种。
我费力地睁开眼。白色的墙壁,白色的床单。是公社卫生所。床边站着一个人。很高。
穿着笔挺的绿军装,没戴帽子,露出利落的板寸。肩很宽,背脊挺得笔直。他正背对着我,
跟穿白大褂的医生低声说话。“……脑震荡,
需要观察……额头伤口缝了三针……注意别感染……”声音低沉,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度。
我的心猛地一跳。一个模糊又清晰的念头冒出来。是他?医生点点头,又交代了几句,走了。
男人转过身。我的呼吸瞬间屏住。那是一张棱角分明的脸。肤色是长期风吹日晒的小麦色。
眉毛很浓,像两把出鞘的剑。鼻梁高挺,嘴唇抿成一条坚毅的直线。最慑人的是那双眼睛。
深邃,像不见底的寒潭。此刻,那寒潭正看向我。带着审视,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复杂?
四目相对。空气仿佛凝固了。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他先开了口,声音比刚才更沉,
没什么温度。“苏晚晚?”我喉咙发紧,只能点点头。“我是沈砺锋。”简单的五个字。
像一块巨石投进我心里,掀起滔天巨浪。我的丈夫。第一次见面,是在我摔得头破血流之后。
真是……好极了。他走到床边,居高临下地看着我。那目光沉甸甸的,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
“怎么摔的?”他问。我垂下眼,避开他的视线,声音细得像蚊子哼。
“捡柴……不小心滑倒了。”他没再追问。沉默在狭小的病房里蔓延。我攥着被角,
手心全是汗。不知过了多久,他忽然说:“我只有三天假。”我茫然地抬眼看他。什么意思?
“队里紧急任务。”他言简意赅,目光扫过我额头上缠着的纱布,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
“你,跟我回部队驻地。”我彻底懵了。“什……什么?”“你是我妻子。”他语气平淡,
像是在陈述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事实,“留在家里,我不放心。”最后三个字,他说得很轻。
却像一颗小石子,在我死水般的心湖里,投下了一点涟漪。不放心?是对我的伤不放心?
还是……对那个“家”不放心?没等我细想,他又补了一句,带着军人特有的干脆。
“收拾一下,明天一早走。”婆婆和沈玉兰得知我要跟着沈砺锋走,脸色精彩极了。
婆婆拍着大腿嚎:“哎哟我的儿啊!娘好不容易把你盼回来!这媳妇才进门几天,
你就要带走?她走了,这一大家子活儿谁干?谁伺候我老婆子?
”沈玉兰也尖着嗓子帮腔:“就是啊哥!嫂子笨手笨脚的,去部队不是给你添乱吗?再说,
娘身子骨不好,离不得人伺候!”沈砺锋正在帮我收拾那个可怜的小包袱。闻言,
他动作没停,头也没抬。“家里不是有玉兰?”沈玉兰一噎。
婆婆哭嚎得更响:“玉兰还是个姑娘家!哪能什么都干!砺锋啊,你是不是娶了媳妇忘了娘?
这狐狸精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娘。”沈砺锋终于直起身。他个子很高,往那一站,
屋里顿时显得逼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沉甸甸的压迫感。“晚晚是我妻子,她受了伤。
”他目光扫过婆婆和沈玉兰,那眼神锐利得像能穿透人心,“她在这里,我不放心。
”“部队有卫生员,条件好些。这是命令。”“命令”两个字,斩钉截铁。
婆婆的哭嚎戛然而止。沈玉兰也缩了缩脖子,不敢再吱声。她们再泼,
也怕这个穿着军装、一身煞气的儿子/哥哥。我低着头,心里五味杂陈。他是在……护着我?
仅仅是因为我是他名义上的妻子?还是……别的?第二天天蒙蒙亮,
吉普车就停在了沈家门口。引来不少村民围观。沈砺锋拎着我那个小包袱,大步走在前面。
我亦步亦趋地跟着,额头的伤口还隐隐作痛。婆婆扒着门框,眼神怨毒地盯着我。
沈玉兰更是毫不掩饰地翻着白眼。坐进吉普车后座,引擎发动。车子驶离村子,
扬起一片尘土。我看着后视镜里越来越小的沈家瓦房,还有那两个模糊的人影。
心里没有一丝留恋。只有一种逃离牢笼般的轻松。随即,又被巨大的茫然和忐忑淹没。
部队驻地,等待我的会是什么?一路颠簸。沈砺锋坐在副驾驶,腰杆挺得笔直,
几乎没怎么说话。只有司机小战士偶尔和他低声交谈几句,用的都是我听不懂的术语。
我蜷在后座角落,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陌生景色。山越来越高,路越来越险。最后,
车子开进一个戒备森严的大门。哨兵持枪肃立,庄严地敬礼。沈砺锋回礼。我的心,
也跟着提了起来。家属院在山脚下,一排排整齐的红砖平房。沈砺锋的房子在最边上,
小小的两间,带一个巴掌大的院子。屋里陈设极其简单。一张木板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
一个掉了漆的木头衣柜。地上扫得干干净净,水泥地泛着冷硬的光。“你睡里屋。
”沈砺锋把我的小包袱放在靠里的那张床上,“我在外间搭行军床。”“哦…好。
”我小声应着,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放。他看了我一眼,似乎想说什么,
最终只是指了指墙角一个暖水瓶。“先歇着。我去营部一趟。暖瓶里有热水。”说完,
他戴上军帽,转身大步离开。背影消失在门口。屋里只剩下我一个人。静得可怕。
我慢慢走到床边坐下,硬邦邦的床板硌得慌。看着这简陋到极点的“家”,
再想想婆婆的刻薄和小姑子的刁难。这里,至少没有那些刀子一样的话。可是……沈砺锋呢?
他像一座沉默的山。我看不透。傍晚,他回来了。手里端着两个搪瓷饭盆,还冒着热气。
“食堂打的。吃吧。”他把饭盆放在桌上。一个盆里是糙米饭,一个盆里是白菜炖粉条,
上面盖着几片薄薄的肥肉。油水不多,但分量很足。我默默坐下,拿起筷子。
饭菜的味道很普通,甚至有点寡淡。但我吃得很认真。这顿饭,没人骂我败家,
没人嫌我吃得慢。只有沉默的咀嚼声。吃完饭,他收拾碗筷去外面公用水龙头下洗。
动作利落。我坐在桌边,看着他宽阔的背影。昏黄的灯光下,竟生出一丝不真实的感觉。
这就是……我的丈夫?夜里,我躺在里屋的床上。
能清晰地听到外间他整理东西、铺行军床的窸窣声。还有他平稳的呼吸。隔着一堵薄薄的墙。
很近,又很远。额头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我闭上眼。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未来,
一片混沌。随军的日子,像上了发条的钟,规律又单调。沈砺锋很忙。天不亮就出操,
深夜才回来是常事。偶尔能按时回来吃晚饭,也是匆匆扒拉几口,话极少。
他似乎把沉默刻进了骨子里。我像一只误入军营的鹌鹑,小心翼翼地活着。
家属院里也有别的军嫂。隔壁王营长的爱人赵大姐,是个热心肠。看我总是一个人缩在屋里,
额头上还带着伤疤,主动过来串门。“小苏啊,别总闷着,出来晒晒太阳,跟我们唠唠嗑!
”她拉着我,介绍其他几个军嫂。李连长的爱人刘嫂子,嗓门大,爱笑。孙排长的爱人小周,
年纪和我差不多,有些腼腆。大家都很和气。知道我是新来的,又受了伤,对我格外照顾。
教我生炉子,告诉我哪里的供应点能买到新鲜蔬菜,怎么用煤票、粮票。
“砺锋兄弟是干大事的人,忙!咱们当军嫂的,就得自己把日子支棱起来!
”赵大姐拍着我的肩膀,语重心长。我学着她们的样子,笨拙地操持起这个小小的家。扫地,
洗衣,去供应点排队买菜。偶尔,沈砺锋回来得早,会看到我在院子里晾衣服,
或者对着怎么也点不着的煤炉子较劲。他从不说什么。有时会默默地走过来,
接过我手里的火柴,三两下就把炉子生旺。有时会把我晾得歪歪扭扭的衣服重新抖开,抻平。
动作依旧没什么温度。但那些细微的举动,像冬日里偶尔透出云层的一缕阳光。不炽热,
却足以驱散一点寒意。额头的伤渐渐好了,只留下一道浅浅的粉痕。
日子似乎就这么平静无波地流淌下去。直到那天下午。我正和赵大姐她们在院子门口摘菜。
一辆眼熟的吉普车卷着尘土开进家属院,停在我家门口。车门打开。婆婆张金花和沈玉兰,
拎着大包小包,从车上下来了!我手里的豆角“啪嗒”掉在地上。血液好像瞬间冲到了头顶。
她们怎么找来了?婆婆一眼就看到了我,脸上堆起夸张的笑,几步就冲过来,
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哎哟我的好儿媳!可想死娘了!”那力道,掐得我生疼。
沈玉兰也扭着腰过来,声音甜得发腻:“嫂子!我和娘不放心你,特意来看你!我哥呢?
”周围的军嫂们都好奇地看过来。赵大姐笑着打招呼:“婶子,妹子,
你们是苏晚晚的家人吧?快屋里坐!”婆婆眼珠子滴溜溜转,打量着周围的红砖房,
撇撇嘴:“哎哟,这部队条件也忒艰苦了!还没咱家瓦房敞亮呢!”她嗓门大,
引得更多人侧目。我脸上**辣的,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娘,玉兰,进屋说吧。
”我挣开婆婆的手,声音发紧。把她们让进屋。婆婆一**坐在屋里唯一那把好椅子上,
沈玉兰挨着她坐下。眼睛像探照灯一样在屋里扫射。“啧啧,就这么点地方?
我哥好歹是个排长,就住这?”沈玉兰语气嫌弃。婆婆拍着大腿:“就是!
砺锋也太亏待自己了!晚晚啊,不是娘说你,你这媳妇怎么当的?也不知道收拾收拾,
添置点东西?看这屋里,空荡荡的,像什么样子!”我低着头,站在屋子中间。
像个等待审判的犯人。“娘,部队有规定,不能乱添东西。”我小声解释。“规定?
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婆婆嗓门更高了,“我看你就是懒!在家就笨手笨脚,
到了这儿还是这副死样子!白瞎了我儿子那么多彩礼钱!连个蛋都……”“娘!
”我猛地抬头,打断她。脸涨得通红,手指死死掐着掌心。“你叫我什么?
”婆婆三角眼一瞪,腾地站起来,手指几乎戳到我鼻子上,“反了你了!敢顶撞婆婆?
沈家怎么娶了你这么个丧门星!”沈玉兰在一旁帮腔:“就是!娘大老远来看你,
你不感恩戴德,还顶嘴?哥真是瞎了眼!”污言秽语像冰雹一样砸下来。
周围似乎有邻居探头探脑。屈辱和愤怒像火一样烧着我。就在我浑身发抖,
几乎要站不住的时候。门口光线一暗。一个高大的身影堵在那里。是沈砺锋。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的。军装笔挺,帽檐下的脸,沉得像暴风雨前的海。
屋里的叫骂声戛然而止。婆婆脸上的凶悍瞬间变成了委屈,拍着大腿就要嚎:“砺锋啊!
你可算回来了!你看看你这媳妇!娘好心好意来看她,她……”“出去。”沈砺锋开口了。
声音不高。像淬了冰。两个字,清晰地砸在寂静的屋子里。婆婆的哭嚎卡在喉咙里,张着嘴,
像被掐住脖子的鸡。沈玉兰也吓得往后缩了缩。沈砺锋迈步走进来。军靴踩在水泥地上,
发出沉闷的声响。他走到我身边,高大的身躯像一堵墙,隔开了婆婆那咄咄逼人的视线。
然后,他转过头,目光沉沉地看向婆婆和沈玉兰。那眼神,锐利,冰冷,
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我说,出去。”他又重复了一遍。声音更沉,更冷。
整个屋子的空气都凝滞了。婆婆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
最终在儿子那慑人的目光下,一个字也吐不出来。沈玉兰更是吓得脸都白了,
赶紧去拉婆婆的胳膊。“娘…娘…我们先出去,
哥好像不高兴了…”婆婆被女儿半拖半拽地拉起来,灰溜溜地往外走。走到门口,
还不甘心地回头剜了我一眼。沈砺锋没再看她们。他转过身,面对着我。我低着头,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强忍着不让它掉下来。一只带着薄茧的大手,轻轻落在我肩膀上。很轻。
却带着一种奇异的力量。“没事了。”依旧是没什么温度的声音。却像一股暖流,
瞬间冲垮了我强撑的堤坝。眼泪终于忍不住,大颗大颗地滚落下来。砸在水泥地上,
洇开小小的深色圆点。他没说话,也没动。只是那只手,一直稳稳地放在我肩上。
无声地传递着一种支撑。婆婆和沈玉兰在部队招待所住了下来。显然没打算轻易走。
沈砺锋依旧很忙。但只要在家,婆婆她们就不敢太放肆。顶多用那种淬了毒的眼神剜我,
或者指桑骂槐几句。那天,沈砺锋难得中午回来吃饭。我炒了个土豆丝,煮了点挂面。
刚端上桌。婆婆就拉着沈玉兰进来了。“砺锋啊,吃饭呢?”婆婆脸上挤出笑,
眼睛却盯着桌上那点可怜的饭菜,“啧啧,就吃这个?晚晚啊,你也太不会心疼男人了!
你男人在部队多辛苦,你就给他吃这个?”沈玉兰立刻接口:“就是!哥,你看嫂子,
自己在家肯定吃香的喝辣的,等你回来就对付!一点都不知道顾家!”我端着碗,
手指捏得发白。沈砺锋拿起筷子,夹了一筷子土豆丝,放进嘴里,慢慢嚼着。然后,他抬眼,
看向婆婆和沈玉兰。“你们吃了?”婆婆一愣:“没…还没呢…”“那还不去吃?
”沈砺锋语气平淡,“炊事班开饭时间过了?”婆婆被噎得够呛。沈玉兰赶紧说:“哥,
我们这不是想着陪你和嫂子吃嘛……”“不用。”沈砺锋打断她,声音没什么起伏,
“晚晚做的,够我俩吃。你们去食堂吧。”说完,他不再看她们,低下头,大口吃面。
动作干脆利落。婆婆气得脸都青了,狠狠瞪了我一眼,拉着沈玉兰摔门走了。门关上。
屋里只剩下碗筷碰撞的轻微声响。我低着头,小口吃着面。心里堵着的那口气,莫名地顺了。
面汤的热气氤氲上来,有点模糊了视线。他似乎……总是在这种时候,用最直接的方式,
挡在我前面。几天后,沈砺锋要去更远的山里参加演习。临走前,他给了我一个牛皮纸信封。
“拿着。”他言简意赅,“家里开销。”信封有点厚度。我知道,是他的津贴。
“我…我不用这么多。”我小声说。“拿着。”他又重复了一遍,语气不容置疑,“有事,
找隔壁赵大姐,或者去营部找王干事。”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我的脸,似乎想说什么。
最终只是交代:“自己小心点。”然后,背上行囊,大步离开。他的背影消失在晨雾里。
我心里莫名地空了一下。捏着那个厚厚的信封。第一次觉得,这钱,有点烫手。沈砺锋一走,
婆婆和沈玉兰立刻变本加厉。她们搬进了我们的小屋,美其名曰“照顾我”。实际上,
是把我当成了使唤丫头。“晚晚,去,把这堆衣服洗了!用热水!手洗!
洗衣机那玩意儿洗不干净!”“晚晚,我腰疼,去供应点买两斤排骨回来炖汤!要肋排!
”“晚晚,玉兰想吃供销社新来的点心,你快跑一趟!”我成了她们的佣人。稍有迟疑,
就是劈头盖脸的辱骂。“懒骨头!吃我儿子的喝我儿子的,让你干点活委屈你了?
”“不下蛋的母鸡!白占着茅坑!要不是你,我儿子早娶上能生养的媳妇了!”那些话,
像针一样扎在心上。我只能咬着牙,默默忍受。不想给沈砺锋添麻烦。更不想让邻居看笑话。
那天,婆婆又支使我去山脚下的河边洗被单。被单又厚又重,浸了水,沉得像块石头。
我费力地揉搓着。深秋的河水,冰凉刺骨。手冻得通红麻木。沈玉兰嗑着瓜子,
在旁边监工似的。“用点力!没吃饭啊?洗个被单磨磨蹭蹭!”我咬着唇,使劲揉搓。突然,
脚下一滑!整个人失去平衡,朝冰冷的河水里栽去!“啊——!”我惊恐地叫出声。
刺骨的寒意瞬间包裹全身!河水呛进鼻子和喉咙!慌乱中,我拼命挣扎,
抓住岸边一块凸起的石头。冰冷的河水漫到胸口,冻得我牙齿打颤,浑身发抖。
沈玉兰站在岸上,非但没有拉我,反而拍着手笑起来!“哈哈!活该!笨死你算了!
洗个被单都能掉河里!”她笑够了,才慢悠悠地伸出手。“喏,抓住!
”我颤抖着伸出手去够。就在我快要抓住她手的时候,她猛地缩了回去!脸上带着恶意的笑!
“哎呀,没抓住!你自己爬上来吧!可得抓紧了,别松手啊!”我泡在冰冷的河水里,
看着她那张写满恶毒的脸。心,比河水更冷。绝望像水草一样缠住我。力气在一点点流失。
抓着石头的手指,开始发僵,发麻。难道……要死在这里?就在这时,岸上传来一声暴喝!
“沈玉兰!你找死!”一个穿着绿军装的身影,像一阵风似的冲了过来!是赵大姐的爱人,
王营长!他身后还跟着几个战士!王营长脸色铁青,几步冲到河边,毫不犹豫地跳进水里!
冰冷的河水瞬间没到他大腿。他一把抓住我的胳膊,用力把我从水里拖了上来!“晚晚!
怎么样?没事吧?”他焦急地问。我浑身湿透,冻得嘴唇发紫,说不出话,只是不停地发抖。
王营长立刻脱下自己的军装外套,裹在我身上。然后,他猛地转身,
那双平时总是带笑的眼睛,此刻喷着火,死死盯住岸上吓傻了的沈玉兰。“你!给我滚过来!
”沈玉兰吓得脸都白了,腿一软,差点跪在地上。
“王…王营长…我…我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王营长声音像炸雷,
“眼睁睁看着人掉水里不拉?还故意松手?你这是谋杀军属!你知道什么罪吗!
”他带来的几个战士也围了上来,脸色都很难看。沈玉兰彻底吓瘫了,哭嚎起来:“我没有!
我没有!是她自己没抓住!娘!娘救命啊!”婆婆闻声从屋里跑出来,看到这阵仗,
也吓懵了。“哎哟!这是怎么了?玉兰!我的儿啊!”她扑过去想护住沈玉兰。
王营长根本不看她,指着沈玉兰,厉声道:“把她给我看住了!等沈砺锋回来处理!还有你!
”他目光如刀,射向婆婆,“纵女行凶!部队不是你们撒野的地方!
”婆婆被他的气势吓得一哆嗦,不敢再嚎。“小张!”王营长对旁边一个战士吼道,
“立刻去营部!给演习指挥部发电报!十万火急!让沈砺锋以最快速度给我滚回来!
他家里反了天了!”“是!”战士领命,拔腿就跑。王营长又转向我,语气缓和下来,
带着担忧:“晚晚,走,先去卫生所!别冻坏了!”他招呼另一个战士:“小刘,搭把手!
”我被裹在宽大的、带着体温的军装外套里。被两个战士小心地搀扶着,
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卫生所走。身后,是婆婆惊恐的哭喊和沈玉兰绝望的尖叫。
冰凉的河水似乎还包裹着我。但裹在身上的外套,还有身边这些战士紧张关切的眼神,
像微弱的火苗,一点点驱散着刺骨的寒意。沈砺锋。我脑子里只剩下这个名字。
他……会回来吗?卫生所里。卫生员给我换了干衣服,灌了热水,又打了针。
我裹着厚厚的被子,缩在病床上,还是止不住地发抖。一半是冷的,一半是吓的。
赵大姐闻讯赶来,心疼地抱着我,一个劲骂沈玉兰和婆婆不是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