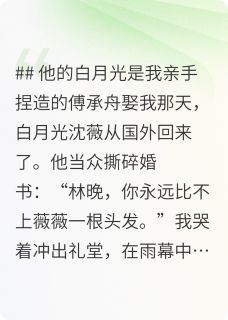
冰冷的液体顺着静脉针管,缓缓注入我的身体。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特有的、有些刺鼻的味道,混合着高级病房里若有似无的香氛,形成一种矛盾而紧绷的气息。**在床头,身上已经换上了干燥柔软的纯棉病号服,湿透的婚纱像一个被丢弃的噩梦,不知被护士收拾去了哪里。
脚踝处传来一阵阵闷痛,医生说是韧带扭伤,已经做了处理,裹上了厚厚的弹性绷带。
病房门被无声地推开。
傅承洲走了进来。他脱去了那件被雨打湿的大衣,只穿着一件质地精良的深色衬衫,袖口随意地挽到手肘处,露出线条流畅的小臂。他手里拎着一个保温桶,步履从容,脸上依旧是那副波澜不惊的表情,仿佛几个小时前在傅家那场惊天动地的闹剧从未发生过。
“醒了?”他把保温桶放在床头柜上,旋开盖子,一股温热清甜的米粥香气飘散出来,“吃点东西。”
他的目光落在我裹着绷带的脚踝上,停留了一瞬,才移回我的脸:“医生怎么说?”
“扭伤。”我的声音有些沙哑,像砂纸摩擦过喉咙,“没什么大事。”
“嗯。”他应了一声,语气平淡无波。他盛出一小碗粥,递到我面前。勺子轻轻磕碰着碗沿,发出清脆的声响。
我没有接,只是抬起眼,定定地看着他。病房顶灯的光线落在他镜片上,反射出一点冷光,让我看不清他眼底真实的情绪。雨水带来的冰冷似乎还残留在骨髓里,但更冷的,是傅承洲那句话带来的寒意。
“游戏才刚开始……”我重复着他那句如同魔咒的低语,声音干涩,“傅承洲,你什么意思?你早就知道沈薇会回来?还是说……这一切都在你的预料之中?”
傅承洲端着粥碗的手稳稳地停在半空,对我的质问没有表现出丝毫意外。他镜片后的目光平静地迎上我探究的视线,嘴角甚至勾起一丝极淡、几不可察的弧度,那弧度里没有温度,只有一种洞悉一切的漠然。
“预料?”他轻轻反问,声音低沉平缓,像在陈述一个无关紧要的事实,“沈薇对傅承舟意味着什么,整个北城谁不知道?那是他心口上剜不掉的一块肉,是他傅承舟活了**十年,唯一像个活人的时候。”
他微微俯身,将粥碗放在床头柜上,动作不疾不徐。那温热的香气此刻闻起来竟有些讽刺。
“我那位好大哥,”他直起身,双手随意地**西裤口袋,姿态带着一种置身事外的疏离,“精明、冷酷、掌控欲强到变态。可唯独在沈薇这件事上,他像个彻头彻尾的蠢货,被过去那点所谓的‘救命之恩’蒙蔽了双眼,心甘情愿地画地为牢。”
“救命之恩?”我捕捉到这个关键的字眼,心脏莫名地紧了一下。傅承舟对沈薇的执念深到可怕,难道仅仅是因为爱情?这背后……
傅承洲仿佛看穿了我的疑惑,他踱步到窗边,背对着我,望着窗外依旧没有停歇的雨幕。城市的霓虹在雨水中晕染成一片模糊的光团。
“十年前,城西废弃的化工厂大火。”他的声音透过雨声传来,带着一种奇异的穿透力,“傅承舟那时年轻气盛,不知天高地厚,为了一个所谓的项目赌约,半夜独自闯了进去。结果……意外失火。火势蔓延得极快,他被困在里面,差点被活活烧死。”
窗玻璃上倒映着他模糊的侧影,平静无波。
“是沈薇。”他缓缓吐出这个名字,“据说她当时恰好路过,不顾危险冲进火场,拼死把昏迷的傅承舟拖了出来。她自己背部被掉落的燃烧物严重灼伤,留下了一大片难看的疤痕。傅承舟醒来后,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守在他床边、背上缠满纱布的沈薇。”
他转过身,镜片后的目光重新落在我脸上,带着一丝冰冷的审视:“从那一刻起,沈薇就成了他生命里唯一的光,唯一的救赎。是刻在他骨头里的执念。你觉得,这样的执念,会因为另一个女人的出现,或者几年的分离,就轻易消失吗?”他嘴角那抹讽刺的弧度加深了些许,“林晚,你未免太高估自己,也太低估傅承舟的愚蠢了。”
我的指尖无意识地抓紧了身下的被单。废弃工厂大火……十年前……背部灼伤……
这些信息碎片在我脑中飞速旋转、碰撞。傅承舟书房里那张被他摩挲得发旧的、沈薇背影的照片,照片上她穿着露背礼服,肩胛骨下方那片狰狞扭曲的皮肤……原来如此。这就是他认定的、永不磨灭的恩情烙印。
“所以,”我的声音有些发紧,“你早就知道沈薇回来会毁掉这场婚礼?你当时等在门口,不是巧合?”
傅承洲没有直接回答。他走回床边,重新端起那碗已经有些温凉的粥,用勺子轻轻搅动着,动作优雅得像在调制一杯咖啡。
“傅承舟需要一个理由撕毁和你的婚约,或者说,他内心深处一直在等待这个理由。”他舀起一勺粥,递到我唇边,语气平淡得像在谈论天气,“沈薇的出现,就是那个最完美、最不容他抗拒、也最能说服他自己的理由。我只是……恰好预判了他的预判。”
“而你,”他的目光落在我被迫微微张开的唇上,带着一种审视物品般的冷静,“需要一个足够强大的外力,把你从那场注定是牢笼的婚姻里拖出来。或者说,让你彻底看清傅承舟的真面目,斩断你心里那点不切实际的念想。这样,你才能心甘情愿地,成为我棋盘上最有用的一颗棋子。”
勺子抵在我的唇边,温热的米粥气息钻入鼻腔。我没有张嘴,只是死死地盯着他镜片后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睛。
棋子?外力?看**面目?
心脏在胸腔里剧烈地跳动,撞击着肋骨,分不清是愤怒还是后怕。原来我自以为的挣扎和痛苦,在傅承洲眼中,不过是一场精心安排的“外力介入”?他像一个冷静的棋手,站在棋盘之外,看着我们这些棋子按照他预想的轨迹互相撕咬、互相毁灭。
“傅承洲,”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异常冷静,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你到底想要什么?”
他没有收回勺子,只是微微歪了歪头,镜片反射着顶灯的光,像某种冷血爬行动物的眼睛。
“很简单。”他唇角勾起,那笑容冰冷而笃定,带着一种势在必得的掌控感,“我要傅承舟拥有的,失去他所珍视的。我要他……从云端,跌进泥里。”
他的目光扫过我缠着绷带的脚踝,语气带着一丝命令式的残忍:“养好你的伤,林晚。这场戏,少了你可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