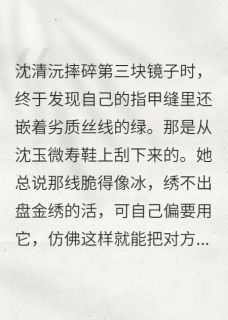
沈清沅摔碎第三块镜子时,终于发现指甲缝里嵌着的绿。
那是从沈玉微寿鞋上刮下的丝线碎屑。劣质涤纶遇热泛出的荧光绿,像块洗不掉的疤。
她总说这线脆得像寒冬的冰,绣不出盘金绣的活气,
可自己偏要用它——仿佛这样就能把对方钉在"粗鄙"的标签上,钉进沈府的尘埃里。
"姐姐的云纹绣谱借我瞧瞧?"她捏着绣帕笑,指尖却在谱子边缘掐出深深的折痕,
像要把那些娟秀的字迹掐死在绢布上。沈玉微正在绣凤凰尾羽,
赤金缕线在绢布上游走如活物。"你学不会的。"她头也未抬,银针穿透布面的瞬间,
金线突然亮了亮。"凭什么?""盘针要像流水绕石,"对方终于抬眼,眸光比丝线还亮,
"而你心里的针,太急。"1、沈玉微指尖触到云纹绣帕的刹那,指腹被那涩意蜇了一下。
丝线在掌心爬动,带着沙砾磨过粗布的糙感。这不是生母留下的苏绣。贡品苏绣该是润的,
像江南晨露浸过的白梅瓣,存再久,纤维里也锁着三分水汽,
捏在手里能觉出那点不肯服帖的韧劲。她把帕子翻过来,针脚歪得像被狂风揉乱的蛛丝,
打籽绣的结头松垮垮敞着口,能塞进半根手指——这手艺,绣坊里三年的学徒都要撇嘴的。
"偷东西的贱婢!"沈清沅的尖叫淬了冰,扎得人耳鼓发麻。藕荷色罗裙扫过沈玉微手背,
那凉意比深秋草叶上的霜还重。"侯府三公子送的定亲信物,你也配碰?"沈玉微攥紧帕子,
指腹碾过那些歪扭的针脚。这不是侯府的活计,是街角"锦绣阁"阿翠姑娘的手笔。
上个月她还在那绣坊帮工,认得阿翠针脚里藏的小性子——第三针总爱多绕半圈,
像姑娘家闹别扭时撅起的嘴。"我没偷。"她声音轻得像羽毛,带着绣坊里泡久了的皂角香。
三天前被沈府的人从绣架前拽走时,怀里还揣着没绣完的帕子,
那股草木清气至今缠在衣襟上,洗不净,也褪不去。"还敢犟!"沈父从雕花屏风后转出来,
手里翡翠珠串被捏得咯吱响。他瞥向沈玉微袖口沾的线头,眉峰拧成个死结,
"刚从乡下捞回来就不安分,当我沈府是收破烂的?"沈玉微垂下眼。三天前,
这对父女把她从绣坊拽回来,说她是沈府流落在外的真千金。此刻他们看她的眼神,
比看门口讨饭的还嫌恶。就因她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靛蓝染料,指腹带着握针磨出的茧子?
就因她袖口沾着的线头,不是沈府惯常使用的贡品云锦线?"爹,妹妹许是不懂规矩。
"沈清沅挽住沈父胳膊,鬓边珍珠步摇晃得人眼晕。指尖划过鬓角,新染的蔻丹在阳光下闪,
像在炫耀什么,"她在绣坊长大,哪见过这般金贵物事?要不就......""不行!
"沈父打断她,目光像剪刀刮过沈玉微的脸,"今日不罚,日后还不知要闹出多少笑话!
来人,拖去柴房,没我的话,不许出来!"两个小厮架起胳膊时,帕子从怀里滑出来,
落在地上。沈玉微看见沈清沅弯腰去捡,指尖在帕角云纹处顿了顿,
眼里闪过一丝慌——那云纹绣得挤挤挨挨,连最基本的"水路"都没留,
明眼人一瞥就知是仿的。仿得急,仿得糙,像生怕慢一步就会露馅。
柴房的霉味呛得人喉咙发紧。沈玉微靠住冰冷的土墙,从怀里摸出个油布包。
半块绣了一半的屏风露出来,是绣坊掌柜塞给她的,生母的遗物。凤凰尾羽用的赤金缕线,
在昏暗中泛着柔得发绵的光,虫蛀了几个小洞,金线的韧劲仍在,
捏在手里能觉出那点不肯断的固执。指尖抚过金线,她忽然笑了。沈清沅大约不知道,
真正的云纹绣,每一针都藏着记号。就像她指腹的茧,分布在指节和掌心的特定位置,
是十几年针杆磨出来的,仿不来的。就像这赤金缕线,要在晨露未干时拆成七缕,
混着蚕丝捻匀,才能在绢布上生出流动的光——这些,偷来的绣谱上不会写。
2、沈玉微被拖出柴房时,灯笼纸的腥气正往鼻孔里钻。丫鬟们抱着丝线穿梭,
胭脂混着香粉的甜腻漫过来,像发了酵的蜜,腻得人舌尖发苦。沈清沅坐在梨花树下,
描金笔在绢布上顿着,阳光穿过花瓣,在她身上绣出细碎的光斑,
倒比她绷上的"八仙过海"鲜活。"妹妹醒了?"沈清沅抬头,笑在脸上凝着,甜得发僵。
描金笔在"铁拐李"的拐杖上顿了顿,"帮我瞧瞧,这'八仙'用什么色线称?
"沈玉微走过去,目光落在绣绷上。铁拐李的拐杖歪得像被踩过的蛇,
何仙姑的裙摆比例失了准头,吕洞宾的拂尘飘带硬挺挺的,活像条晒干的鳝鱼。
她捏起根朱红线,指腹碾了碾——线在指缝里脆生生断了,断口泛着白茬,
像被虫蛀过的棉絮。"这线掉色。"沈清沅脸色僵了僵,手指绞着帕子:"怎么会?
苏州带来的上等货,二两银子才得这一小绺。""上等线不这样脆。
"沈玉微将断线凑到眼前,"苏绣线经得住三折,松开还能直回来。
去年绣坊收过类似的'西洋线',绣好的屏风挂了不足月,红就褪成了残霞色,
雇主的拐杖差点砸穿柜台。"沈清沅的声音拔尖了些:"妹妹在乡下待久了,不懂这新染法。
看着脆,实则——"她卡了壳,指尖在帕子上抠出个小洞,"......总之是好东西。
"沈玉微没接话,转身要走。"站住!"沈清沅的声音带着命令。起身时带倒了线筐,
五颜六色的线轴滚了一地,像撒了把碎珠子。"祖母寿辰近了,你既会绣,就做双寿鞋。
也让她瞧瞧,我沈府的女儿,不只会做粗活。"沈玉微接过丫鬟递来的绸缎与线,
指尖刚触到线团,就觉出那糙意——是掺了涤纶的次货,纤维短脆,走不了"盘金绣",
最多能走几道平针。沈清沅眼里的得意漫出来,像偷食得逞的猫。沈玉微忽然想笑,这伎俩,
好比绣坊里最劣的仿品,针脚里全是破绽。"好。"她应着,抱了东西回小院。
院里石榴树的枝桠光秃秃的,指向灰蒙蒙的天,像谁随手画的败笔。夜来时,
油灯在案头跳着。沈玉微对着劣质线团发怔,忽然从油布包里摸出赤金缕线。
金线细得像蛛丝,她抽出几缕,混进绛红线里。指尖捏着针,
第一针从鞋头的牡丹花苞扎下去,金线在绛红里若隐若现,像晨露在花瓣里藏的光。
她要绣一双寿鞋。用最次的线,绣出最活的花。让所有人看看,
好手艺能让糙线开出花来——就像她自己,在泥里滚过,也能凭着这双手,站成自己的模样。
3、沈玉微将寿鞋捧给祖母时,沈清沅的眼亮得像淬了火的针。鞋面上的重瓣牡丹正开得烈,
近看是绛红丝线,远了瞧,却有层淡金在花瓣间流,像朝霞被揉碎了铺在上面。
牡丹边缘的针脚时密时疏,是"虚实针"的手法,让花瓣鼓出立体的褶,像能掐出露水来。
"这......怎绣出来的?"祖母枯手抚过花瓣,指腹在针脚处顿了顿。
她年轻时见多了好东西,此刻眼里的惊奇藏不住。"掺了点金线。
"沈玉微的声音轻得像丝线,"拆成细丝混在绛红里,不惹眼,却能看出心。
"沈清沅的笑突然炸开,带着刻意的尖:"妹妹好手段,只是这线......看着眼熟,
莫不是我上月丢的贡品苏绣线?"沈玉微指尖一颤。贡品苏绣线是侯府送的,
一两抵十两银子,沈清沅当日宝贝得藏在樟木箱里,锁匙贴身戴着,怎会丢?她抬眼,
沈清沅眼里的算计像没藏好的线头,支棱着刺人。"清沅胡吣什么!
"祖母把寿鞋往怀里拢了拢,瞪她一眼,"玉微刚回府,哪来的贡品线?这线看着寻常,
没那金贵光泽。"沈清沅低下头,声音委屈得发颤,指尖却在帕子上抠,
把朵兰花绣得脱了线:"许是我记错了......祖母别气,妹妹有这份心,
孙儿该替您欢喜。"沈玉微没作声。她知道这只是开始。沈清沅的怨毒藏在眼底,
像绣错了色的线,遮不住的。定亲宴前三日,沈清沅的"八仙过海图"挂在了客厅中央。
女眷们围着称赞,声音像撒了把碎银。"清沅**的手艺越发精了!""这铁拐李的拐杖,
绣得活过来似的!"沈玉微立在人群外,看着那幅绣品,突然觉得喉咙发紧。
铁拐李的拐杖用了平针,针脚排得像条僵蛇;何仙姑的裙摆用了粗线,笨得像捆柴。
最刺目的是满幅的挤,连"水路"都没留,图案堆得像要从绢布上溢出来——这哪是绣品,
分明是急着邀功的堆砌。"妹妹觉得如何?"沈清沅凑过来,腰间玉佩撞在绣绷上,
叮当作响。她把绣绷往沈玉微面前送,炫耀像没藏好的线头。沈玉微看着她,突然开口,
声音不高,却够周围人听见:"这绣品,不是你一人绣的吧?"沈清沅的脸唰地白了,
像被泼了井水:"你胡说!""铁拐李的拐杖用平针,何仙姑的裙摆用盘针。
"沈玉微的指尖点过绣面,"平针的线头藏在背面,盘针的却露着,
明眼人一看就知是生手绣的。"女眷们的窃窃私语漫过来,像潮水上了岸。
"好像......真不一样。""盘针的地方是糙些。"沈清沅突然拔高声音,
脸涨得通红:"你们懂什么!这是新绣法!铁拐李朴实,用平针;何仙姑灵动,用盘针!
"话没说完,一个喷嚏打出来,刚绣的莲花震得掉了线头。这番话漏洞像没锁好的门,
却把女眷们唬住了。谁也不愿得罪未来的侯府少奶奶,笑着打圆场,把话岔了过去。
沈玉微没再理,转身出了客厅。她知道多说无益。定亲宴那日,自会有分晓。
书房的门虚掩着,墨香混着旧书味漫出来,像生母绣架旁的气息。
沈玉微的目光爬上书架最高层,紫檀木盒子的锁扣上,
刻着朵祥云——和生母屏风上的一模一样。她搬来凳子,踮脚取下盒子。铜锁咔嗒开了,
里面躺着本线装绣谱,封面上"云纹绣法详解"六个字,是生母的笔迹,娟秀里藏着韧。
第一页上,生母写着:"云纹绣,贵在活。一针一线要如流水,忌僵。
"沈玉微的指尖抚过字迹,泪突然砸在纸页上,晕开一小团湿。原来母亲一直在这里等她,
留着最重要的东西。那些年在绣坊的苦,那些被人嘲笑的"粗鄙",突然都有了归宿。
4、侯府定亲宴的红绸子从大门缠到后院,风一吹,像条活过来的火龙。
宾客们的衣香鬓影里,虚伪的笑沾着脂粉气,
眼角却都往客厅中央瞟——沈清沅那幅"八仙过海图"挂在最显眼处,
针脚歪得像没牵直的线。沈清沅裹着大红礼服,凤冠上的宝石晃得人眼晕。
她时不时踮脚望门口,嘴角的笑僵着,像绣绷上绷太紧的绢布。沈玉微立在角落,
月白衫子素得像没染色的坯布。手里的云纹绣谱被指尖摩挲得发暖,封面的祥云磨出了浅痕。
心湖静得很,像绣完最后一针的绷面。侯夫人的石青色诰命服踏进门时,空气都凝了凝。
陪房们的目光带着秤砣,称着满厅的虚礼。她的眼扫过红绸,掠过宾客,
最后落在"八仙过海图"上。"这绣品倒热闹。"侯夫人笑着走近,玉扳指抚过绣面,
在铁拐李的拐杖处停了停。沈清沅往前凑了凑,声音甜得发腻:"绣了三个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