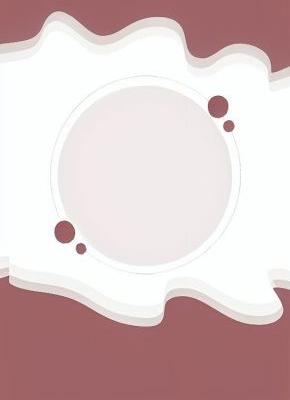
逃荒路上,我捡了个娇贵的小少爷。他连野菜都认不全,却理直气壮使唤我:“你是我夫君,
不该养我吗?”后来我为护他被打断腿,他哭着给我上药:“你、你不许死……我只有你了。
”我揉揉他脑袋:“那下次换你养我?”他涨红脸把全部家当塞给我——三枚铜板,
和一朵野花。(双男主)---热风裹着沙土,刮过龟裂的田埂,
也刮过人干裂的嘴唇和望不到头的路。赵铁牛走在逃荒的人流里,
像一块沉默的、会移动的石头。他个子高,骨架大,粗布短打被汗水反复浸透,晒干,
硬邦邦地贴在身上,勾勒出常年打猎劳作攒下的结实身板。脸上皮肤黝黑粗糙,
浓眉压着一双沉静的眼睛,嘴唇总是习惯性地抿着,不说话。背上一个灰扑扑的包袱,
手里提着一根磨得光亮的木棍,既是探路,也是防身。他不大跟人扎堆,只闷头走自己的路,
偶尔抬头望望灰黄的天,估算着还有多久能到下一个可能找到水的地方。爹娘前些年病没了,
就剩他一个。山里猎户出身,力气有,也认路,会找些野物果腹,
在这条望不到头的逃荒路上,比起周围那些拖家带口、面黄肌瘦的同路人,
他算得上是“从容”了。只是心里头空落落的,跟这被晒得冒烟的荒野一样。
日头渐渐毒起来,人流慢了下去,寻了处背阴的土坡歇脚。赵铁牛找了块大石头坐下,
从包袱里摸出半块硬得硌牙的杂粮饼子,就着皮囊里仅剩的一点水,小口小口地啃。
周围弥漫着疲惫的喘息和孩童细弱的哭声。就在这时,一阵突兀的嘈杂声从前头传来,
夹杂着几声粗野的喝骂和一个清亮、却明显带着慌乱的争执声。“放手!这水囊是我的!
”“你的?小娘子,这路上捡着的就是爷的!识相点,把身上值钱的玩意儿都交出来!
”赵铁牛皱眉望去,只见几个流里流气的汉子围住了土坡另一侧一个孤零零的身影。
被围住的是个少年,穿着一身料子明显不错、但此刻已经脏污破损的月白色长衫,头发散乱,
脸上也蹭着灰,可即便这样,也掩不住那份与周遭格格不入的精致和……娇嫩。
皮肤是晒不黑的那种白,此刻因愤怒和焦急染上薄红,眼睛很大,睫毛湿漉漉的,咬着下唇,
死死抱着怀里一个锦绣水囊不撒手。“我不是小娘子!这水是我……我家人留给我的!
”少年声音带着颤,却还努力挺直那细瘦的脊梁。“哟呵,还嘴硬!
”一个疤脸汉子伸手就去抢。少年惊叫一声,下意识往后躲,脚下被乱石一绊,
整个人朝后摔去。水囊脱了手,被那疤脸汉子一把捞住。赵铁牛就是在这一瞬间站起来的。
他没多想,身体比脑子动得快。那块硬饼子被他随手塞回包袱,提着木棍就走了过去。
“东西还他。”他的声音不高,甚至有点闷,但配上那堵墙似的身板和没什么表情的黑脸,
自有一股压迫力。疤脸汉子一愣,上下打量他,随即嗤笑:“哪来的愣头青,想充好汉?
滚一边去!”赵铁牛没滚。他往前走了一步,木棍杵在地上,看着疤脸汉子手里的水囊,
又重复了一遍:“还他。”另外两个同伙围了上来,眼神不善。逃荒路上,
为了一口水打死人的事不新鲜。少年跌坐在地上,仰头看着突然出现的陌生高大男人,
忘了哭,也忘了喊,只是呆呆地看着。疤脸汉子被赵铁牛那沉静的目光看得有些发毛,
但众目睽睽,不能输了气势,啐了一口:“找死!”挥拳就朝赵铁牛面门砸来。
赵铁牛侧身避过,动作不快,但恰到好处,同时左手探出,
像铁钳一样攥住了疤脸汉子的手腕,反向一扭。疤脸汉子惨叫一声,水囊掉在地上。
赵铁牛脚尖一挑,水囊飞起,他看也没看,抬手接住,然后手腕一抖,木棍横扫,
逼退了另外两个想扑上来的家伙。干净利落,没一句废话。疤脸汉子捂着手腕,
疼得龇牙咧嘴,知道碰上了硬茬子,狠狠瞪了赵铁牛一眼,又贪婪地瞟了瞟地上的少年,
终究是没敢再上,带着同伙骂骂咧咧地走了。围观的人群窃窃私语,
很快又恢复了死气沉沉的安静,各自缩回自己的角落。乱世里,自保是常态。
赵铁牛这才转过身,走到少年面前,蹲下,把水囊递过去。少年没接,还是呆呆地看着他,
大眼睛里映着赵铁牛棱角分明的脸。离得近了,赵铁牛才看清,这少年生得是真好看,
像年画上的瓷娃娃,只是此刻瓷娃娃脸上脏兮兮,头发乱糟糟,嘴唇干得起皮,
眼神里透着惊魂未定和浓浓的茫然无助。“你的。”赵铁牛把水囊又往前递了递,
声音依旧闷闷的。少年长长的睫毛颤了颤,终于回过神,猛地一把抓过水囊,紧紧抱回怀里,
像是抱着救命稻草。然后,他抬起头,泪水毫无预兆地滚落下来,大颗大颗的,
顺着沾满灰尘的脸颊滑落,冲出一道道白痕。“谢……谢谢……”他抽噎着,哭得直打嗝,
毫无形象,却有种惊人的脆弱感。赵铁牛心里那处空落落的地方,好像被这眼泪烫了一下。
他有点无措,张了张嘴,干巴巴地说:“不用谢。能起来吗?”少年试着动了一下,
立刻“嘶”了一声,眉头紧紧皱起,露出痛苦的神色。他的脚踝扭了,
刚才摔倒时还擦破了手掌和膝盖,血迹混着沙土,看起来有点惨。赵铁牛眉头也拧了起来。
他沉默地解下自己包袱,从里面翻出一小块相对干净的粗布,
又拿起自己的水囊——里面水也不多了,犹豫了一下,还是倒出一点点,浸湿了布角。
“忍着点。”他说,然后不由分说,拉过少年擦伤的手掌,用湿布小心地擦拭掉上面的沙土。
动作不算轻柔,但很仔细。少年疼得直吸气,却咬着唇没缩手,只是眼泪掉得更凶了,
砸在赵铁牛粗粝的手背上。擦干净手,赵铁牛看了看他肿起来的脚踝和擦破的膝盖,想了想,
转身背对着他蹲下:“上来。这里不能久留。”少年看着眼前宽阔的、被汗水浸透的脊背,
愣了愣,哭声小了下去,变成小声的抽噎。他犹豫着,慢慢伸出手,环住了赵铁牛的脖子。
赵铁牛稳稳地站起来,单手托住他,另一只手拿起木棍和包袱。少年很轻,
背在身上几乎没什么分量,骨头硌人。那股淡淡的、混合着汗味和尘土气息的味道涌上来,
并不难闻,反而有种奇异的踏实感。少年把脸轻轻贴在那汗湿的背上,眼泪无声地流。
走出一段距离,离开了那片歇脚地,赵铁牛才开口,声音因为负重而有些低沉:“叫什么?
去哪?”背后的少年安静了一会儿,才带着浓浓的鼻音小声说:“我叫……林玉安。
去……去雍州投亲。”顿了顿,声音更低了,像是自言自语,“爹娘……都没了。
管家也走散了……”赵铁牛脚步顿了一下,没再问。投亲?这兵荒马乱的,
雍州远在千里之外,一个娇生惯养、毫无自保能力的小少爷,能找到亲戚的可能性有多大,
他心里清楚。这世道,有时候孤身上路,反而更安全些。他没说话,只是背着林玉安,
一步步往前走。日头偏西,风依旧燥热。傍晚时分,赵铁牛找到一处相对避风的岩壁凹陷处,
决定在这里过夜。他放下林玉安,让他靠着岩壁坐下,自己则迅速捡来一些干柴,
生起一小堆火。火光跳跃起来,驱散了些许寒意和黑暗。林玉安抱着膝盖,
看着赵铁牛沉默地忙碌,从包袱里拿出最后小半块饼子,掰开,将明显大一些的那半递给他。
“吃。”林玉安接过,盯着那黑乎乎的、粗糙的饼子,没动。
赵铁牛已经自顾自啃起了自己那一小半。过了好一会儿,林玉安才小口咬了一下,
随即眉头紧紧皱起,努力咀嚼了半天,才勉强咽下去,脸都皱成了一团。
他看了看赵铁牛面不改色吞咽的样子,又低头看看手里的饼子,忽然小声开口,
带着点理所当然的委屈:“这个……好硬,剌嗓子。没有别的吗?”赵铁牛抬眼看他。
林玉安被他看得有点心虚,但委屈感占了上风,
继续小声嘟囔:“我……我以前早上喝燕窝粥,配四样细点,午膳至少八菜一汤,
晚膳……”他说不下去了,因为赵铁牛的眼神没什么变化,只是默默收回了目光,
继续啃自己的饼子。林玉安瘪瘪嘴,肚子却不合时宜地叫了起来。他红着脸,闭上眼睛,
视死如归般又咬了一口饼子,用力嚼着。夜里风大,岩壁缝隙里灌进来的风呜呜作响。
林玉安裹紧了自己破损的绸衫,还是冷得直哆嗦,牙齿轻轻打颤。
他偷偷瞄了一眼几步外和衣躺下的赵铁牛,那高大的身影在火光映照下显得格外安稳。
犹豫了再犹豫,他一点点挪过去,挨着赵铁牛的手臂躺下,汲取那一点点热源。
赵铁牛身体僵了一下,没动,也没推开他。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赵铁牛就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