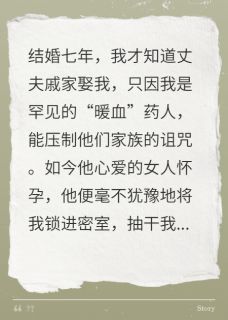
结婚七年,我才知道丈夫戚家娶我,只因我是罕见的“暖血”药人,能压制他们家族的诅咒。
如今他心爱的女人怀孕,他便毫不犹豫地将我锁进密室,抽干我的生命力为她续命。
他不知道,我母亲的遗物暖玉观音,是锁住我气运的封印。当他逼我交出玉佩的那一刻,
封印已解,猎杀开始。看着他家破人亡、跪地求饶的样子,他终于傻眼了。
1戚泊君的“福星”怀孕了。十年一次的戚家祭祖大典,
他把那个叫舒晚的女人直接领进了祠堂。他看都没看我一眼,
像吩咐一个下人般开口:「舒晚命格金贵,闻不得油烟,以后家里的三餐你来准备,
菜谱每天送到她房里,由她亲自点。」「还有,她身子弱,怕阴气,晚上一个人睡不安稳。」
戚泊君的声音没有一丝温度,「把你东院的东西收拾一下,搬去西跨院。我陪她。」
戚家的西跨院,是用来锁疯子的。我没吭声,转身拖出角落里早就收拾妥当的行李箱,
箱子的滑轮碾过昂贵的大理石地面,发出刺耳的噪音。管家脸上闪过一丝不忍,
想上来说什么,却被戚泊君一声嗤笑打断。「由着她疯。」他揽着舒晚的腰,
嘴角勾出一个看死人似的弧度,「整个京城谁不知道,她岑漾离了我戚泊君,
就是一条连宗祠都进不去的丧家犬。我跟你们赌,不出十二个时辰,
她就会哭着滚回来求我开门。」话音一落,戚家那帮看热闹的亲戚瞬间爆发出哄笑。
他们甚至当着我的面,开了个五千万的盘口。赌我岑漾今晚就会跪在大门口,
像条哈巴狗一样,舔着脸求戚泊君的收留。他们都忘了,我岑漾,曾经也是有家的。
也没人知道,戚家铁门外那辆黑色的宾利,已经等了我一个小时。这一次,我不是闹脾气。
我是要他的命。2就在我的手即将碰到冰冷的大门把手时,戚泊君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像一条淬毒的鞭子。「站住。把你脖子上的暖玉观音解下来,给晚晚。」
那块玉观音是我妈留给我唯一的遗物,据说能用体温养着玉,玉也能反过来滋养人。
我缓缓转身,眼圈一瞬间就红了,死死地瞪着他。他脸上满是不耐,
好像我的悲伤是什么脏东西。「别用那种眼神看我。」他从钱包里抽出一张黑卡,扔在地上,
「给你钱,别耍脾气。」我嫁给他七年,像个傻子一样,用我所谓的“暖血体质”,
去中和他们戚家人世代相传的“寒症”,像个活体暖炉一样被利用。这段婚姻值多少钱?
我懒得算。我只记得,上一次舒晚说喜欢我的狐裘大衣,我没给,
戚泊君就让保镖把我扒光了锁在顶楼的露台上,冻了一夜。那一夜,我们的第一个孩子,
就那么悄无声息地化成了一滩血水。我闭上眼,伸手颤抖地解下脖子上的红绳。
走到舒晚面前,将那块已经被我体温捂得温热的玉观音,戴在她纤细的脖子上。舒晚的脸上,
是毫不掩饰的、胜利者的微笑。我对着她的肚子,一字一句地说:「祝你,
还有你肚子里的东西,都平平安安,长命百岁。」或许是我顺从得太快,
戚泊君的脸色竟缓和了几分,他破天荒地施舍了一丝怜悯:「岑漾,只要你听话,
我戚家的继承人,将来也一样叫你一声妈。」仿佛是印证他话里的虚伪,他话音刚落,
舒晚尖叫一声——那块暖玉观音像是被什么东西烫到,从她脖子上猛地滑落。“啪”的一声,
碎成了几瓣。一片锋利的碎玉,正好划破了舒晚的小腿,渗出殷红的血珠。「晚晚!」
戚泊君瞬间脸色大变,一把将她打横抱起,对着周围的佣人厉声咆哮:「家庭医生呢?
让他三分钟内滚过来!」那紧张的模样,引得周围的宾客都用看笑话的眼神瞟着我。这一幕,
何其可笑。就在上个月,我的“寒症”突然发作,浑身冷得像冰块,连路都走不稳,
就差口吐白沫了。而戚泊君,正要带舒晚去马尔代夫度假。我拉着他的裤脚求他别走,
他却嫌恶地一脚踢开我,面不改色地从我快要僵硬的身体上,直接跨了过去。
在我失去意识前,我最后听到的是他冰冷的嘱咐:「找人把这块地毯烧了,别等晚晚回来,
闻到晦气。」现在,他那滔天的怒火终于对准了我。行李箱被他一脚踹翻,
我的手腕被他死死攥住,力道大得像是要捏碎我的骨头。「道歉。」「……什么?」
话没说完,一股巨力将我掀翻在地。我整个人被他拖拽着,跪在了舒晚面前。
膝盖狠狠磕在破碎的玉石上,瞬间鲜血淋漓。戚泊君看到血,像是看到了什么病毒,
立刻甩开了我的手,眼神里全是嫌弃。「你故意弄坏晚晚的观音,还害她见了血,
难道不该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嫁给戚泊君之后,这三个字说的比“我爱你”多一万倍。
给他炖的补汤咸了,对不起。怕他应酬喝坏身子,多发了条信息提醒他,
打扰了他和舒晚约会,对不起。无意中看到舒晚手机里存着我流产那天,
戚泊君陪她看日出的照片,多看了两眼,也对不起。我把嘴唇咬出一股铁锈味,
从地上缓缓撑起身体,对着舒晚,深深地、一百八十度地鞠了一躬。一遍又一遍。「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直到舒晚的脸色从得意变得有些不安,我才直起身,漠然地转向戚泊君,
嘴角的血珠滚落,声音轻得像鬼魅。「戚总,够了吗?」他盯着我嘴角的血,
喉结剧烈地滚动了一下,胸口起伏。「岑漾,戚家的老爷子已经死了,
你装出这副恶心的样子,是想给哪个孤魂野鬼看?」话音未落,家庭医生提着药箱冲了进来。
戚泊君一把将我撞开,领着医生冲到舒晚身边,仿佛我是什么会传染的病毒。
趁着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那道金贵的伤口上,我拖着残破的行李箱和残破的身体,一步一步,
走向那扇我期盼了无数个日夜的大门。然而,铁门在我面前缓缓打开,夜风还未吹到我脸上,
两个黑衣保镖就像铁塔一样挡住了我的去路,面无表情地做了个“请”的姿势。「夫人,
戚总有请。」不是请,是押送。我被重新带回了这座金丝笼。这一次,
迎接我的是戚家祖宅深处,那间从不示人的密室。3密室里没有窗,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陈腐的檀香味。我被他们用牛筋绳五花大绑在正中央的一张寒玉床上,
手腕脚腕都被精铁的镣铐锁死。一个穿着唐装、仙风道骨的老头,指挥着下人,
在我周围的地板上,用朱砂画着我看不懂的符咒。半开的门缝外,
传来家庭医生和戚泊君的对话,医生的声音里带着无法掩饰的恐惧:「戚总,
岑夫人的‘寒症’本就严重,全靠那股气血吊着。您要是用老先生这个阵法强行‘渡气’,
等于是釜底抽薪,她、她很可能会当场休克的!」「你废话太多了。」
戚泊君的声音冷得像冰,「我花钱请你,是让你保证晚晚安然无恙,至于其他的,
轮不到你操心。」脚步声越来越近,我缓缓闭上了眼睛,连多看他一眼都觉得恶心。
他走到我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我,那张曾经让我痴迷的脸上,此刻只剩下陌生的冷酷。
破天荒的,他的语气里竟然带上了一丝……安慰?「很痛苦吗?忍一忍,
等晚晚肚子里的孩子稳固下来,就结束了。」我猛地扭过头,拒绝和他进行任何交流。
那种感觉,就像是把活人的灵魂一丝一丝抽离身体,再灌进另一个躯壳。我的身体越来越冷,
嘴唇开始发紫,连呼吸都带着冰碴子。就在这时,
主卧方向传来舒晚一声刻意拔高的、娇弱的咳嗽。就这一声。
戚泊君立刻伸手按住了那个准备收手的老头,眼神决绝:「不够,再加倍。」
老头吓得满头大汗:「戚总!再这样下去,夫人……夫人会死的!」
戚泊君的身体僵硬了片刻。只有两秒。然后,我听到了我这辈子听过的,最残忍的一句话。
「晚晚怀的是我戚家的未来。一切,以孕妇为重。」「可是……」这一次,
我主动打断了那个还想劝说的老头。「继续。」我的声音轻飘飘的,却无比清晰,「渡完了,
我就能走了。」戚泊君那张冰封的脸上,终于出现了一丝裂痕,他死死地盯着我,
像是不认识我一般。他似乎想问,岑漾,你闹够了没有?难道真要为这点“小事”,
跟我决裂?可就在他开口的前一秒,
舒晚又在外面柔柔地唤了一声:「泊君哥哥……我有点怕。」这一声,像一个无形的钩子,
瞬间就把他的魂勾走了。他最后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但终究还是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去。
密室的门,在我眼前缓缓合上,隔绝了最后的光明。再醒来时,
我躺在疗养院纯白色的病床上,入眼便是戚泊君坐在床边,处理着文件的侧脸。
他察觉到我醒了,我们四目相对,沉默了足足一分钟。最后,
他面无表情地端起一碗温热的粥,用勺子舀起,递到我嘴边。我却偏了偏头,躲开了。
「我自己来。」他看着我机械地、毫无滋味地喝了半碗粥,
终于忍不住开口:「还有哪里不舒服?」我没回答,
只是平静地提出我的要求:「把我的手机给我。」我的语气太平静,太疏离了。
戚泊君愣了好几秒,才像是回过神来,吩咐管家把我的手机送了过来。
他瞥见屏幕上几十个未接来电,冷不丁地问了一句:「谁打来的?」过去的他,
从来不会问这些。我眼底划过一丝几乎无法察觉的厌恶,声音像结了冰:「你不认识的人。」
这个回答显然**到了他。戚泊君解开衬衫最顶端的扣子,露出一截锁骨,
带着一股压迫感俯视着我:「岑漾,你这大**脾气,打算发到什么时候?我给了你台阶,
你就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以前他只要露出这种表情,我一定会吓得立刻检讨自己,
想尽办法安抚他。可现在,我只是指了指他口袋里正在震动的手机,
陈述一个事实:「你的『福星』找你。」“福死”两个字,我说得极重。
戚泊君脸上的怒气一滞,随即转换成一抹讥诮的笑。他习惯性地转身,
走到走廊里去接那个电话,把所有的温柔和耐心都给了另一个女人。他刚一走,
我的手机就响了。看到那个号码,我立刻接通。「清清!说好了落地就来找我,
你是不是后悔了?」电话那头的声音急得快要破音。「没有后悔。」
我抚着todavía隐隐作痛的心口,嘴角却不由自主地上扬,
「只是……出了点小意外。」「意外?你怎么了?你等着,我现在就订票回国……」
我轻笑着打断了他的话,眼底是我自己都没察觉到的柔光:「别急,阿澈。再给我五天,
就五天。」等戚泊君挂了电话,冷着脸走回病房时,
正好看到我还没来得及收起的、那抹发自内心的笑意。那笑容太刺眼了,
他已经很多年没在我脸上见过了。一股莫名的烦躁,像野草一样从他心底疯长出来。
但他刚刚答应了舒晚,要马上回去给她和孩子讲睡前故事。于是,
他也只能暂时压下心头那点莫名的火气,拿起公文包,头也不回地丢下一句:「公司有事,
我过几天再来看你。」他没想过问我,电话是谁打来的。在他眼里,我岑漾的朋友圈,
除了几个早就被他隔绝了的女性亲戚,还能有谁?或许是哪个想巴结戚家,
来讨好我的远房表妹吧。他这么想。4他口中的“过几天”,变成了永远。之后整整一周,
戚泊君都没有再出现。但我那些所谓的“朋友”,却争先恐后地给我发来他的动态。
他在私人酒会上,当着所有人的面,宣布舒晚是他此生唯一的挚爱。他包下整个私人岛屿,
只为陪舒晚看一场流星雨。他在朋友圈里发了一张九宫格。落日余晖下,
他将一枚硕大的钻戒,戴在舒晚的手上,两人在镜头前深情拥吻。配文是:【往后余生,
请多指教,我的戚太太。】下面一堆京圈太子爷们的起哄,有人艾特我,
问我这个正牌的戚太太什么时候滚蛋。我躺在病床上,
面无表情地在那条朋友圈下评论:【新婚快乐,百年好合。】不到五分钟,
戚泊君的电话就追了过来。我没接,直接拉黑。半小时后,我独自办完了出院手续。
讽刺的是,我在妇产科的VIP候诊区门口,又撞见了他们。
一个小护士满眼羡慕地对舒晚说:「戚太太,你先生对你可真好。每次产检都亲自陪着,
做B超前,怕那个凝胶太凉,都非要先在手心里焐热了才让我们用。」
周围等待的孕妇们纷纷投来羡慕的目光。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平坦的小腹。这里,
曾经也有一个孩子的。在我被锁在雪地里,绝望地发着高烧时,我拼命给他打视频电话,
乞求他回来救我。视频接通了,镜头里出现的却是舒晚裹着浴巾,一脸无辜的脸。「岑夫人?
泊君刚刚输了游戏,现在正被我罚不许穿衣服呢。你找他……有急事吗?」
我什么都说不出来,直接挂断。一分钟后,戚泊君的电话打了回来。背景音里,
是舒晚委屈的抽泣声。而他,像一头被激怒的野兽,
对着电话那头的我破口大骂:「你这种连自己的孩子都保不住的**,活着还有什么用!
岑漾,你怎么不干脆死在外面算了!」是的,他让我去死。我收回思、我深吸一口氣,
剛準備轉身從另一條路離開,戚泊君冰冷的聲音就砸了過來。「站那儿装死给谁看?」
我垂下眼,甚至懒得解释,只是本能地重复着那三个字:「对不起,打扰了。」「等等。」
他皱着眉喊住我。旁边的舒晚,立刻敏锐地察觉到了什么,眼中掠过一丝嫉妒。
她收紧挽着戚泊君手臂的手,脸上堆起完美的、无懈可击的笑容:「姐姐,你别走呀。
我都还没好好谢谢你呢!要不是你帮忙,我和宝宝现在肯定还在难受呢。泊君哥哥,
我们就让姐姐跟我们一起回家吧,好不好嘛?」戚泊君宠溺地刮了一下她的鼻子,
声音腻得让我反胃:「都听我们家小善人的。」我正准备回去收拾最后的证件,没有拒绝。
宽敞的劳斯莱斯后座,空间大得足够我们三人隔开楚河汉界。如舒晚所愿,我一上车,
就看到座椅夹缝里,一枚眼熟的、属于男人的袖扣。只是上面,缠着几根不属于我的长发。
舒晚立刻故作惊讶地尖叫起来:「哎呀!泊君哥哥,你怎么把这个都弄丢在这里啦?
人家找了好久的!」她说着,就钻进戚泊君怀里,用小拳头娇嗔地捶着他的胸口。
戚泊君一边笑着道歉,说都是他的错,一边用眼角的余光,不动声色地观察我的反应。
他失望了。我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连眉毛都没动一下。我只是专心地看着我的手机,
好像上面有什么天大的生意。那种让他心烦意乱的烦躁感,又一次毫无征兆地袭来。「岑漾。
」他语气不善,「从上车到现在,你就没抬过头,在跟谁发信息?你的那个神秘表妹?」
我刚刚订好了飞往苏黎世的头等舱机票,闻言,平静地按灭了屏幕。「看新闻。」这三个字,
像是点燃了**的引信。他眉宇间的不悦,瞬间变成了暴怒。趁我不备,一把抢过我的手机,
沉声质问:「密码。」「戚总的生日。」我说。结婚七年,这么简单的六位数字,
他输了三次,直到手机屏幕显示一分钟后再试,他都没能解开。他不知道,我的手机密码,
早就换成了我那个死去的孩子的预产期。一个他永远也不会记得的日子。车内死一样的寂静,
一直维持到别墅。车一停稳,戚泊君就小心翼翼地把有些孕反的舒晚扶下车,亲自送回主卧,
然后吩咐厨房做她最爱吃的燕窝粥。他下楼时,正好看到我拖着空行李箱,
走向西跨院那个如同鬼屋般的背影。鬼使神差的,他对厨房说:「给……给夫人也准备一份,
晚饭摆三副碗筷。」5西跨院里,常年不见阳光,阴冷潮湿。我打开我的行李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