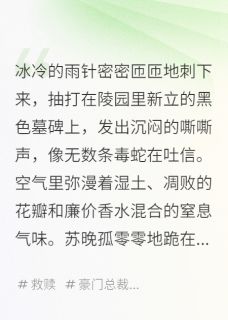
冰冷的雨针密密匝匝地刺下来,抽打在陵园里新立的黑色墓碑上,发出沉闷的嘶嘶声,
像无数条毒蛇在吐信。空气里弥漫着湿土、凋败的花瓣和廉价香水混合的窒息气味。
苏晚孤零零地跪在母亲墓碑前的泥水里,昂贵的黑色裙摆早已吸饱了泥浆,
沉甸甸地贴在腿上,寒意直往骨头缝里钻。“晚晚啊,你妈妈走得太突然了,
真是…真是让人心都碎了!”继母赵美娟尖锐的哭嚎声穿透雨幕,刺得人耳膜生疼。
她手里死死攥着一方雪白的手帕,夸张地按在干涩的眼角,
精心描绘的眼线被雨水和假惺惺的泪水洇开,在脸上拖出两道滑稽又肮脏的黑痕。
苏晚没有抬头,视线固执地胶着在墓碑照片上母亲温柔含笑的眉眼,
那笑容凝固在冰冷的石头上,无声地诉说着无尽的冤屈和未尽的嘱托。“姐姐,节哀顺变啊。
”妹妹苏莹娇滴滴的声音响起,带着一种刻意拿捏的、令人作呕的甜腻。
她穿着一身裁剪合体的黑色小洋装,外面罩着价格不菲的羊绒大衣,
在几个塑料姐妹的簇拥下款款走近,雨水似乎都识趣地避开了她。她弯下腰,
涂着鲜红蔻丹的手指“啪”的一声,
将一份薄薄的、被雨水打得半透明的文件拍在苏晚面前湿漉漉的青石板上。“喏,
这是律师刚送来的,妈妈生前签的股权**协议和遗嘱公证书,”苏莹的声音陡然拔高,
带着毫不掩饰的恶意和胜利者的轻蔑,清晰地穿透雨声,“看清楚了,白纸黑字,
苏氏集团所有的股份,还有家里的房子、车、存款,全都是我和我妈的!跟你苏晚,
一分钱关系都没有!”那份文件像一片肮脏的落叶,被雨水迅速打湿、泡软,
墨迹开始晕染模糊。苏晚的呼吸猛地一窒,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狠狠攥住,
尖锐的疼痛瞬间蔓延至四肢百骸。她认得那份文件的格式,那是母亲生前请律师草拟的初稿,
上面甚至还有母亲娟秀的字迹做的几处备注!母亲当时拉着她的手,
眼中是殷切的期望:“晚晚,妈身体不好,这些……以后都是你的倚仗……”“不可能!
”苏晚猛地抬起头,雨水瞬间模糊了她的视线,她胡乱抹了一把脸,
声音嘶哑却带着一股玉石俱焚的决绝,“我妈绝不可能签这种东西!是你们伪造的!
”她挣扎着想要站起来,膝盖却被冰冷的泥水冻得麻木。“伪造?”赵美娟的哭声戛然而止,
脸上瞬间换上一副刻毒的冷笑。她猛地弯腰,
苏晚手中那份被雨水打湿的文件——那是母亲真正留给她的、委托私人律师保管的遗嘱副本。
苏晚甚至没来得及反应,只听“嗤啦——嗤啦——”几声刺耳的裂帛之音,
赵美娟肥胖的手指粗暴地将那几页薄纸撕成了碎片!雪白的纸屑混着肮脏的泥水,
被赵美娟狠狠一扬手,劈头盖脸地砸在苏晚脸上。“不识抬举的东西!
”赵美娟的声音淬了毒,“你妈就是个短命鬼!她留下的?她留下个屁!这苏家的一切,
现在是我赵美娟说了算!你算个什么东西?丧家犬一条!”纸屑粘在苏晚冰冷的脸上,
又被雨水冲刷下来,像一场肮脏的雪。她浑身剧烈地颤抖着,不是因为冷,
而是因为那几乎要冲破胸膛的、焚毁一切的恨意。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嫩肉里,
尖锐的疼痛却压不住那股灭顶的绝望和愤怒。“好了妈,跟这种人废什么话。
”苏莹不耐烦地撇撇嘴,挽住旁边一个西装革履男人的手臂,声音腻得发嗲,“亲爱的,
我们走吧,这里的空气都被某些垃圾熏臭了。”她**似的将头靠在男人肩上,那个男人,
正是苏晚相恋三年、原本约定等她母亲病情稳定就结婚的男友——林哲。林哲的眼神躲闪,
不敢与苏晚通红的、燃烧着火焰的眼睛对视,只是低声对苏莹说:“莹莹,少说两句吧,
毕竟……”他试图打圆场,却被苏莹狠狠掐了一下胳膊。“毕竟什么?毕竟她是你前女友?
”苏莹嗤笑一声,刻薄的目光刀子一样剐向苏晚,“林哲,你可得擦亮眼睛,
别什么垃圾都往回捡!她苏晚现在连垃圾都不如,就是个欠了一**债的扫把星!你问问她,
她妈那破公司欠银行的几千万到期了吗?拿什么还?卖身吗?
哈哈……”刺耳的笑声像淬了毒的针,密密麻麻扎进苏晚的耳朵里。
林哲脸上最后一丝尴尬也消失了,只剩下急于撇清的冷漠和一丝不易察觉的鄙夷。
他搂紧了苏莹,几乎是半强迫地带着她,和那群看客一起,转身离开。
皮鞋踩在湿漉漉的青石板路上,发出空洞的、渐行渐远的嗒嗒声,
将苏晚彻底遗弃在这冰冷的墓园中心。雨下得更大了,砸在脸上生疼。
世界只剩下哗哗的雨声和墓碑上母亲那永恒不变的、温柔到令人心碎的笑容。
苏晚像一尊被抽走了灵魂的石像,在母亲墓碑前不知跪了多久。冰冷的雨水早已浸透骨髓,
每一寸皮肤都麻木得失去了知觉,唯有胸腔里那颗心,被仇恨的毒液反复浸泡,
灼烧般地痛着。赵美娟撕碎的纸屑混在泥水里,被踩踏得面目全非,如同她此刻的人生。
直到天色彻底黑透,陵园的管理员提着昏黄的手电筒,远远地催促:“要关门了,赶紧走吧!
”那声音带着一丝不耐烦,穿透冰冷的雨幕。苏晚才猛地一个激灵,
僵硬的手指撑着湿滑冰冷的墓碑,用尽全身力气,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膝盖像灌满了锈蚀的铅,每一步都沉重得如同拖拽着千钧巨石。
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那片埋葬了至亲也埋葬了她所有希望的墓园的。
城市的霓虹在雨帘后扭曲、晕染开,变成一片片模糊而冰冷的光斑。
她身上那件价值不菲、如今却沾满污泥的黑色丧裙,紧紧贴在身上,
勾勒出单薄而狼狈的轮廓。昂贵的面料吸饱了雨水,变得沉重冰冷,像一层裹尸布。
雨水顺着她散乱的发梢,沿着苍白的脸颊不断滚落,分不清是雨还是泪。
她漫无目的地在雨夜里踉跄前行,只想离那个地方越远越好。不知走了多久,
拐进一条狭窄、幽深的后巷。巷子两旁是高耸的、沉默的旧楼,
像两堵巨大的、湿漉漉的黑色墙壁。巷子里弥漫着一股垃圾在雨天发酵的酸腐气味,
混杂着劣质烟草和尿骚味。昏暗的路灯被厚厚的雨雾包裹着,只能投下几团模糊昏黄的光晕,
勉强照亮脚下坑洼不平、积水横流的水泥地。突然,几道刺眼的强光猛地从巷口方向射来,
像几只凶兽的眼睛,瞬间撕裂了巷道的昏暗,将苏晚纤瘦的身影牢牢钉在湿漉漉的墙壁上。
刺目的光线让她下意识地抬手遮住眼睛。“哟,这不是苏大**吗?真让我们好找啊!
”一个流里流气的声音响起,带着毫不掩饰的恶意和贪婪。苏晚的心猛地一沉,
透过指缝和刺目的光柱,看清了来人。三个男人,为首的是个光头,
脖子上挂着粗俗的金链子,即使在昏暗的光线下也闪着油腻的光。他咧着嘴,
露出一口被烟熏得焦黄的牙齿。旁边两个,一个瘦得像竹竿,眼神阴鸷,另一个矮壮敦实,
手里把玩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弹簧刀。是“虎哥”的人。母亲的公司濒临破产时,
赵美娟不知从哪里引来了这家臭名昭著的高利贷公司,签下了巨额短期债务合同。
合同陷阱重重,利息高得离谱,母亲病重昏迷期间,这笔债务就像滚雪球一样,
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足以将她彻底压垮的天文数字。而赵美娟,
显然早就“忘了”这笔债的存在,或者说,是故意让它成为压垮苏晚的最后一根稻草。
“怎么?苏大**贵人多忘事?你家那破公司欠我们虎哥的钱,今天可是最后期限了!
”光头男一步步逼近,脸上横肉抖动,唾沫星子几乎喷到苏晚脸上,带着浓重的烟臭和口臭,
“连本带利,两千三百八十万!一分都不能少!”巨大的绝望如同冰冷的潮水,
瞬间将苏晚淹没。两千三百八十万!别说现在身无分文,就是母亲的公司还在她手里,
也未必能立刻拿出这么多现金!赵美娟!苏莹!这两个名字在她心中疯狂燃烧,
带来噬骨的恨意。“钱……钱在赵美娟手里……”苏晚的声音嘶哑干涩,如同砂纸摩擦,
“公司现在是她……”“放**屁!”光头男粗暴地打断她,
猛地一把揪住苏晚湿透的衣领,巨大的力量勒得她几乎窒息,双脚离地,“虎哥说了,
合同上签的是你那个死鬼妈的名字!现在她死了,父债子偿,天经地义!就找你!”“老大,
跟这娘们废什么话!”旁边那个瘦高个不耐烦地舔了舔嘴唇,
眼神淫邪地在苏晚被雨水勾勒出的曲线上逡巡,“看她这细皮嫩肉的,
苏家大**呢……嘿嘿,就算还不上钱,拉去‘夜色’坐台,也能给虎哥回点本不是?
听说以前还是林大少爷的女人?肯定值钱!”“就是就是!”矮壮的那个挥舞着弹簧刀,
刀锋在昏黄的灯光下划出森冷的弧线,发出“咔哒”的脆响,贪婪的目光像湿滑的蛇信,
“先让哥几个验验货也行啊!这脸蛋,
这身段……”污言秽语伴随着令人作呕的笑声在狭窄的巷子里回荡。恐惧像冰冷的藤蔓,
瞬间缠紧了苏晚的心脏,让她四肢冰凉。但比恐惧更汹涌的,是滔天的屈辱和恨意!她苏晚,
母亲捧在手心的明珠,何曾受过这等折辱?赵美娟!苏莹!是你们把我逼到如此绝境!
“滚开!”苏晚爆发出被逼到绝境的尖利嘶吼,用尽全身力气猛地挣扎,
指甲狠狠抓向光头男的脸颊。“操!给脸不要脸!”光头男猝不及防,脸上**辣一痛,
瞬间暴怒。他狠狠将苏晚掼在冰冷湿滑的墙壁上,粗糙的砖石棱角重重硌在她的背脊,
剧痛让她眼前发黑,闷哼一声。“臭**!敢挠老子!”光头男啐了一口,
扬手就是一个凶狠的耳光扇了过来!带着风声!苏晚下意识地闭紧双眼,
绝望地等待着那即将到来的剧痛和更深的羞辱。然而——预想中的重击并未落下。
时间仿佛凝固了一瞬。只有雨水砸落的哗哗声,以及光头男同伴倒抽一口冷气的声音。
苏晚颤抖着睁开眼。一只骨节分明、修长有力的大手,稳稳地、如同铁钳般,
在半空中扣住了光头男粗壮的手腕。那只手异常干净,指甲修剪得整齐圆润,腕骨突出,
戴着一块低调却价值不菲的铂金腕表,表盘反射着巷口方向射来的、更加明亮的车灯光晕,
泛着冰冷的光泽。与光头男那布满刺青和粗毛的手臂形成了极其强烈的、令人心悸的对比。
光头男脸上暴怒的横肉瞬间僵住,随即转为惊愕和难以置信。他使劲挣了挣,
那只看起来并不十分强壮的手却纹丝不动,反而如同精钢浇筑,越收越紧。
光头男甚至能听到自己腕骨在对方指下不堪重负发出的轻微“咯咯”声,
剧痛让他额头瞬间冒出冷汗。“谁……谁他妈多管闲事?!”光头男又惊又怒,
色厉内荏地吼着,目光顺着那只手向上看去。苏晚的目光也顺着那只救赎般的手向上移动。
巷口,不知何时悄无声息地停着一辆线条冷硬流畅的黑色迈巴赫。
车灯如同两只威严的巨兽之瞳,将狭窄巷道的黑暗彻底驱散。车门旁,站着一个男人。
他身形极高,穿着剪裁完美、一丝不苟的纯黑色手工西装,肩线挺括。
外面随意地披着一件同样质感的黑色羊绒大衣,敞开着。雨水落在他肩头、发梢,
却奇异地无法浸染那份迫人的冷峻。他的脸大半隐在迈巴赫投射出的浓重阴影里,
只能看到线条锋利如刻的下颌,和紧抿的、薄而冷的唇线。周身散发出的气息,
比这冰冷的雨夜更加凛冽,如同出鞘的绝世名剑,带着无形的、令人窒息的威压。
仅仅是站在那里,就仿佛将整条肮脏的后巷都冻结了。他身后的阴影里,
无声地立着两个同样穿着黑色西装的魁梧男人,如同两座沉默的山岳,目光锐利如鹰隼,
牢牢锁定了光头男三人。“陆……陆先生?!”光头男在看清阴影中男人轮廓的瞬间,
脸上的血色“唰”地一下褪得干干净净,惊骇得连声音都变了调,带着无法抑制的颤抖。
他认出了眼前的人——陆沉舟!
那个在商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名字本身就代表着规则和生杀予夺的男人!虎哥在他面前,
连提鞋都不配!“虎哥?”陆沉舟开口了。声音低沉平缓,没有丝毫起伏,
却像冰锥一样刺入骨髓,带着一种天然的上位者威压。他甚至没有看光头男一眼,
目光穿透雨幕,落在了狼狈不堪、如同风中残烛般贴在墙上的苏晚身上。那目光深邃、冰冷,
却又带着一种审视猎物的、奇异的穿透力。“是…是是!小的王虎,给陆先生请安!
”光头男——王虎,吓得魂飞魄散,腰瞬间弯成了九十度,被陆沉舟扣住的手腕还在剧痛,
他却连哼都不敢哼一声。“她欠你们的钱?”陆沉舟的视线终于从苏晚身上移开,
极其淡漠地扫了王虎一眼。“是…是的陆先生!两千三百八十万!她妈签的合同,
今天到期……”王虎语无伦次,豆大的汗珠混着雨水从光头上滚落。“合同。
”陆沉舟只说了两个字,毫无情绪,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王虎浑身一哆嗦,
哪里还敢有半点犹豫,连忙用那只自由的手,哆哆嗦嗦地从怀里掏出一个防水文件袋,
从里面抽出一份折叠的合同,双手捧着,恭恭敬敬地递到陆沉舟面前,姿态卑微到了尘埃里。
陆沉舟终于松开了钳制王虎手腕的手。他动作优雅地从西装内袋里取出一方雪白的手帕,
慢条斯理地擦拭着刚才扣住王虎的那只手,仿佛碰触了什么极其肮脏的东西。擦完后,
随手将那方价值不菲的手帕丢进了旁边肮脏的积水里。然后,他才用两根手指,
夹起了那份被雨水打湿了些许的合同。他甚至没有翻开细看,
目光只是在那签名处——苏晚母亲的名字上停顿了一瞬。随即,他另一只手伸进大衣口袋,
再拿出时,指间赫然夹着一支通体漆黑、镶嵌着幽蓝碎钻的钢笔。“陆先生!
您这是……”王虎惊疑不定,心中涌起强烈的不安。陆沉舟没有理会他。他拿着笔,
在合同金额“23,800,000.00”那一长串冰冷的数字上,
极其随意地划了两道线。动作漫不经心,却带着一种掌控一切的漠然。接着,
他在旁边空白处,用那支蓝钻钢笔,签下了一个龙飞凤舞的名字——陆沉舟。字迹遒劲有力,
力透纸背。签完,他将那份被改动的合同,像丢垃圾一样,随意地抛回给呆若木鸡的王虎。
“现在,她的债主是我。”陆沉舟的声音依旧毫无波澜,却如同惊雷在王虎耳边炸响,
“带着你的人,滚。三秒。”“是是是!谢谢陆先生!谢谢陆先生!我们这就滚!这就滚!
”王虎如蒙大赦,哪里还敢有半点迟疑,连滚带爬地捡起地上的合同,
也顾不上招呼那两个同样吓得腿软的同伴,连滚带爬地朝着巷口冲去,生怕慢了一秒。
那两个手下也屁滚尿流地跟上,转眼就消失在雨幕和巷口的车灯光晕之外。狭窄的后巷里,
瞬间只剩下哗哗的雨声,迈巴赫沉稳的引擎低鸣,以及……狼狈靠在墙上的苏晚,
和站在几步之外、如同神祇般降临的陆沉舟。冰冷的雨水顺着苏晚的额发、脸颊不断滑落,
流进眼睛里,带来一阵刺痛。她浑身控制不住地颤抖着,牙齿咯咯作响,
一半是因为刺骨的寒冷,一半是劫后余生的巨大冲击和后怕。
她看着那个刚刚如同碾碎蝼蚁般处理了王虎的男人,一步一步,踩着巷子里浑浊的积水,
沉稳地朝自己走来。昂贵的手工皮鞋踏在水洼里,发出清晰而规律的声响,
每一步都像踩在苏晚紧绷到极致的心弦上。他高大的身影完全笼罩了她,
带来更深的阴影和更强烈的压迫感。雨水打湿了他额前几缕黑发,贴在冷峻的眉骨上,
更添几分凌厉。那双深邃如寒潭的眼睛,
此刻清晰地映出她苍白如鬼、沾满污泥、瑟瑟发抖的倒影,像审视一件摔碎的瓷器。
苏晚下意识地想后退,背脊却死死抵着冰冷粗糙的砖墙,退无可退。她张了张嘴,
喉咙里却像堵着一团浸了水的棉花,发不出任何声音。
只有惊悸的喘息声在两人之间微不可闻。陆沉舟在她面前一步之遥停下。他微微俯身,
距离骤然拉近。苏晚能闻到他身上一种极其清冽、冷肃的气息,像是初雪后的松林,
又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清苦的薄荷味,奇异地穿透了巷子里污浊的空气和雨水的湿腥,
钻入她的鼻息。这气息带着一种强大的、不容置疑的力量感,
让混乱惊惶的苏晚莫名地感到一丝诡异的安定。他没有说话。
目光从她惊恐未定的脸上缓缓下移,落在了她垂在身侧、紧紧握成拳头的右手上。
白皙的手背上,几道新鲜的、被粗糙砖石划破的血痕异常刺眼,混合着泥水和雨水,
正缓缓渗出细小的血珠。更触目惊心的是,她紧握的拳心里,
似乎也渗出了暗红的血——那是她之前在母亲墓前,用指甲生生掐破掌心留下的伤口,
此刻在刚才的挣扎中再次撕裂。陆沉舟的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
快得几乎让人以为是错觉。他再次伸出手,动作却与刚才扣住王虎时的雷霆万钧截然不同。
他的手指修长、稳定、干燥,带着一种近乎冷漠的精准,
轻轻握住了苏晚冰冷、沾满泥污和血水的手腕。苏晚猛地一颤,如同被电流击中,
下意识地想抽回手。但他的力道看似不重,却带着一种不容抗拒的坚定。“别动。
”他低声说,声音依旧低沉平缓,却像带着某种奇特的魔力,让苏晚紧绷的身体僵住。
他另一只手从西装裤袋里,又拿出了一方新的、雪白得没有一丝杂质的手帕。他垂着眼,
动作异常专注,用那方干净到极致的手帕,极其轻柔、极其仔细地,
一点点擦拭掉苏晚手背上和掌心里那些混着污泥的血污。他的动作带着一种近乎苛刻的细致,
仿佛在修复一件稀世珍宝上沾染的尘埃,又带着一种冰冷的、程序化的精确。
冰凉的丝质手帕擦过**辣的伤口,带来一丝细微的刺痛,
但更多的是一种奇异的、被珍重对待的错觉。苏晚怔怔地看着他低垂的眉眼,
浓密的睫毛在眼睑下投下一小片阴影,侧脸的线条冷硬如雕塑。
巷口车灯的光晕勾勒出他完美的轮廓,雨水顺着他冷峻的下颌线滑落。他离得这样近,
近到她能看清他皮肤上极细微的纹理,
能感受到他指尖透过薄薄手帕传来的、稳定而微凉的体温。这感觉太过荒谬。
一个陌生、强大、冷得像冰的男人,在一条肮脏污秽的后巷里,
为一个刚刚被高利贷逼到绝境的陌生女人,擦拭手上的血污。时间仿佛被拉长,
雨声、城市的喧嚣都成了模糊的背景音。只有手腕上那微凉而稳定的触感,
和他身上那股清冽冷肃的气息,无比清晰地烙印在苏晚的感官里。终于,他停下了动作。
原本雪白的手帕已经沾满了污泥和暗红的血渍,变得肮脏不堪。他随手将其丢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