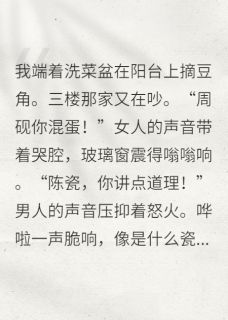
我端着洗菜盆在阳台上摘豆角。三楼那家又在吵。“周砚你**!”女人的声音带着哭腔,
玻璃窗震得嗡嗡响。“陈瓷,你讲点道理!”男人的声音压抑着怒火。哗啦一声脆响,
像是什么瓷器砸在地板上。对门李婶的脑袋从隔壁阳台探出来,朝我撇撇嘴:“又开始了。
这小陈,看着温温柔柔,脾气可真不小。周先生多好的人,有钱,模样又周正。
”我嗯了一声,没接话。好不好的,外人哪知道。豆角在我手里掰成整齐的小段。
争吵声低了下去,变成一种令人窒息的沉默。过了一会儿,沉重的脚步声咚咚咚下楼,
汽车引擎暴躁地吼叫着开走了。第二天,陈瓷就不见了。听楼下小超市的王姨说,
天没亮就拖着个大箱子走的,眼睛肿得像桃子。周砚的车在楼下停了两天,他上去过几次,
下来时脸色一次比一次沉。后来,那扇门再也没开过。时间像小区门口那棵老槐树掉叶子,
一茬一茬,无声无息。五年。我在菜市场门口的小摊上挑土豆。“妈妈!你看!
”一个脆生生的童音,像清晨刚沾了露水的嫩黄瓜。我下意识抬头。几步开外,
一个穿着洗得有点发白的鹅黄色小裙子的女孩,正踮着脚,
努力去够旁边水果摊上一个红彤彤的大苹果。小脸圆嘟嘟,扎着两个歪歪扭扭的小揪揪,
眼睛又大又亮,像浸在水里的黑葡萄。“贝贝,别乱动。”一只手及时拉住了小女孩,
声音温软,带着点疲惫。我手里的土豆差点掉地上。是陈瓷。她瘦了很多,
脸颊微微凹陷下去,穿着简单的T恤牛仔裤,背着一个很大的帆布包,里面鼓鼓囊囊,
像是塞满了东西。眉眼间那股子曾经被娇养出来的矜贵气没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生活磋磨过的韧劲,像河滩上被打磨过的石头。她没看见我,
正低头从帆布包侧袋里掏出一个洗得发白的小钱包,仔细数着里面的零钱给水果摊老板。
“老板,苹果……能便宜点吗?孩子想吃。”老板是个胖胖的中年女人,瞥了一眼陈瓷,
又看看眼巴巴望着苹果的小女孩贝贝,叹了口气:“行吧行吧,看你带孩子不容易,
给你挑个小的。”陈瓷连忙道谢,
小心翼翼地把那个小了一圈的苹果放进自己拎着的环保袋里,牵起贝贝的手:“走,贝贝,
回家妈妈给你削。”“妈妈,大的好看。”贝贝小声嘟囔,
一步三回头地看着摊子上那些又大又红的苹果。陈瓷没说话,只是更紧地握住了女儿的小手,
快步离开了人群。我看着她们母女俩消失在菜市场的人流里,心里有点不是滋味。
当年那个在阳台上砸东西、声音尖利的陈瓷,和眼前这个为了一颗苹果讨价还价的单亲妈妈,
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日子照旧。只是我偶尔会在小区里,
或者附近的街口碰到陈瓷和贝贝。陈瓷总是很忙。有时候看她急匆匆地赶公交,
手里还抱着厚厚的文件夹;有时候很晚才回来,贝贝趴在她背上睡得小脸红扑扑。
她在一个很小的广告公司做设计,听说接很多私活。贝贝很乖,不像一般孩子那么闹腾。
陈瓷忙的时候,她就自己坐在小马扎上画画,安安静静的。那孩子有双特别干净的眼睛,
看人的时候,让你觉得心里都亮堂了。一次下大雨,我下班回来,
在楼道口看见陈瓷浑身湿透地站在那儿,对着单元门禁按键,急得团团转,
帆布包紧紧护在怀里。贝贝被她用外套裹着,只露出个小脑袋。“怎么了?”我走过去。
陈瓷看到我,像看到救星:“李姐!我钥匙……钥匙好像落公司了!门禁卡也在里面!
”雨水顺着她的头发往下淌,狼狈不堪。“先进来吧。”我刷开单元门。“谢谢!谢谢李姐!
”她连声道谢,抱着贝贝跟我进了电梯。到了我家门口,
她犹豫着不肯进:“太麻烦你了李姐,我们身上都是水……”“湿衣服穿着要生病的,
进来吧。”我打开门。陈瓷这才抱着贝贝进来,拘谨地站在玄关,不敢乱动。
贝贝从我怀里探出头,大眼睛好奇地打量着我的屋子。我找了干毛巾给她们,又倒了热水。
陈瓷用毛巾小心地给贝贝擦头发,自己的湿衣服还在往下滴水。
“贝贝爸爸……”我犹豫了一下,还是问了。这情况,孩子爸总该管管吧?
陈瓷擦头发的手顿了一下,声音很轻:“他不知道贝贝的存在。”我愣住了。
“当年走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有了。”她低着头,看着怀里乖巧的女儿,眼神复杂,
“后来知道了……也不想回去找他。我们分开,闹得很难看。”她没细说,我也不好多问。
那天,陈瓷借用我的电话联系了开锁公司。等锁匠来的时间里,贝贝坐在我的小沙发上,
安安静静地吃着我给她的饼干。陈瓷抱着那个始终不离身的帆布包,靠在墙边,
疲惫地闭着眼。“李阿姨,”贝贝突然小声叫我,
小手从她那个小小的、印着卡通图案的挎包里掏啊掏,
掏出一个亮晶晶的、指甲盖大小的小东西,“送给你。谢谢饼干。”她摊开小手。
我凑近一看,是一颗小小的、水钻一样的装饰扣?看着像从什么衣服上掉下来的,
切割面在灯光下折射出细碎的光。“呀,贝贝,这哪来的?”陈瓷睁开眼,有些惊讶。
“地上捡的,亮晶晶,好看。”贝贝奶声奶气地说。“不好意思啊李姐,孩子乱捡东西。
”陈瓷有点窘。“没事没事,孩子喜欢亮晶晶的东西很正常。”我笑着接过那颗小水钻扣,
随手放在茶几上,“贝贝真乖。”开锁师傅来了,修好了门。陈瓷再三道谢,
抱着贝贝回去了。那颗小水钻扣就留在了我的茶几角落。又过了些日子,
小区里突然热闹起来。好几辆看着就很贵的黑色轿车停在楼下,
下来几个穿着西装、气场很强的人。为首那个男人,个子很高,穿着剪裁合身的深灰色西装,
侧脸线条冷硬。他一下车,抬头看向陈瓷住的那栋楼,眉头紧锁。是周砚。五年不见,
他身上的气势更沉了,像块吸满了寒气的墨玉。我心里咯噔一下。他找来了?果然,没多久,
争吵声隐隐约约从三楼传下来。比五年前那次更压抑,更激烈。听不清具体内容,
只偶尔捕捉到“孩子”、“骗”、“负责”几个尖锐的词。楼下的黑车旁,
那几个西装革履的安保人员(用户要求,避免警察等词汇)站得笔直,面无表情。
陈瓷的哭声断断续续传来,带着绝望。还有贝贝害怕的抽泣声。邻居们探头探脑,议论纷纷。
“啧,找上门了?我就说嘛,孩子哪能没爹……”“看着不像善茬啊,小陈这下麻烦了。
”“那孩子可怜哦……”我站在阳台,心里揪着。周砚这架势,看着就不像是来好好谈的。
争吵持续了快一个小时。砰的一声巨响,像是门被狠狠甩上。周砚沉着脸从楼道里出来,
脸色铁青,薄唇抿成一条冰冷的直线。他径直走向车子,安保人员立刻替他拉开车门。
就在他要弯腰坐进去的瞬间——“妈妈!妈妈!我的小兔子!
”贝贝带着哭腔的喊声从楼道里冲出来。一个小小的、鹅黄色的身影跟着跑了出来,
怀里紧紧抱着一个破旧的毛绒兔子玩偶。她大概是追着妈妈跑出来的,没看清路,
小短腿一绊,整个人朝着单元门口的水泥台阶就扑了下去!“贝贝!
”陈瓷撕心裂肺的尖叫从后面传来。周砚的动作猛地顿住,几乎是本能地转身,
一个箭步冲过去。他速度极快,在贝贝的小脑袋即将磕到坚硬台阶边缘的前一瞬,长臂一伸,
稳稳地捞住了那个小小的身体。巨大的惯性让他也踉跄了一下,但他立刻抱紧了孩子,
护在怀里。空气瞬间凝固。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贝贝显然吓坏了,小脸煞白,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死死抱着她的小兔子,惊恐地看着这个突然抱住她的陌生高大男人。
周砚低头看着怀里的孩子。那张小脸,眉眼像陈瓷,柔和温婉。可那挺直的小鼻梁,
紧抿的、显得有些倔强的嘴唇,
瞪得圆圆的、像受惊小鹿般的眼睛深处透出的一点点强撑的勇敢……活脱脱就是缩小版的他。
他脸上的冰霜,像被投入滚水的坚冰,瞬间裂开一道缝隙。那是一种极其复杂的震动,
混杂着难以置信、茫然、还有一丝猝不及防的、源自血脉深处的悸动。他抱着孩子的手臂,
不自觉地收紧了些,似乎想确认这不是幻觉。陈瓷跌跌撞撞地冲下楼,看到这一幕,
猛地停住脚步,捂住嘴,眼泪汹涌而出。“放开我女儿!”她冲过去,想把贝贝抢回来,
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周砚抱着贝贝,没松手,也没看陈瓷,他的目光牢牢锁在贝贝脸上,
声音低沉得有些沙哑:“……她叫什么名字?”“周砚!你放开她!
”陈瓷尖叫着去掰他的手。贝贝看看妈妈,又看看抱着自己的陌生叔叔。
大概是因为刚刚被救了,又或者是因为这个男人抱着她的感觉……很奇怪,有点硬邦邦的,
但莫名地让她没那么害怕了。她小声地,带着浓浓的鼻音回答:“我叫……陈贝贝。
”“陈贝贝……”周砚低声重复了一遍,眼神深得看不见底。他抬眼,
终于看向脸色惨白、浑身发抖的陈瓷,眼神锐利如刀,“陈瓷,你瞒得真好。
”陈瓷像是被抽干了所有力气,靠着冰冷的墙壁滑坐到地上,无声地流泪。
贝贝看到妈妈哭了,小嘴一瘪,也哇地哭出声,朝妈妈伸出小手:“妈妈!妈妈抱!
”周砚沉默了几秒,终于弯腰,小心翼翼地把哭泣的贝贝放回陈瓷怀里。
陈瓷立刻像抱住了失而复得的珍宝,紧紧搂着女儿,脸埋在贝贝小小的肩膀上,
肩膀剧烈地耸动。周砚站直身体,居高临下地看着蜷缩在地上的母女俩。
他脸上的震动和复杂情绪已经收敛,又恢复了那种深沉的、看不出喜怒的平静。
只是他插在西装裤兜里的手,攥得很紧,指节泛白。“明天上午九点,”他开口,声音冷硬,
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带着孩子,到恒远大厦顶层找我。我们谈谈。”说完,
他不再看她们,转身走向车子。安保人员替他关上车门。几辆黑色轿车,
沉默地驶离了老旧的小区,留下死寂的沉默和瘫坐在地上的母女,以及一群目瞪口呆的邻居。
那天晚上,陈瓷家的灯一直亮到后半夜。第二天早上,我出门上班,
正好碰到陈瓷牵着贝贝下楼。陈瓷眼睛肿得像核桃,脸色苍白,
但神情却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平静。她给贝贝穿了条最好看的小裙子,头发也仔细梳过了。
“李姐。”她跟我打了个招呼,声音沙哑。“去……见他?”我问。她点点头,
握紧了贝贝的手:“总要有个了断。”贝贝仰着小脸,看看妈妈,又看看我,
小声说:“李阿姨,我们去见那个很高的叔叔。妈妈说他……是我爸爸?
”她的小脸上满是困惑。陈瓷眼圈又红了,没说话,只是摸了摸贝贝的头。“贝贝乖,
听妈妈的话。”我只能这么安慰。看着她们母女俩走出单元门,
走向公交站台那瘦小而倔强的背影,我心里沉甸甸的。恒远大厦顶层。
巨大的落地窗外是城市的全景,阳光洒进来,明亮得有些刺眼。
空气里弥漫着昂贵的咖啡香和一种无形的、令人窒息的压迫感。陈瓷坐在宽大的真皮沙发上,
背脊挺得笔直,像一根绷紧的弦。贝贝挨着她坐着,小手紧紧抓着妈妈的衣角,
大眼睛里充满了对这个陌生豪华环境的紧张和好奇。周砚坐在巨大的办公桌后面,
手指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光滑的桌面,发出笃笃的轻响。他换了一身更休闲的深色衬衫,
袖子随意挽到手肘,少了几分昨日的冷厉,但眼神依旧锐利,审视着对面的母女。“条件。
”他开门见山,没有任何寒暄,“孩子必须认祖归宗。周家的血脉,不能流落在外。
”陈瓷放在膝盖上的手猛地攥紧,指甲几乎掐进肉里:“贝贝是我的女儿!
”“她身上流着我的血!”周砚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不容置疑的强势,随即又压了下去,
恢复冰冷,“抚养权,我不会放弃。你可以提任何物质上的要求。”“我不要你的钱!
”陈瓷的声音也在发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愤怒,“我只要我的女儿!周砚,
我们当年为什么分开你心里清楚!你那样对我,凭什么现在来抢我的孩子?
”周砚的眼神瞬间沉了下去,像暴风雨前的海面:“陈瓷,当年的事,各执一词。
但孩子的事,你隐瞒五年,这是事实!
你让她跟着你过这种……”他扫了一眼陈瓷洗得发白的衣角,眼神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痛楚,
但很快被冷硬取代,“……拮据的日子,就是为她好?”“拮据?”陈瓷像是被刺痛了,
猛地站起来,“是!我是没钱!我没法给她买最好的玩具,穿最贵的衣服!
但我给了她全部的爱!我每天陪着她!你呢?周砚,这五年你在哪里?你在哪个女人身边?
你现在凭什么来指责我?”贝贝被妈妈突然拔高的声音吓到了,小嘴一瘪,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紧紧抱住陈瓷的腿。“妈妈……”她小声呜咽。
周砚看着女儿害怕的样子,眉头狠狠拧起,刚想开口。
“叮铃铃——”他放在桌上的私人手机突然尖锐地响了起来,
打破了办公室里剑拔弩张的气氛。周砚被打断,脸色更加难看,瞥了一眼来电显示,
是公司一个重要项目的紧急联络人。他深吸一口气,强压下火气,拿起手机,
声音冷硬:“什么事?说。”他听着电话,眉头越皱越紧,脸色也越发阴沉。陈瓷抱着贝贝,
胸口起伏,眼泪无声地滑落。
办公室里只剩下周砚压抑着怒火的低沉通话声和贝贝压抑的抽泣声。
就在这僵持而紧绷的时刻——坐在沙发上的贝贝,
大概是被那个一直响个不停的电话吸引了注意力,又或许是想找点东西分散自己的害怕。
她的小手无意识地伸进自己那个小小的、印着小熊的挎包里,摸啊摸。然后,
她摸到了一个小小的、硬硬的东西。她把它掏了出来。
是一颗亮晶晶的、指甲盖大小的小水钻扣。正是那天她送给我的那一颗,
后来不知怎么又回到了她的小包包里。阳光透过落地窗,正好照在这颗小水钻扣上。
切割面瞬间折射出无数道细小而璀璨的光芒,像小小的彩虹,跳跃着,
晃过周砚因为烦躁而低垂的眼睫。周砚正被电话那头的坏消息搅得心头火起,刚想发火,
那道细碎跳跃的彩光毫无预兆地撞入他视线。他下意识地眯了下眼,
目光顺着光线的来源看去。办公桌对面,沙发边上,
那个小小的、穿着旧裙子、脸上还挂着泪珠的女孩,正摊开小手,
专注地看着掌心那颗折射出七彩光芒的小东西。阳光给她柔软的头发镀上一层毛茸茸的金边。
她看得那么认真,长长的睫毛上还沾着泪珠,却因为手里那点小小的“星光”,忘记了哭泣,
小脸上只剩下孩童最纯粹的、发现新奇事物的好奇和一点点小心翼翼的欢喜。那道细碎的光,
和她安静专注的侧影,像一颗小小的石子,毫无预兆地投入周砚此刻充满怒意和烦躁的心湖。
电话那头,下属还在焦急地汇报着一个关键数据模型的重大错误,可能导致项目延期数月,
损失巨大。周砚的目光却停留在贝贝和她掌心那颗不起眼的小水钻上。时间仿佛凝滞了一秒。
就在那一秒里,他脑海里电光火石般闪过一个模糊的片段——很多年前,
大概也是贝贝这么大的时候,他好像也在什么地方,
被类似这样一道小小的、不起眼的折射光吸引过?然后……然后发生了什么?
好像避开了一次不大不小的麻烦?记忆太遥远太模糊,抓不住。
但那道来自女儿掌心的、微弱的、彩虹般的光,却奇异地像一盆冰水,
瞬间浇熄了他心头那簇因为项目危机和眼前谈判僵局而熊熊燃烧的怒火。
一种莫名的、近乎荒谬的平静感,毫无道理地涌了上来。他对着电话那头,
原本准备爆发的斥责,到了嘴边,鬼使神差地变成了一句异常冷静的指令:“……等等。
把你刚才说的那个原始数据包,后缀是‘备份_V3’的那个,重新加载一次试试看。
”电话那头显然愣住了,几秒后传来敲击键盘的声音,
然后是下属难以置信的、带着狂喜的声音:“周总!加载成功了!
之前的错误……是、是加载错了版本!天啊!备份V3是对的!模型运行正常了!没有错误!
项目可以按时推进了!”巨大的危机,因为一个极其低级的、错拿旧版本数据的失误,
因为周砚在怒火边缘离奇恢复的冷静,而戏剧性地化解了。办公室里一片死寂。
周砚缓缓放下电话,目光再次落回沙发边。贝贝似乎感觉到他的注视,抬起小脸,
怯生生地看了他一眼,又飞快地低下头,小手紧紧攥住了那颗小水钻扣。陈瓷也愣住了,
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周砚看着贝贝紧握的小拳头,又看看她身上那条洗得发白的旧裙子,
再看向陈瓷那张苍白却写满倔强的脸。刚才那股因为项目危机解除而升起的荒谬感,
混合着一种更深沉、更复杂的情绪,翻涌上来。他沉默了很久。久到空气都快要凝固。然后,
他站起身,绕过巨大的办公桌,一步一步,走向沙发边的母女。他的脚步很沉,
每一步都像踩在陈瓷紧绷的心弦上。她下意识地把贝贝往身后藏了藏,像护崽的母兽。
周砚在她们面前停下,高大的身影投下一片阴影。他没有看陈瓷,而是缓缓地、极其生疏地,
蹲下了身。视线与坐在沙发上的贝贝齐平。这个在商场上杀伐决断、从不低头的男人,
此刻以一种近乎笨拙的姿态,蹲在一个小小的孩子面前。
他看着贝贝那双像小鹿一样清澈又带着怯意的眼睛,看着她紧紧攥着的小拳头,声音低沉,
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连他自己都感到陌生的艰涩和……温和。“贝贝,”他叫她的名字,
有些拗口,“你手里拿的……是什么?”贝贝被这个高大叔叔突然蹲下来的动作吓了一跳,
小身子往后缩了缩,紧紧贴着妈妈。她看看周砚,又看看自己攥紧的小拳头,犹豫了一下,
才非常非常慢地,摊开了小手。那颗小小的、廉价的水钻扣,静静躺在她的掌心,
在阳光下折射着细碎的光。“亮晶晶……”贝贝小声说,声音细细的,带着点鼻音。
周砚的目光落在那个小东西上。很普通,甚至有些劣质,大概是从哪个地摊发卡上掉下来的。
但此刻,它躺在女儿小小的、柔软的手心里,却仿佛承载着某种奇异的分量。
他想起刚才那道让他恢复冷静的光。想起下属在电话那头劫后余生的狂喜。想起这五年,
他缺席的时光。再开口时,他声音里的冰碴子,似乎被某种东西融化了些许。“嗯,很亮。
”他应了一声,目光从水钻扣移开,重新看向贝贝,又缓缓抬起眼,看向紧绷如弓的陈瓷。
“抚养权的事,”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斟酌每一个字,“暂时搁置。”陈瓷猛地睁大眼睛,
难以置信。“孩子还小,突然改变环境对她不好。”周砚的声音平稳,听不出情绪,
“她需要时间适应。”他站起身,居高临下,但那份迫人的气势收敛了许多。
“我会承担她的一切生活、教育费用。你可以继续和她生活在一起,”他看着陈瓷,
“但我要随时可以探视她。每周至少两次。”这突如其来的转变,巨大的让步,
让陈瓷彻底懵了。她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只是下意识地把贝贝抱得更紧。
周砚的目光最后落在贝贝身上,那眼神深处,有什么东西在悄然改变。不再是冰冷的审视,
而是多了一丝……探究?或者说,是一种被命运猝不及防塞到怀里的、带着巨大问号的联系。
“今天先这样。”他转过身,走向办公桌,背影依旧挺拔,却似乎卸下了某种沉重的铠甲,
“司机会送你们回去。具体细节,我的助理会联系你。”陈瓷抱着贝贝,
浑浑噩噩地走出了恒远大厦那气派非凡的旋转门。阳光刺得她眼睛发痛。刚才发生的一切,
像一场光怪陆离的梦。周砚态度的急转直下,那莫名其妙的“搁置”,
还有他看着贝贝时那复杂难辨的眼神……是因为贝贝手里那颗小水钻?因为那道光?
这个念头荒谬得让她自己都觉得可笑。可除此之外,她找不到任何合理的解释。
在周砚看到贝贝手里那颗小东西之前,他的态度强硬得像块钢板,没有丝毫转圜余地。
就在那之后……陈瓷低头,看着怀里安静玩着自己小挎包的贝贝。“贝贝,”她声音有些哑,
“刚才那个……亮晶晶,能给妈妈看看吗?”贝贝很听话,
立刻从小挎包里掏出那颗小水钻扣,递给妈妈。陈瓷捏着这颗小小的、廉价的塑料水钻。
它很轻,边缘甚至有点刮手。除了在强光下能闪一闪,没有任何特别之处。
难道……真的只是巧合?是周砚自己突然想通了?或者,是那个及时的电话让他心情变好了?
她甩甩头,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赶出去。无论如何,周砚暂时放弃了立刻争夺抚养权,
这对她来说,是天大的喘息机会。接下来的日子,像是被投入石子的湖面,涟漪不断,
却又诡异地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周砚的助理效率极高,第二天就联系了陈瓷。
的抚养费;周砚在市中心一个安保极好、环境清幽的高档小区给她们安排了一套宽敞的公寓。
陈瓷看着那份协议,手指冰凉。她不想接受。这像是一种变相的圈养,
一种用金钱编织的牢笼。周砚随时可以用这份“优渥”来证明他更适合抚养孩子。
但现实是残酷的。贝贝需要好的教育环境,需要更稳定的生活。她单薄的力量,
在周砚庞大的资本面前,不堪一击。拒绝,可能意味着更激烈的冲突,
意味着周砚会立刻重启抚养权官司,而她几乎没有胜算。最终,她颤抖着手,
在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每一笔,都像刻在心上。搬家那天,周砚没有出现。
只有他的助理和搬家公司的人忙前忙后。新公寓很大,很漂亮,
窗外是葱郁的绿化和安静的花园。家具都是崭新的,一应俱全,
甚至还有一间专门给贝贝准备的、堆满了崭新玩具和绘本的儿童房。
贝贝第一次看到这么多新玩具,兴奋地跑来跑去,小脸红扑扑的。
陈瓷站在空荡荡的客厅中央,看着女儿开心的笑脸,心里却空落落的,
像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这华丽的一切,都带着周砚的印记,提醒着她,她们母女的生活,
已经不再完全属于自己了。周砚的探视,准时开始。第一次,是在周末的下午。门铃响起时,
陈瓷的心跳得像打鼓。打开门,周砚站在门外。他换下了西装,
穿着质地柔软的深色羊绒衫和休闲裤,少了几分商场的凌厉,
但那份与生俱来的气场依旧让人无法忽视。他手里拎着一个巨大的、包装精美的玩具盒。
“爸爸!”贝贝从陈瓷身后探出小脑袋,小声地、试探性地叫了一声。自从那天在办公室,
周砚蹲下来跟她说话后,小家伙对这个“很高的叔叔”的恐惧似乎少了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