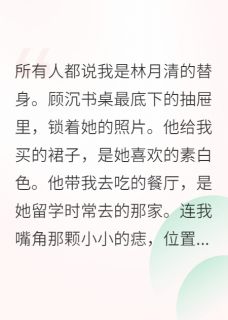
所有人都说我是林月清的替身。顾沉书桌最底下的抽屉里,锁着她的照片。他给我买的裙子,
是她喜欢的素白色。他带我去吃的餐厅,是她留学时常去的那家。连我嘴角那颗小小的痣,
位置都和她一模一样。顾沉从不否认。他只是捏着我的下巴,
眼神像在估价一件瓷器:“蓝薇,做好你该做的事。”我该做的事,
就是扮演好林月清的影子。直到她本人回来。林月清回国那天,顾沉亲自去机场接她。
我坐在客厅等到凌晨。玄关传来声响。顾沉扶着林月清进来。她穿着米白色的羊绒大衣,
脸颊微红,靠在他肩上,柔弱无骨。顾沉的眼神,是我从未见过的温柔。“阿沉,
我好晕……”林月清的声音像浸了蜜糖。“我扶你上去休息。”顾沉的声音低柔。
他看都没看我一眼,仿佛我只是空气。林月清的目光却扫过来。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
“这位是……?”她明知故问。顾沉这才瞥向我,眉头微皱,语气淡漠:“蓝薇。
”连句“我女朋友”都吝啬。林月清恍然,对我露出一个歉意的笑:“不好意思,
打扰你们了。阿沉就是太紧张我,我时差没倒过来,有点不舒服。
”她手指轻轻拽着顾沉的袖口。像某种无声的宣告。顾沉拍了拍她的手背,动作自然亲昵。
“客房收拾好了,你先上去。”他对林月清说。又转向我,命令的口吻:“蓝薇,
去倒杯蜂蜜水。”我站着没动。指甲掐进掌心。顾沉脸色沉下来:“没听见?
”林月清立刻打圆场:“算了阿沉,别麻烦蓝**,我自己来就好……”“她住在这里,
就是佣人。”顾沉打断她,眼神冰冷地钉在我身上,“让你去倒水,很难?”佣人。
原来我连替身都不是了。只是个佣人。心口像是被捅了一刀,又被狠狠拧了一把。
我转身走进厨房。身后传来林月清压低的声音,带着恰到好处的担忧:“阿沉,
你这样……蓝**会难过的。”顾沉的回答清晰地传过来,像淬了毒的冰针。“她?
一个影子罢了。认清自己的位置,就不会难过。”蜂蜜罐的盖子有点紧。我用力拧开。
金黄色的粘稠液体倒进玻璃杯。加温水。搅拌。动作机械。眼泪砸在流理台上,一滴,两滴。
没有声音。倒完水,我没有送去客厅。直接上了三楼的小阁楼。那是顾沉堆放旧物的地方。
平时不许人进去。今天门没锁。大概是他急着去接林月清,忘了。里面堆满了蒙尘的纸箱。
**着冰冷的墙壁滑坐到地上。抱住膝盖。替身三年。一千多个日夜。我以为时间久了,
石头也能焐热。结果只是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林月清回来了。
我这个劣质的赝品,就该退场了。也好。该醒了,蓝薇。阁楼窗户没关严,冷风灌进来。
我打了个哆嗦。目光无意间扫过墙角一个敞开的旧纸箱。里面露出一个褪色的蓝色书包一角。
很眼熟。我鬼使神差地爬过去。拨开上面压着的几本旧书。把那个书包抽了出来。帆布材质,
洗得发白,边角磨破了。书包侧袋上,用红线歪歪扭扭地绣着一朵小小的向日葵。
像一道闪电劈进脑海。我猛地拉开主袋拉链。里面空荡荡。
只有一张折叠起来的、泛黄的硬卡纸。我颤抖着手打开它。是一张儿童蜡笔画。画得很幼稚。
蓝天,白云,绿草地。草地上躺着一个穿西装的小男孩,闭着眼睛。
旁边站着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手里举着一块砖头。画的右下角,
用铅笔写着两个歪歪扭扭的字:【证物】。记忆的闸门轰然倒塌。十二年前。
城西那个废弃的工厂。我去捡废铁,想卖钱给妈妈买退烧药。听见里面传来打骂声和哭声。
几个染着黄毛的小混混,围着一个穿着精致小西装的男孩。拳打脚踢。男孩抱着头,
缩在地上,一声不吭。旁边扔着一个被踩烂的蛋糕。“顾家的小少爷?呸!落单了就是条狗!
”“把你身上值钱的都交出来!”“骨头还挺硬!”一个混混抄起半块砖头,
要朝男孩头上砸。我脑子一热。从藏身的废铁堆后面冲出去。用尽全身力气,
把手里的半块砖头砸在那个举砖混混的后背上。“啊!”他吃痛,砖头掉了。
“哪来的死丫头!”其他混混反应过来,恶狠狠地瞪着我。我害怕得要命。腿肚子都在抖。
但还是捡起掉在地上的砖头,举起来,挡在那个男孩前面。
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我……我报警了!警察马上就到!”其实是唬人的。我哪有钱打电话。
混混们互看一眼,有点迟疑。“妈的,晦气!快走!”领头的啐了一口。他们跑了。
我浑身脱力,砖头掉在地上。转身去看那个男孩。他脸上有伤,嘴角破了,流着血。
但眼睛很亮。像落满星子的夜空。他挣扎着想站起来。我扶了他一把。他靠着我,
声音很低:“谢谢。”我从那个破书包里,掏出皱巴巴的半张草稿纸和一小截铅笔头。
“你……你叫什么名字?”我问他。他沉默了一下。“顾沉。”我在纸上画了刚才那一幕。
画得很丑。我指着画里举着砖头的小人:“我,救了你。
”又指着那个躺在地上的小人:“你。”然后把画塞到他手里。“拿着,当证物。
以后……以后你要是忘了今天的事,不认账,我就拿这个找你。”他拿着那张画,
愣愣地看着我。“你叫什么?”他问。“蓝薇。”我说完,想起妈妈还在发烧,转身就跑,
“我得走了!”跑了几步,回头。他还站在原地,手里紧紧攥着那张画。小小的身影,
在空旷的废弃工厂里,显得格外孤单。后来,我再也没见过他。直到三年前。
我在顾氏集团应聘前台。面试我的主管临时有事,让我去总裁办公室送份文件。推开门。
宽大的办公桌后,男人抬起头。眉眼深邃,气质冷冽。只一眼。我就认出了他。
是那个废弃工厂里,眼睛像落满星子的男孩。顾沉。他也看到了我。
目光在我脸上停顿了几秒。尤其在我嘴角那颗小小的痣上。然后,他问了我的名字。“蓝薇。
”当天下午,人事通知我,被破格录取为总裁助理。搬进了他的别墅。开始了替身生涯。
我一直以为,他留我在身边,是因为记得。记得当年那个举着砖头救他的小女孩。
哪怕只有一点点模糊的印象。毕竟,我嘴角这颗痣,位置很特别。可现在。
看着手里这张泛黄的儿童画。看着那个被我珍藏了十二年的破书包。再看看楼下客厅里,
他对林月清呵护备至的样子。一个冰冷的事实砸得我头晕目眩。他认错人了。
他以为当年救他的人,是林月清。所以,他收集林月清的照片。给她所有她想要的东西。
把我留在身边,只因为我嘴角这颗痣,和林月清一模一样。他透过我,在看另一个女人。
而我,这个真正的救命恩人,在他眼里,不过是个可笑的替代品。连佣人都不如。
心像是被掏空了。冷风呼呼地往里灌。我捏着那张薄薄的画纸。指尖冰凉。原来,这十二年。
是我的一场独角戏。楼下隐约传来林月清娇软的声音和顾沉低沉的回应。像针一样扎进耳朵。
我慢慢地把那张画折好。连同那个旧书包。一起塞回了纸箱最底下。用旧书盖好。站起来。
拍了拍身上的灰。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眼泪早就干了。也好。该彻底结束了。第二天一早。
我下楼时,顾沉和林月清已经在餐厅吃早餐。阳光透过落地窗洒进来。林月清穿着真丝睡裙,
外面披着顾沉的西装外套。宽大的外套衬得她愈发娇小。她正小口喝着牛奶。
顾沉坐在她旁边,面前放着平板看新闻。画面和谐得像一幅画。我穿着昨晚那身衣服,
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林月清看见我,立刻放下杯子,露出甜美的笑容:“蓝**早!
昨晚睡得好吗?”她语气真诚。仿佛昨晚那个被顾沉亲自扶上楼的人不是她。顾沉头也没抬,
手指划着平板屏幕。我拉开椅子坐下。没看林月清。直接对顾沉说:“顾总,我今天搬出去。
”餐厅里瞬间安静。只有平板电脑里财经新闻主播毫无感情的声音在播报。
顾沉划屏幕的手指顿住。他终于抬起眼。目光落在我脸上。
带着审视和一丝不易察觉的……不悦?“理由。”他声音没什么温度。“林**回来了,
我再住这里不合适。”我语气平静。林月清连忙开口,一脸善解人意:“蓝**,你别误会!
是我打扰了你们才对!我找到房子就搬走的!阿沉,你说句话呀!
”她轻轻推了推顾沉的胳膊。顾沉没理她。他放下平板,身体往后靠在椅背上,看着我。
眼神像冰冷的探照灯。“你在闹什么?”闹?我扯了扯嘴角。“顾总误会了。我只是觉得,
正主回来了,我这个替身该退场了。占着位置,对林**不尊重。”“蓝薇!
”顾沉的声音陡然沉下去,带着警告。林月清的脸色也变了一下,但很快恢复如常。
她站起身,走到我身边,想拉我的手。我避开了。她的手僵在半空,眼圈瞬间红了,
看向顾沉,声音委屈:“阿沉,蓝**是不是生我气了?
我真的不知道会这样……”顾沉的脸色更难看。他盯着我,眼神像刀子。“道歉。
”我愣了一下。“什么?”“为你刚才的话,向月清道歉。”他一字一句,不容置喙。
荒谬感像潮水一样淹没了我。我看着眼前这个男人。这个我默默喜欢、小心陪伴了三年的人。
这个我十二年前用半块砖头救下的小男孩。只觉得无比陌生。心口那片被掏空的地方,
开始细细密密地疼。我深吸一口气。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稳。“顾总,我没有说错什么,
不需要道歉。我只是通知您,我今天会搬走。”说完,我站起身,准备离开餐厅。“站住!
”顾沉的声音带着怒意。他猛地站起来,椅子腿刮擦大理石地面,发出刺耳的声音。
几步就跨到我面前。高大的身影带着压迫感。阴影笼罩下来。“蓝薇,我是不是太纵容你了?
”他声音压得很低,像暴风雨前的闷雷,“让你忘了自己的身份?”身份?替身的身份?
佣人的身份?我抬起头,直视着他冰冷的眼睛。那里面,没有一丝一毫十二年前的星子。
只有深不见底的寒潭。“顾总,”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出奇地冷静,“我的身份,是您给的。
现在,我不要了。”他瞳孔似乎缩了一下。像是没料到我会这样顶撞他。
林月清适时地**来,拉住顾沉的胳膊,柔声劝:“阿沉,你别生气!蓝**可能心情不好,
我没事的,真的!”她转向我,眼神带着恳求:“蓝**,你先冷静一下,别冲动好吗?
搬出去你能住哪里呀?”“不劳林**费心。”我避开她的目光,看向顾沉,
“我的东西不多,很快收拾好。钥匙我会放在玄关。”不再看他们任何人的脸色。
我转身走出餐厅。上楼。身后传来林月清带着哭腔的劝解和顾沉压抑着怒火的呼吸声。
与我无关了。我的东西确实不多。几件衣服,一些洗漱用品,一个用了多年的旧笔记本。
全部塞进行李箱,绰绰有余。这个住了三年的地方,没有留下任何我生活过的痕迹。
就像我这三年的人生。一场徒劳。拉着行李箱下楼。顾沉和林月清还站在客厅里。气氛僵持。
顾沉背对着我,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背影紧绷。林月清坐在沙发上,眼睛红红的,
像是哭过。听到动静,她立刻看过来。顾沉也缓缓转过身。他看着我手里的行李箱,
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蓝薇,你想清楚。”他声音低沉,带着最后通牒的意味,
“走出这个门,就别想再回来。”我停下脚步。看着他。
看着这张让我魂牵梦萦了十二年的脸。第一次,看得如此清晰,如此心冷。“顾总,
”我平静地开口,“三年前我进来,就没想过再回来。”他下颌线绷紧。
眼神锐利得像要穿透我。我拉着行李箱,继续往玄关走。“蓝薇!”他猛地提高声音,
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急?林月清也站起来,快步走过来,想拦住我。“蓝**,
你别这样!阿沉他……”我绕开她。走到玄关。把别墅钥匙从包里拿出来。
轻轻放在那个昂贵的水晶托盘里。发出“叮”的一声脆响。然后,我拉开了厚重的雕花大门。
外面阳光很好。有点刺眼。我拉着行李箱,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身后。是死一般的寂静。
门关上的瞬间。仿佛隔绝了两个世界。我租了个小单间。离顾氏集团很远。
用这些年攒下的钱付了押金和三个月房租。卡里还剩一点。够我撑到找到新工作。
顾沉没有找我。一条信息,一个电话都没有。意料之中。我在网上投简历。重新开始。
日子忙碌而平静。像退潮后的沙滩。空旷,却踏实。偶尔,会从财经新闻上看到顾氏的消息。
或者,在八卦小报的边角,看到顾沉和林月清出双入对的**照。郎才女貌。很登对。
我看着。心里没什么波澜。那颗曾经为他跳动的心。好像真的死了。半个月后。
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是蓝薇**吗?这里是仁和医院,
请问顾沉先生是您的紧急联系人吗?他出了点意外,方便的话,
请您尽快过来一趟……”紧急联系人?我愣了一下。才想起,刚搬进别墅时,
顾沉让助理处理过一份文件,里面似乎有紧急联系人这一项。当时助理随口问填谁。
顾沉头也没抬:“填她。”助理就把我的名字和号码填上去了。后来,大概也忘了改。
我握着手机。沉默了几秒。“抱歉,我和顾先生已经没有任何关系。麻烦你们联系其他人吧。
”说完,我挂了电话。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心里一片平静。没有去看他的理由。
更没有去看他的立场。傍晚。手机又响了。还是那个号码。我皱了皱眉,挂断。
对方锲而不舍。第三次打来时,我接了。“蓝**!求您了!顾总他……他情况不太好,
一直在昏迷中喊……喊您的名字!林**也在,但她……”护士的声音带着焦急和为难。
我打断她:“你们应该联系他的家人。”“联系了!顾董和夫人都在国外,一时赶不回来!
林**她……她好像被吓到了,一直在哭,完全没办法……”护士的声音带着恳求,
“蓝**,就当帮帮忙,来看一眼行吗?顾总他……好像很需要您。”昏迷中喊我的名字?
我扯了扯嘴角。大概是喊“月清”,护士听错了吧。“抱歉,我……”“蓝**!
”护士急得快哭了,“顾总他……他刚才心率突然不稳,医生在抢救!
他嘴里一直含糊不清地念着‘薇薇’……是您的名字吧?求您了!
”薇薇……我的指尖猛地一颤。这个名字,除了我妈,只有小时候……废弃工厂里,
那个小男孩,好像这样叫过我一次。像一根极细的针,猝不及防地扎进心口最深处。
泛起细密的疼。我闭了闭眼。深吸一口气。“地址发我。”推开病房门。
消毒水的味道扑面而来。高级单间。很安静。顾沉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头上缠着纱布,
闭着眼,还在昏迷。点滴一滴一滴往下落。林月清坐在旁边的沙发上,眼睛肿得像核桃,
脸色比顾沉还白。看到我进来,她像是看到了救星,猛地站起来。“蓝**!你来了!
”她的声音带着哭腔,扑过来想抓我的手。我下意识地后退一步。她的手僵在半空。
脸上闪过一丝尴尬和……怨怼?但很快被楚楚可怜取代。“蓝**,你来了就好!
阿沉他……他刚才好吓人……”她说着又要哭。我避开她,走到床边。看着病床上的人。
眉头紧锁,嘴唇干裂,即使在昏迷中,也透着一种不安稳。额角的纱布渗出一点淡红。
“怎么回事?”我问护士。护士松了口气,连忙解释:“顾总下午参加一个奠基仪式,
工地临时搭建的台子突然塌了,顾总为了保护旁边的林**,
被一根掉落的钢管砸到了头……”保护林**。我扯了扯嘴角。果然。“医生怎么说?
”“轻微脑震荡,有淤血,需要观察。刚才突然心率不稳,可能是淤血压迫神经导致,
现在已经稳定了。”护士顿了顿,小心地看了一眼旁边的林月清,“顾总昏迷后,
一直……不太安稳,叫您的名字。”林月清的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她咬着嘴唇,
泫然欲泣地看着我:“蓝**,我知道以前……是我不好。但现在阿沉需要你,
你能不能……留下来陪陪他?我……我有点害怕……”她身体微微发抖,
像是真的受了很大惊吓。我看着她。没说话。护士也恳求地看着我:“蓝**,
顾总现在的情况,最好有熟悉的人陪着,情绪会稳定些。林**她……状态不太好。
”言下之意,林月清靠不住。我看着病床上脆弱的顾沉。
那个在商场上叱咤风云、在我面前永远高高在上的男人。此刻像个无助的孩子。
他干裂的嘴唇微微翕动。发出模糊不清的音节。护士凑近听了听,
对我肯定地点点头:“是在叫‘薇薇’。”心口那根针,又往里扎深了一点。
带着陈年的锈迹。“我留下。”我说。林月清明显松了口气,脸上挤出感激的笑:“谢谢你,
蓝**!那……那我先回去休息一下,我头好晕……”她扶着额头,弱不禁风地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