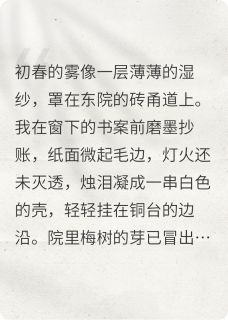
他侧头想了想:“因为早,会被人抢话;晚,会被人收个尾。
你只要在他们最想把你压下去前一瞬站起来,说一句看得见、摸得着的话,就够了。其余,
让他们自己乱。”我怔了一下,才发现这道理简单得像算盘珠子,碰一下就响。
我忽然笑了一下,那笑意里有凉风,也有一点点热气。他似乎也轻松了些,正要说话,
忽有脚步从另一边的廊下急急踏来。来人低声道,祖堂吩咐:宗案拟给东院一纸文书,
嫁妆铺由我临管三月,三月后再议。我接过那纸,看了一眼,落款与印记齐全,
手里的纸在灯下微微泛黄。我把纸放进袖里,谢过来人。顾延看我,眼神里有一句“恭喜”,
却没说出口。三月,足够把每一个洞填住,也足够让每一只手露出指尖。我回屋把文书放好,
坐在书案前,点灯,把陆掌柜那几张票据与对照表重新摊开。阿秀端了茶进来,眼角还有红。
我让她坐,她小心看我一眼,坐在角落。我把要做的事一一说给她听:先复盘南市的货,
按出入项把每一条录成册;再去各铺回访,
向行家解释递延的原委;再借宗案之名清查库房钥匙,换成分管制;徐三那边,
暂调小徒来东院,白日里按时对账,夜里不许留灯;还有,给母亲留的几处旧契,
明日请亲近长辈来鉴,现场过数,立字为凭。阿秀一项一项记,手指飞快,
像捞住了根能抓的绳子。这些事说完已近三更。风小了,窗纸上的光也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