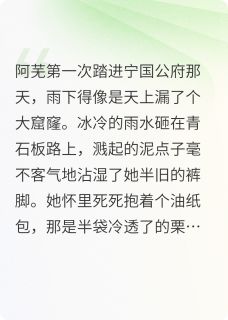
阿芜第一次踏进宁国公府那天,雨下得像是天上漏了个大窟窿。冰冷的雨水砸在青石板路上,
溅起的泥点子毫不客气地沾湿了她半旧的裤脚。她怀里死死抱着个油纸包,
那是半袋冷透了的栗子糕,也是她全部的行李。雨水顺着她湿透的发梢往下淌,流进脖颈里,
激得她一个哆嗦,可抱着油纸包的手臂却收得更紧了些。牙婆在旁边点头哈腰,
脸上堆着过分谄媚的笑,声音在哗啦啦的雨声里拔得又尖又细:“世子爷,您瞧,
这丫头可像?”高高的廊檐下,顾珩之就那么坐着,一身华贵的锦袍,
衬得周遭都黯淡了几分。他手里捏着一截东西,在黯淡的天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
阿芜眯起被雨水糊住的眼睛,才看清那是半截白玉簪子,簪头雕着一朵小巧精致的杏花,
花瓣舒展,栩栩如生。他抬眼,目光穿过迷蒙的雨幕,直直落在阿芜脸上。那目光,
像被烧红的烙铁烫了一下,猛地缩了回去,却又带着一种奇异的执拗,再次定定地看了过来。
阿芜只觉得脸上**辣的,下意识地想低头,却又强撑着规矩地站直了。“像。
”他终于开口,声音低得几乎要被磅礴的雨声彻底吞没,却又像一根细细的针,
清晰地扎进阿芜的耳朵里,“就是她了。”阿芜当时完全不懂他话里的意思,
只觉得这男人生得实在过分好看,眉眼像是画里走出来的一般,可那好看里头,
又裹着一层化不开的冷硬。她规规矩矩地低头行礼,
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能在这深宅大院里混口饭吃,冬天不用挨冻,挺好。她不知道,
自己这张脸,像极了顾珩之心底那个早早就埋了的人。那位传说中早逝的沈家**,沈杏,
那个总被人提起的、在杏花树下吹笛子的姑娘。她更不知道,怀里这半袋冷掉的栗子糕,
日后会成为她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成为某个人心头再也化不开的甜。
---顾珩之给她取名叫阿芜。“芜,”他当时坐在书案后,
手里还是无意识地摩挲着那半截白玉簪,目光落在窗外的虚空处,声音没什么起伏,
“就叫阿芜吧。”阿芜站在下首,恭敬地应了声“是”。心里却在偷偷嘀咕:芜?
听着有点荒凉的意思,不过……总比老家村里那些“狗剩”、“铁蛋”强多了,挺文雅,
挺好。宁国公府,门第森严,规矩大得能压死人。阿芜初来乍到,像只误入金丝笼的麻雀,
处处谨小慎微,生怕行差踏错半步。端茶倒水,轻手轻脚;走路说话,屏息凝神。
她把自己缩得小小的,恨不能变成墙角的影子。可顾珩之待她,却好得让她心里一阵阵发慌。
那好,不是主子对下人该有的好。太近了,太亲昵了,
带着一种她无法理解的、沉甸甸的专注。尤其到了夜里。书房里烛火摇曳,光线昏黄而暧昧。
顾珩之常常会放下手中的书卷或公文,靠在宽大的椅子里,朝侍立在一旁的阿芜伸出手,
声音像是被炉火煨化了的蜜糖,又软又黏:“阿芜,过来。”阿芜的心就会猛地一跳,
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了。她挪着步子走过去,刚靠近,就被他轻轻一带,
整个人便跌坐在他怀里,侧身坐在他坚实的大腿上。陌生的男性气息瞬间将她包裹,
带着清冽的松木香和淡淡的墨味,让她浑身僵硬得如同木偶。他的指尖带着薄茧,
带着夜里的微凉,轻轻抚上她的眉眼。那动作极慢,极细致,像在描摹一件稀世珍宝的纹路。
他的目光沉沉地落在她脸上,却又仿佛穿透了她,落在某个遥远得触碰不到的地方。
指尖划过她的眉骨、眼睑、鼻梁、脸颊……一寸一寸,带着一种令人心悸的贪婪和怀念。
寂静的书房里,只有烛花偶尔爆开的细微声响,
和他低得如同呓语般的呼唤:“阿杏……”“阿杏,你回来了……”“阿杏,
我好想你……”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冰冷的小锤子,轻轻敲在阿芜的心口上。原来如此。
所有的好,所有的温柔,所有的专注,都不是给她的。是给她这张脸,
给那个叫“阿杏”的、已经不在人世的姑娘。一股酸涩猛地冲上鼻腔,直逼眼眶。
阿芜用力地眨了眨眼,把那点不合时宜的水汽硬生生逼了回去。她微微垂下眼睫,
遮住眼底翻涌的情绪,一遍遍在心里告诫自己:阿芜,别犯傻,看清楚,你就是个影子,
就是个摆在眼前的念想。世子爷眼里的那个人,从来就不是你。她提醒自己:别犯傻,
你就是个替身。这府里的饭可以吃,这府里的暖可以享,唯独这虚妄的情,碰不得。
---日子像屋檐下滴答的雨水,不紧不慢地往前淌。阿芜在宁国公府这方精致的牢笼里,
渐渐摸到了一些生存的门道,也把“替身”这个身份,咀嚼得越发苦涩,却也越发习惯。
她发现,这位高高在上的世子爷顾珩之,其实骨子里是个顶难伺候的主儿。
偏偏这难伺候的点,还都跟那位沈家**沈杏脱不了干系。他嗜甜,却偏偏又怕腻得慌。
府里厨房变着花样做的精致点心,他常常只尝一口便搁下了,
眉宇间笼着一层不易察觉的烦躁。直到有一次,阿芜大着胆子,
把自己偷偷在厨房角落用粗陋法子蒸出来的、带着点朴素焦香的栗子糕,用小碟子盛了,
低着头呈了上去。顾珩之看着那几块卖相实在称不上好的糕点,难得地没有立刻让人撤下。
他拿起一块,咬了一小口,咀嚼的动作很慢。阿芜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片刻,
他竟又拿起一块,直到碟子快空了,才抬眼看向垂手侍立、紧张得手指都绞在一起的阿芜。
“以后……就照这个做。”他的声音听不出太多情绪,只是目光在她脸上停留的时间,
似乎比平时长了那么一瞬。阿芜的心重重落回肚子里,又悄然升起一丝莫名的微澜。从此,
给世子蒸栗子糕,成了她专属的差事。水温要恰到好处,粉要筛得极细,
火候更是要掐得精准无比,多一分少一分,都会被他尝出来。
阿芜在小小的厨房角落守着蒸笼,看着氤氲的热气,常常出神地想,那位沈**,
是不是也爱吃这样带着烟火气的栗子糕?顾珩之夜里睡不安稳,是府里公开的秘密。
有时阿芜守夜,能听见内室传来压抑的翻身声,或是模糊不清的低唤。有次她值夜时太困,
头一点一点地打瞌睡,被半夜口渴醒来的顾珩之撞见。他倒没斥责,只是第二天,
阿芜看见他眼下那片青黑更深了些。鬼使神差地,阿芜开始留意起安神的方子。
她偷偷攒下月钱里少得可怜的几个铜板,央求出门采买的婆子帮她带些便宜的干花和草药。
丁香、薰衣草、晒干的橘皮……她在自己那点小小的光亮下,笨拙地穿针引线,
用素净的棉布缝制小小的香囊。手指被针扎破是常事,她也不在意,
只把那点血珠子在粗布衣襟上蹭掉,继续一针一线地缝,缝得格外仔细,
仿佛要把所有无声的关切和提醒自己清醒的酸楚都缝进去。缝好了,她也不敢直接给他。
只是在他又显出疲惫烦躁时,低着头,
装作不经意地把那个小小的、针脚歪歪扭扭的香囊放在他枕边。顾珩之拿起香囊,
放在鼻尖下嗅了嗅。那是一种混合着廉价草药和干花、谈不上多高雅,
却莫名让人心神宁静的气息。他什么也没说,只是那晚,内室似乎安静了许多。第二天,
阿芜在他枕边看到了那个空了的香囊。最难的,是学吹笛子。府里的老乐师教**们学琴时,
阿芜曾远远地听过几次那清越悠扬的笛声。她听说,沈**杏花树下吹笛子的身影,
是世子心头抹不去的画。不知哪里来的勇气,或许是那晚顾珩之醉酒后,眼神迷离地看着她,
喃喃着“阿杏……笛……”,让阿芜心里那点不甘和隐秘的模仿欲破土而出。
她用攒了很久的月钱,托人从外面买回一支最最便宜的竹笛。没有老师,
她就躲在废弃的后院柴房里,对着墙上斑驳的光影,一点点摸索。气息不稳,
吹出来的声音像垂死挣扎的鸭子叫。手指僵硬地按着冰凉的笛孔,不一会儿就冻得通红麻木,
再用力按下去,指腹很快磨破了皮,渗出血丝,混着汗水,一按下去就钻心地疼。
“嘶……”她痛得倒抽冷气,看着渗血的指尖,心里那股倔劲儿却上来了。
她撕下衣角一小条布,胡乱缠住受伤的指腹,忍着疼,继续对着那小小的笛孔,
吹出断断续续、不成调的呜咽。日复一日,柴房里那鬼哭狼嚎般的笛声,
竟也渐渐有了点模样。至少,能把一曲最简单的《杏花天》吹得连贯起来了,
虽然离悠扬动听还差着十万八千里。终于,在一个顾珩之应酬归来,醉得不轻的夜晚。
他靠在榻上,眉头紧锁,显然极不舒服。阿芜看着他那副样子,心一横,
从袖中摸出那支磨得光滑了些的竹笛,凑到唇边。清幽的、带着几分生涩怯意的笛音,
在寂静的夜里缓缓流淌开来。正是那曲《杏花天》。笛声响起的那一刻,
原本闭目蹙眉的顾珩之,身体几不可察地僵了一下。他没有睁眼,只是紧锁的眉头,
在笛声中,一点点、极其缓慢地松开了。一曲终了,阿芜放下笛子,手心全是汗。
顾珩之不知何时睁开了眼,那双深邃的眸子在烛光下显得有些迷蒙,却一瞬不瞬地锁着她。
那目光复杂得让阿芜心慌,有怀念,有恍惚,还有一种她读不懂的、沉甸甸的东西。
他看了她很久,久到阿芜几乎要承受不住那目光的重量,想要落荒而逃。他才终于动了动,
朝她伸出手。阿芜迟疑了一下,慢慢走过去。他的手没有像往常那样抚上她的眉眼,
而是带着酒后的温热,落在了她的发顶,轻轻地、带着一种近乎怜惜的力道,揉了揉。
“阿芜,”他的声音因为醉酒而沙哑,却异常清晰地落在她耳中,“你乖。
”阿芜努力牵动嘴角,想挤出一个温顺的笑,心口却像猛地被塞进了一团浸透了水的棉花,
又沉又胀,堵得她几乎喘不上气。那股酸涩再次汹涌地漫上来,几乎要将她淹没。
---那天的杏花开得正好,粉白的花瓣簇拥在枝头,空气里浮动着甜丝丝的香气。
阿芜提着个小巧的竹篮,站在花园一角的杏树下,小心翼翼地挑选着开得最饱满的花枝。
她想着,书房里那尊素净的白瓷瓶,插上几枝杏花,或许能让他心情好些。
剪刀刚触到一根斜逸的枝条,两个小丫鬟清脆又带着点刻意压低的议论声,
就顺着风断断续续地飘了过来。“……听说了吗?天大的消息!”“什么呀?快说快说!
”“沈家!就是那个……以前跟咱们府上有婚约的沈家!”“啊?沈家怎么了?
”“沈家那位**!沈杏!没死!听说当年是得了急病被送到南边庄子上养着,瞒得死死的,
现在……人好了!要回京了!”“哐当!”阿芜手中的剪刀脱力地掉在地上,
锋利的尖端擦着她的鞋面划过,差一点就戳到了手指。她却浑然未觉,
只觉得一股冰冷的寒意从脚底板猛地窜起,瞬间流遍四肢百骸,冻得她血液都似乎凝固了。
沈**没死。那个她模仿了这么久,努力去靠近的影子,
那个顾珩之心心念念、刻在骨头里的名字……她没死。那她阿芜呢?
这个摆在眼前、聊以慰藉的替身,是不是该……退场了?像戏台上唱完了自己那折戏的龙套,
该悄无声息地撤下去了?她呆呆地站在原地,连剪刀都忘了捡。篮子里的几枝杏花,
在微风中轻轻颤动,粉白的花瓣零落地飘下几片,沾在她的衣襟上,像无声的祭奠。
那天傍晚,顾珩之回府了。他踏入院门时的脸色,是阿芜从未见过的难看。
阴沉得像暴风雨前的天空,薄唇抿成一条冰冷的直线,周身散发着一股生人勿近的戾气。
显然,他也得到了消息。他大步流星地穿过庭院,目光扫到独自坐在廊下发呆的阿芜时,
脚步猛地顿住。他几步走到她面前,高大的身影瞬间将她笼罩在一片阴影里。阿芜抬起头,
脸上没什么表情,平静地看着他。顾珩之突然伸出手,一把攥住了她的手腕。
那力道大得惊人,像是要把她的骨头捏碎,带着一种近乎绝望的凶狠。“阿芜,
”他的声音又低又沉,像从喉咙深处挤压出来,每一个字都带着灼人的热度,
“你哪儿也不许去!听见没有?!”手腕上传来的剧痛让阿芜微微蹙眉。
她看着眼前这个男人,看着他眼底翻涌的惊涛骇浪——有难以置信,有被欺骗的愤怒,
有得知旧爱尚存的狂喜,或许……还有那么一丝丝,对她这个替身去留的恐慌?真奇怪。
阿芜在这一刻,心里那片沉甸甸的、堵了许久的棉花,忽然像被戳破了一个口子,泄了气。
她甚至觉得有点好笑。她轻轻地,却又异常坚定地,一点一点,
将自己的手腕从他的铁钳般的大手中抽了出来。动作很慢,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疏离。
“世子爷,”她迎着他变得错愕的目光,唇角甚至勾起了一抹极淡、极飘忽的笑意,
声音平静得像一潭不起波澜的死水,“我本来就是……借来的物件儿。正主儿回来了,
物归原主,天经地义。”顾珩之的瞳孔猛地收缩,像是被这句话狠狠刺中了。他张了张嘴,
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只是死死地盯着她,眼里的风暴更加汹涌。阿芜不再看他,
低下头,揉了揉被捏得发红发痛的手腕。廊下的风,带着杏花最后的甜香,吹拂而过,
竟有几分刺骨的凉意。---沈家**沈杏回京的日子,选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
宁国公府,像是要把过去几年所有的沉寂都一扫而空。大红灯笼高高挂起,
崭新的绸缎彩带从门口一路铺陈到内院,仆役们脚步匆匆,脸上带着刻意的喜气,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浮夸的热闹。这喧嚣,与阿芜无关。她的小包袱,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几件洗得发白、叠得整整齐齐的旧衣裳,一套换洗的内衫,
还有……那支顾珩之曾经无数次摩挲在指尖、后来不知何时被她偷偷藏起来的白玉簪。
簪头的杏花依旧玲珑剔透,冰凉的触感透过布料传到手心。
阿芜最后看了一眼这个住了不算太久、却承载了她太多酸涩与隐秘期盼的屋子。没有留恋,
只有一种尘埃落定般的疲惫和解脱。她轻轻关上门,隔绝了外面那不属于她的喧嚣。
抱着小小的包袱,她低着头,沿着回廊的阴影处,像一抹不起眼的影子,悄悄向府门走去。
脚步很轻,却异常坚定。刚走到通往大门的月亮门洞下,
一个高大的身影便如铁塔般堵在了那里。是顾珩之。他显然是一路疾跑过来的,
呼吸还有些不稳,额角甚至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他直直地看着阿芜,
那双总是深不见底、或冷或沉的眼眸,此刻竟布满了骇人的红血丝,像一头濒临失控的困兽。
“阿芜!”他声音沙哑得厉害,带着一种近乎哀求的颤音,猛地伸出手,
似乎想抓住她的胳膊,“别走!”阿芜下意识地后退了一小步,避开了他的手。她抬起头,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平静得像一尊没有生命的玉像。“世子爷,”她微微福身,
行了一个无可挑剔、却也冰冷到极致的礼,“沈**回府,阖府欢庆。
我……也该回自己的地方了。”她的声音不高,却清晰地穿过门洞外隐隐传来的喧闹锣鼓声,
砸在顾珩之的心上。“自己的地方?”顾珩之像是被这几个字烫着了,声音陡然拔高,
带着难以置信的痛楚,“这里……”“这里从来不是我的地方。”阿芜打断他,
语气平静得残忍。她抱着包袱的手指微微收紧,指尖隔着布料触到那支冰冷的玉簪,
“世子爷,保重。”说完,她不再看他一眼,侧身,从他身边擦过。她的背影单薄得惊人,
肩膀瘦削,脊背挺直,像一片被秋风扫落的叶子,轻飘飘地,却又带着一种决绝的姿态,
向着那扇象征着自由与未知的大门走去。顾珩之下意识地抬脚就要追上去,
手臂却猛地被人从后面死死拽住!“世子!世子!”沈杏身边那个伶俐的大丫鬟气喘吁吁,
声音带着哭腔,急急喊道,“**……**她刚下轿,看到府里的布置,
一时激动……晕过去了!您快去瞧瞧吧!”顾珩之的身体猛地一僵,
追出去的脚步硬生生钉在了原地。他像是被一道无形的闪电劈中,霍然回头。
只见通往内院的花径那头,几个丫鬟婆子正簇拥着一个纤细柔弱的身影。
沈杏被人半搀半扶着,脸色苍白如纸,毫无血色,长长的睫毛上挂着晶莹的泪珠,
正盈盈欲坠。她似乎用尽了全身力气,才勉强抬起眼帘,隔着人群,
遥遥地望向门洞下的顾珩之。那眼神,充满了重逢的喜悦、病弱的无助、以及全然的依赖。
像一张精心编织的、脆弱又美丽的网。顾珩之的目光,
在阿芜那越来越远、即将消失在府门外的瘦削背影,
和花径那头苍白柔弱、泪眼盈盈的沈杏之间,来回剧烈地摇摆着。时间仿佛凝固了一瞬。
最终,那脚步,终究没能再向着大门的方向迈出去。他猛地转身,几乎是有些踉跄地,
朝着沈杏的方向大步走去,将那个纤细苍白的身影小心地接住,护在臂弯里。那瞬间的犹豫,
像一把冰冷的钝刀,在阿芜身后无声地落下。阿芜没有回头。她挺直了背,
一步踏出了宁国公府高高的门槛。门外,是车水马龙的街道,是喧嚣的市井气息,
是刺眼的阳光。那阳光照在她脸上,暖洋洋的,却照不进她空落落的心底。---城西,
柳条巷深处。一座小小的、只有两间正房带个巴掌大院落的老屋,便是阿芜唯一的归处。
这是她早逝的娘亲留下的唯一念想,久无人住,透着一股陈年的霉味和尘土气。
阿芜花了几天时间,才把这小小的蜗居收拾出个人样。窗纸重新糊过,
露出干净的窗棂;院角的杂草被连根拔起,
铺上了一层从河边捡来的光滑鹅卵石;屋里那张吱呀作响的旧木床,
被她用麻绳仔细地加固过。安顿下来,生计就成了顶要紧的事。她没别的本事,
唯一拿得出手的,就是那手蒸栗子糕的功夫。那是她在宁国公府厨房角落里,一遍遍摸索,
被蒸汽烫过无数次,才练就的本事——为了那张像沈杏的脸,为了那个爱吃栗子糕的男人。
如今,这本事成了她活下去的依仗。她狠了狠心,把娘亲留下的唯一一支素银簪子当了,
换回些必须的米面油糖、蒸笼灶具。小小的院门旁,挂起了一块简陋的木牌,
上面是她用烧黑的木炭歪歪扭扭写的三个字:栗子糕。小小的铺面,连张像样的桌子都没有。
阿芜把院门敞开,在门口支起一张从旧货市场淘换来的瘸腿小方桌,
上面整整齐齐码放着刚出锅、还冒着腾腾热气的栗子糕。金黄的色泽,朴拙的焦香,
在这烟火气十足的城西小巷里,倒也不算太扎眼。日子一天天过去,
像巷子口那条缓缓流淌的小河,平淡无波。阿芜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淘米磨粉,守着灶火,
看着蒸笼里升腾起白茫茫的雾气,将小小的院落熏蒸得暖意融融。糕蒸好了,
就摆在门口的小桌上,等着街坊邻居或是路过的行人买上几块。生意不算好,也不算太坏,
勉强糊口。只是每次掀开蒸笼盖子,看着那热气腾腾、金灿灿的糕点,闻着那熟悉的甜香时,
阿芜的心口总会莫名地空一下,像是缺了一块什么重要的东西,被那甜腻的香气一冲,
反而显得更加空旷寂寥。她以为日子就会这样不咸不淡地过下去,
像这城西无数个不起眼的小摊贩一样,淹没在市井的喧嚣里,直至被所有人遗忘,
包括她自己。所以,当那天下午,院门被拍得震天响,几乎要把那两扇薄薄的木板拍散架时,
阿芜着实吓了一跳。“谁啊?”她手上还沾着湿漉漉的米粉,一边在围裙上胡乱擦着,
一边疑惑地走过去开门。这粗鲁的拍门声,可不像街坊邻居。门栓刚拉开,
一股浓烈的酒气混杂着汗味和尘土味就扑面而来。门外站着的人,让阿芜瞬间僵在了原地。
是顾珩之。那个曾经在宁国公府高高在上、锦衣玉食、连衣角都纤尘不染的世子爷顾珩之。
此刻的他,完全打败了阿芜所有的记忆。一身华贵的锦袍皱得像在咸菜缸里腌了三天三夜,
沾满了不知是酒渍还是泥点子的污痕。下巴上冒出一片青黑色的胡茬,眼窝深陷,
布满了红血丝,整个人透着一股颓唐到极点的狼狈。唯有那双眼睛,在看到她的一瞬间,
像是濒死的人抓住了最后一根浮木,骤然爆发出骇人的亮光。“阿芜!”他开口,
嗓子哑得像被砂纸磨过,每一个字都带着撕裂般的痛楚,“我……我来接你回家。
”阿芜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冲头顶。她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身体微微绷紧,
手在围裙上擦得更用力了,仿佛要擦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世子爷说笑了。
”她扯了扯嘴角,露出一个极其疏离、甚至带着点讥诮的笑容,眼神却冷得像冰,“我的家,
在城西柳条巷,就这儿。”她抬手指了指脚下这片小小的、属于她的方寸之地。
顾珩之被她话语里的冰冷刺得浑身一颤,那双布满红血丝的眼睛瞬间更红了,
像是要滴出血来。他猛地往前踏了一步,高大的身影带着压迫感罩下来,
声音因为急切而抖得不成样子:“我知道!我知道你不是她!阿芜,我早就知道你不是沈杏!
”这句迟来的、近乎剖白的话,像一块巨石投入阿芜死水般的心湖,
却只激起了一圈微不可察的涟漪,便迅速沉没。阿芜抬起眼,平静地看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