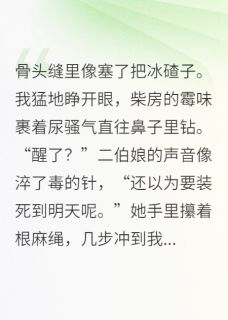
骨头缝里像塞了把冰碴子。我猛地睁开眼,柴房的霉味裹着尿骚气直往鼻子里钻。“醒了?
”二伯娘的声音像淬了毒的针,“还以为要装死到明天呢。”她手里攥着根麻绳,
几步冲到我面前,薅着我头发往墙上撞。“砰”的一声,眼前炸开一片金星。
“蛇王今晚就要来接亲,你倒好,敢绝食?”她唾沫星子喷在我脸上,
“真当自己是金枝玉叶?要不是看在你这身子能换三车粮食,早把你扔去喂狗了!
”我想张嘴骂,喉咙却像被砂纸磨过,只能发出嗬嗬的声。这不是我的身体。
昨天我还在医院里吊水,今天一睁眼,就成了这个叫“阿蛮”的姑娘。
零碎的记忆往脑子里扎——爹娘去年病死,叔伯们抢了家里的两亩薄田,
把我扔进柴房当牲口养。半年前村里老巫跳了场大神,说我是蛇王选中的媳妇,
要在月圆夜献祭。从那天起,他们每天只给我一口馊饭,美其名曰“保持洁净”。“娘,
别打了。”三叔公叼着烟袋走进来,烟锅里的火星在黑暗里明灭,“打出伤来,
蛇王怪罪怎么办?”二伯娘悻悻地松了手,我顺着墙滑到地上,后脑勺的血顺着脖子往下淌。
“这死丫头就是贱骨头。”她踢了踢我的腿,“前天还想爬墙跑,要不是老三反应快,
打断了她的腿,咱们的粮食早飞了!”我的目光落在自己右腿上,裤管空荡荡的,
骨头错位的地方肿得像个馒头。原来阿蛮不是饿死的,是被他们活活折磨死的。
三叔公蹲下来,用烟袋锅敲了敲我的脸:“阿蛮,听话。进了蛇洞,乖乖喝了那碗药,
少受点罪。”他指的是二伯娘手里的黑陶碗,里面飘着股苦杏仁味。是毒药。
他们怕我到了蛇洞哭闹,惹“蛇王”不高兴——虽然他们根本不知道蛇王长什么样。
“我不……”我终于挤出两个字,声音嘶哑得像破锣。二伯娘立刻炸了,
抬脚就往我肚子上踹:“反了你了!”剧痛让我蜷缩成虾米,胃里的酸水直往上涌。
柴房的门没关严,能看见外面飘着的红绸子。那是给“蛇王妻”准备的嫁衣。
三叔公按住二伯娘的肩,冲她使了个眼色。“行,不喝是吧。”他突然笑了,露出黄黑的牙,
“那就等蛇王自己来拿你的命。去年邻村那个犟丫头,被蛇啃得就剩副骨头架子,
听说眼珠子都被啄出来了。”二伯娘跟着笑,
声音尖利得像指甲刮玻璃:“到时候可别求我们。”他们转身出去,
铁链锁门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响。我趴在地上,血和眼泪混在一起,糊了满脸。
窗外传来更夫敲梆子的声,一下,又一下。还有三个时辰,天就要亮了。亮了,
他们就会把我塞进那件红嫁衣,抬去后山的蛇洞。那里没有蛇王。只有等着分粮食的村民,
和早就挖好的坟坑。我摸着断腿的地方,指甲深深掐进肉里。疼。但比起心里的恨,
这点疼算什么。阿蛮,你的仇,我替你报。我拖着断腿爬到柴房角落,
那里堆着阿蛮藏的几块干硬的红薯。必须活下去。哪怕只有一口气,也得从这鬼地方爬出去。
正啃着红薯,外面突然传来窸窸窣窣的声。有人在撬锁。是二伯娘他们反悔了?
我抓起身边的石头,后背死死抵住墙。锁“咔哒”一声开了。月光漏进来,
照出个佝偻的身影。是哑婆婆。她手里端着个粗瓷碗,看见我满身是伤,突然捂住嘴,
眼泪大颗大颗砸在地上。这是村里唯一给过阿蛮好脸的人,总趁叔伯不注意,
偷偷塞个野果给她。哑婆婆快步走过来,把碗递到我面前。是碗热粥,上面还漂着个鸡蛋。
我愣住了。她比划着让我快吃,又指了指后山的方向,手在脖子上划了一下。我懂了。
她是说,蛇洞有危险。可她怎么知道?正想问,
外面突然传来二伯娘的骂声:“老哑巴跑哪去了?”哑婆婆脸色一白,把粥往我怀里一塞,
从袖管里掏出把磨尖的石片,塞到我手里。然后她指了指柴房后墙,又指了指月亮,
最后做了个快跑的手势。后墙有洞?我还没反应过来,她已经转身出去,
故意踢翻了旁边的水桶。“谁在那儿?”二伯娘的声音越来越近。哑婆婆冲我摆了摆手,
一瘸一拐地往相反方向走,嘴里发出呜呜的声,像在故意引开他们。我握紧石片,
粥的热气烫得手心发疼。后墙果然有个狗洞,是阿蛮以前偷偷观察外面挖的。
月光透过洞口照进来,能看见外面的杂草。远处传来二伯娘打哑婆婆的声音,
还有哑婆婆压抑的哭嚎。我咬碎了牙。把粥几口灌进肚子,忍着腿骨断裂的剧痛,
一点点往狗洞挪。石片在手里攥得发白。三叔公,二伯娘。你们欠阿蛮的,欠哑婆婆的,
我会一点一点,全都讨回来。刚爬到洞口,
就听见柴房外传来三叔公阴沉沉的声音:“把老哑巴锁到柴房隔壁,别让她坏了明天的事。
”“那这死丫头……”“跑不了。”三叔公冷笑,“她那条腿,能爬到哪儿去?
”我钻进狗洞的瞬间,眼泪终于掉了下来。外面的风很冷,吹得我浑身发抖。但我知道,
从这一刻起,我不再是任人宰割的阿蛮。我是来索命的。爬过狗洞的那一刻,
草叶上的露水灌进领口。冻得我一哆嗦,断腿的地方像被人拿锥子狠狠扎了一下。
咬着牙往山上挪,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身后传来村子里的狗叫声,
还有三叔公他们骂骂咧咧的动静。他们发现我跑了。不敢回头,
只能盯着前面的黑影——那是后山的方向。哑婆婆刚才指的就是这儿。她肯定知道什么。
裤脚被草勾住,一拽,整个人重重摔在地上。断腿撞在石头上,疼得我眼前发黑,
差点晕过去。“妈的,这死丫头还真能爬!”是二伯的声音,离得不远。
他手里的火把照得周围亮堂堂的,树影在地上歪歪扭扭地晃,像一群张牙舞爪的鬼。
我赶紧往灌木丛里缩,把脸埋进草堆里。泥土的腥气呛得我直咳嗽,只能死死捂住嘴。
“老三,你说她会不会跑回蛇洞?”二伯娘的声音带着慌,“要是让她在蛇洞那边闹起来,
明天粮商来了怎么办?”“闹个屁。”三叔公的声音透着狠,“她那条腿,
能爬到蛇洞就不错了。找到她直接敲晕,扔进去了事。”“那老哑巴呢?刚才我打她的时候,
她眼睛瞪得跟要吃人似的。”“一个哑巴,能翻出什么浪?”三叔公啐了一口,
“等明天换了粮食,就说她偷粮食跑了,让村里的人去搜山,正好让狼把她叼走。
”火把的光越来越远。我趴在草里,浑身的血都在烧。原来他们不仅要我的命,
连哑婆婆都不放过。原来所谓的献祭,根本就是和粮商勾结的骗局。攥着哑婆婆给的石片,
边缘割得掌心渗出血来。血珠滴在草叶上,很快被露水冲淡。缓了半个时辰,
估摸着他们走远了,才敢再动。腿已经肿得像根发面馒头,稍微动一下,
骨头缝里就发出咯吱的响声。必须找个地方躲起来。抬头看见前面有棵老槐树,
树洞里能**。是阿蛮的记忆里的地方,她小时候常去那儿掏鸟蛋。挪到树洞前,
发现里面铺着干草,像是有人经常来。刚钻进去,就摸到一堆软软的东西。借着月光一看,
是几件破衣裳,还有个布包。打开布包,里面是半块饼,还有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
纸上的字歪歪扭扭,像是用炭条写的:二十年前,献祭的是我闺女。他们说她是蛇王妻,
其实是被他们推下山崖摔死的。因为她撞见三叔公偷卖公粮。今年轮到阿蛮,
我不能再让他们得逞。蛇洞后崖有个山洞,能通到山外。别信他们的鬼话,快跑。
字到最后越来越乱,墨迹晕成了一团,像是写字的人手在抖。是哑婆婆写的。
原来她不是哑巴。她是不敢说话,怕被三叔公他们发现。树洞里突然传来沙沙的响。
我猛地攥紧石片,心脏差点跳出来。一只手从洞口伸进来,手里拿着个野果。是哑婆婆!
她脸上还有巴掌印,嘴角带着血,看见我,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别出声。
”她的声音嘶哑得像破锣,“他们在山下搜,一时半会儿找不到这儿。”我把纸递还给她,
她却摇了摇头:“你得知道真相。”“他们为什么要选我?”我咬着牙问,
断腿的疼让我说话都在抖。“因为你爹娘。”哑婆婆抹了把泪,“你爹娘活着的时候,
知道他们偷卖公粮的事,被他们害死了。他们怕你长大报仇,正好老巫说你是天选蛇妻,
就顺水推舟,想把你也弄死。”原来阿蛮的爹娘不是病死的。原来这一家人,
从头到尾都在演戏。哑婆婆突然抓住我的手,往我手里塞了个东西。是把钥匙。
“柴房隔壁的锁,能打开。”她压低声音,“我刚才听见他们说,明天一早粮商就来,
要在蛇洞前验货。他们准备把你扔进去后,就说蛇王显灵,赏了粮食,好让村里人信他们。
”“那你怎么办?”我看着她脸上的伤,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着。“我自有办法。
”她笑了笑,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你快走吧,顺着后山的路,到了山洞就能出去。
别回头,也别惦记我。”说完,她不等我说话,转身就往山下走,故意踩得树枝沙沙响,
像是在引开什么人。我攥着钥匙,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树林里。
突然听见山下传来三叔公的吼声:“抓住那个老东西!肯定是她把那丫头藏起来了!
”接着是哑婆婆的尖叫,还有棍子打人的声音。我咬碎了牙,从树洞里爬出来。
往山下跑了两步,又猛地停住。我不能走。哑婆婆为了救我,把自己搭进去了。
我要是就这么跑了,和三叔公他们有什么区别?摸了摸断腿,疼得钻心。但心里的火更旺。
三叔公,二伯娘。你们不是想让我当蛇王妻吗?明天,我就去蛇洞。但不是去送死。
是去送你们下地狱。把布包里的饼几口吞下去,又把野果揣进怀里。哑婆婆说得对,
我得活着。活着才有机会报仇。拖着断腿往蛇洞的方向挪,月光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
树洞里的破衣裳被我翻了出来,裹在身上挡挡寒气。摸到衣裳口袋里有个硬东西,
掏出来一看,是个哨子。是阿蛮小时候吹的那种。突然想起来,阿蛮的记忆里,这哨子一吹,
后山的野鸡就会叫。不知道为什么,但现在或许能用上。离蛇洞还有半里地的时候,
听见前面有说话声。是三叔公和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明天一早,你带两车粮食过来,
摆在蛇洞前。”三叔公的声音透着谄媚,“村里人看到了,就会信蛇王显灵,
以后我们说什么,他们都得听。”“那丫头呢?”陌生男人的声音很粗,“别出什么岔子,
我可不想惹麻烦。”“放心,”三叔公冷笑,“今晚就算她跑了,我也能把她找回来。
一条断腿的丫头,还能翻天不成?”“最好是这样。”陌生男人哼了一声,“事成之后,
之前说好的三成利,可不能少。”“少不了你的,王老板。”原来那个粮商姓王。
原来他们早就串通好了。我躲在石头后面,看着那个叫王老板的男人带着两个伙计往山下走。
三叔公站在原地,掏出烟袋锅,火光在黑暗里一明一灭。他往蛇洞的方向看了一眼,
阴沉沉地笑了:“明天,就该清算了。”我握紧了手里的石片和哨子。清算?等着吧。
明天清算的,是你们的命。天快亮的时候,我摸到了蛇洞附近。蛇洞前有块平地,
三叔公他们应该是打算明天在这里摆粮食。找了个隐蔽的石缝躲进去,能看见蛇洞的入口,
也能看见山下的动静。断腿已经麻木了,疼得不那么厉害,只是一阵阵发沉。啃了口野果,
酸得牙都快掉了。山下传来鸡叫声。天要亮了。很快,就能看见三叔公他们的嘴脸了。
也能看见,哑婆婆怎么样了。突然听见蛇洞那边有动静。是脚步声,不止一个人。
我赶紧往石缝里缩了缩,从缝隙里往外看。是三叔公和二伯娘,还有两个村里的壮汉。
他们抬着个麻袋,往蛇洞那边走。麻袋里鼓鼓囊囊的,还在动。“快点,王老板的人快到了。
”二伯娘催着,声音里透着急,“把这老东西扔进去,就说她想偷粮食献给蛇王,
被蛇王吃了。”麻袋里传来呜咽的声,像是有人被堵住了嘴。是哑婆婆!我眼前一黑,
差点从石缝里滚出去。攥着石片的手,指节都捏白了。三叔公他们把麻袋往蛇洞门口一扔,
解开绳子。哑婆婆滚了出来,被堵住嘴,手脚都被捆着,看见他们,眼睛瞪得像要裂开。
“老东西,别怪我们。”三叔公踢了踢麻袋,“要怪就怪你多管闲事。
”二伯娘往哑婆婆身上吐了口唾沫:“等会儿王老板来了,就说这是蛇王嫌祭品不够,
把你拖来凑数的。”就在这时,山下传来了马蹄声。王老板来了。三叔公立刻换了副嘴脸,
脸上堆着笑,迎了上去:“王老板,您可来了!快请,蛇洞这边都准备好了。
”一个穿着绸缎衣裳的胖男人下了马,身后跟着几个扛着粮食袋的伙计。“人呢?
”王老板眯着眼,往蛇洞那边瞟。“在洞里呢,”二伯娘笑着说,“蛇王昨晚就接走了,
您看,这是蛇王赏的粮食。”她指了指伙计扛来的粮食袋,眼里的贪婪藏都藏不住。
王老板往粮食袋里摸了一把,冷笑一声:“老三,你这戏演得不错啊。
”三叔公的脸一下子僵了:“王老板,您这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王老板从怀里掏出张纸,扔在三叔公脸上,“这是县里发来的告示,
说有人举报你偷卖公粮,贪赃枉法。我要是把粮食给你,不等于跟你一起犯法?
”三叔公的脸瞬间惨白如纸。二伯娘也慌了:“王老板,您别听人瞎说,
我们没有……”“没有?”王老板指了指被捆着的哑婆婆,“那她是谁?刚才我在山下,
听见她喊救命,说你们杀了她闺女,还要杀这个叫阿蛮的丫头。
”三叔公突然从腰里掏出把刀,指着王老板:“你敢坏我的事?”“就凭你?
”王老板身后的伙计立刻掏出棍子,围了上来。我看着石缝外乱糟糟的场面,突然明白了。
哑婆婆昨晚不是被他们抓住的。她是故意被抓住,好等王老板来的时候,喊救命。
她早就知道王老板今天会来,也知道县里在查三叔公。可三叔公手里有刀。哑婆婆还被捆着。
我摸了摸口袋里的哨子,又看了看手里的石片。断腿的地方突然不那么疼了。深吸一口气,
从石缝里爬了出来。现在,该轮到我了。我吹了声哨子。不是那种清亮的,
是用尽力气攥紧哨子,往死里吹的那种。声音又尖又哑,像被踩住尾巴的猫。
后山的野鸡突然炸了窝。扑棱棱的翅膀声从四面八方涌来,带着尖利的鸣叫,直往人脸上撞。
王老板的伙计们慌了神,举着棍子乱挥。三叔公手里的刀也砍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