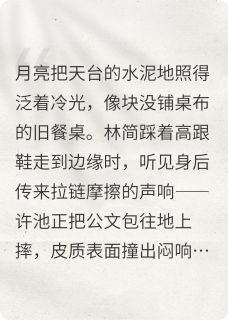月亮把天台的水泥地照得泛着冷光,像块没铺桌布的旧餐桌。林简踩着高跟鞋走到边缘时,
听见身后传来拉链摩擦的声响——许池正把公文包往地上摔,皮质表面撞出闷响,
像谁在远处敲了下鼓。没人说话。风卷着楼下的车流声漫上来,林简拢了拢风衣下摆,
指甲在栏杆上划出细响。她计算过角度,从这里坠落的自由落体时间是3.7秒,
足够忽略掉落地前那声可能不太体面的惊叫。“让让。”许池的声音裹着烟味飘过来,
他没看她,径直往栏杆中间挤,公文包里掉出的工牌在月光里翻了个身,
照片上的人笑得比现在鲜活三倍。林简往旁边挪了半步,高跟鞋跟卡在地砖缝里,
发出刺耳的刮擦声。“左移二十公分,”她开口时,自己都惊讶于语气里的冷静,
“那里的栏杆锈得最厉害,省力气。”许池果然顿了顿,真的往左挪了挪。
他摸出手机看了眼时间,屏幕光映出他眼下的青黑。“十点十七分,”他像是在对自己说,
“这个点跳下去,明天的早会正好能少开半小时。”林简没接话,只是低头解鞋跟。
金属跟卡得很深,她用了点力,指尖突然触到冰凉的栏杆——许池的手正搭在旁边,
骨节突出,虎口处有道新添的划伤,像被文件边缘割的。两人同时缩回手,
像碰着了什么烫人的东西。月亮从云里钻出来,把两道影子钉在天台上,瘦长,摇晃,
像两根随时会断的晾衣绳。许池刚把半个身子探过栏杆,
天台入口突然传来哐当巨响——铁门被风撞开,卷着堆废弃的广告牌砸过来。
他下意识往回躲,胳膊肘正撞在林简肩上,她本就没站稳,高跟鞋跟又卡在砖缝里,
整个人突然往栏杆外倒去。“操。”许池的骂声混着风声砸过来,
他几乎是凭着本能拽住她的风衣后领。布料撕裂的声音在夜里格外刺耳,
林简悬空的那只手胡乱抓着,指甲深深抠进他虎口的伤口里。血珠渗出来,滴在她风衣下摆。
许池闷哼一声,另一只手死死攥住栏杆,锈迹蹭在掌心,像撒了把沙。
“**……”他想说什么,却看见林简垂着的眼睛突然抬起来,月光落在她瞳孔里,
空得像口井。广告牌还在地上滚,发出铁皮摩擦的尖啸。林简终于找回力气,
用鞋跟蹬着墙面往外挣:“松开。”她的声音很平,像在讨论天气,“你耽误我时间了。
”“神经病。”许池反而拽得更紧,伤口被扯得生疼,“要跳也等我完事,别占地方。
”他猛地发力把她拽回来,两人一起摔在水泥地上,公文包被压得变形,
里面的文件散落一地,飘起张诊断书,边角被风吹得打旋。林简盯着那张纸,突然笑了声,
笑声里带着点喘。许池爬起来拍掉身上的灰,
看见她正用手指戳着诊断书上的“重度抑郁”四个字:“巧了,我这儿也有一张。
”她从风衣口袋里摸出张折叠的纸,展开时,许池看见“脑胶质瘤晚期”几个字,
被折痕压得变了形。风把广告牌吹到栏杆边,发出单调的撞击声。
许池突然觉得虎口的伤没那么疼了,他捡起地上的公文包,从里面摸出半盒皱巴巴的烟,
抖出两根,递了一根给林简。“不抽。”她别过脸,却没拒绝他把烟塞到她手里。
许池自己点燃一根,尼古丁混着铁锈味钻进喉咙。他看着林简手里那根没点燃的烟,
突然觉得有点荒谬——刚才还想互相抢着去死的人,现在正并排坐在地上,
听着块破铁皮撞栏杆的声音,像在等什么开场信号。“那什么,”他吸了口烟,
“你刚才……摔下去了吗?”林简没理他,只是把那根烟折成两段,扔进风里。
烟蒂在地上碾出火星时,许池突然盯着林简的高跟鞋出神。那鞋跟卡得太深,
金属边缘已经变了形,像只折了翅膀的蝴蝶。他没说话,蹲下去伸手去抠砖缝里的鞋跟,
指尖触到冰凉的金属,
想起自己公文包里还有支没用完的润滑油——上次修自行车时顺手塞的。“别动。
”林简的声音带着警惕,却没真的推开他。许池从包里翻出润滑油,往砖缝里挤了点,
再用力一拔,鞋跟终于松了。他把鞋子扔给她,掌心沾着黑褐色的锈,
混着刚才没擦干净的血。“你这样走回去?”他指了指她手里那只没跟的鞋,“脚踝会肿。
”林简没接鞋,只是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光脚踩在水泥地上,凉意顺着脚底往上爬,
她突然想起医生说的,肿瘤压迫神经后,可能连路都走不了。“我家就在附近。
”许池突然开口,声音比刚才软了点,“有备用的拖鞋,还有消毒水。
”他指了指自己虎口的伤,“你总不能让我带着这道口子跳下去,像被谁谋杀的。
”林简抬眼看他,月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公文包上的污渍在地上洇出片模糊的黑。
她想起自己的诊断书,想起医生说最多还有三个月,突然觉得去谁家借双拖鞋,
好像也没什么意义。“不去。”她捡起那只坏了的鞋,往栏杆那边走。“喂。
”许池拽住她的手腕,力道不重,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持,“脑胶质瘤……很疼吧?
”他没等她回答,自顾自地说,“我以前邻居家的老头得过,疼得整夜撞墙。
他家冰箱里总囤着冰袋,说敷着能好受点。”林简的脚步顿住了。“我家冰箱里有冰袋。
”许池的声音有点干,“还有止疼药,不是处方药,上次头疼剩的。”他松开手,
往后退了半步,像怕吓着她,“就……借用半小时,处理下伤口,换双鞋。你要是还想跳,
我不拦着,算我耽误你时间了。”风把铁皮广告牌吹得吱呀响,
许池看见林简攥着鞋的手指动了动,骨节泛白。她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只是转过身,
光脚往天台入口走,步调有点瘸。许池赶紧跟上,走在她身后半步的位置,像在护着什么。
他突然觉得,刚才那半小时的“早会”好像也没那么重要了,至少,
得先看着这姑娘把鞋换上。至于之后的事……他摸了摸口袋里的诊断书,纸边硌得慌,
像张没写完的遗书。“对了,”快到楼梯口时,他没话找话,“你……晚饭吃了吗?
我家还有包没开封的速冻饺子。”林简的背影僵了僵,过了好一会儿,
才从喉咙里挤出个单音节:“嗯。”许池的脚步轻快了点,夜风里好像都带上点饺子的热气。
他没问她的名字,也没说自己是谁,只觉得这栋楼的楼梯,好像比上来时短了不少。
楼梯间的声控灯随着脚步亮了又灭,昏黄的光在两人脸上短暂停留,又坠入更深的暗。
林简光脚踩在台阶上,每一步都带着轻微的踉跄,许池跟在后面,公文包偶尔撞在栏杆上,
发出闷响。到了三楼,许池掏出钥匙开门,门轴发出刺耳的吱呀声。屋里没开灯,
月光从阳台钻进来,在地板上投出块菱形的亮斑,能看见沙发上堆着件皱巴巴的西装,
茶几上摆着个空酒瓶。“随便坐。”许池摸黑打开冰箱,冷气“嘶”地涌出来,
他拿出冰袋和消毒水,又从鞋柜最底层翻出双粉色的女士拖鞋,“前租客落下的,没穿过。
”林简没动,就站在玄关,手里还攥着那只断了跟的高跟鞋。金属鞋跟在月光下泛着冷光,
像枚没**的碎片。许池把东西往茶几上一放,自己先拖了把椅子坐下,
撕开消毒水的包装。酒精味瞬间漫开,他倒了点在掌心,往虎口的伤口上抹,疼得嘶了声,
却没皱眉头。“你脚踝都红了。”他抬眼瞥她,“真打算拖着条残腿跳下去?
”林简终于有了反应,低头看了眼脚踝,那里确实肿起块淡红色。她没说话,
弯腰把高跟鞋往鞋柜边一扔,声音很轻,像怕惊扰了什么。“冰袋敷十分钟。
”许池把冰袋推过去,自己又去翻药盒,“止疼药吃两颗,管六小时。”林简拿起冰袋,
没往脚踝上放,反而贴在了自己太阳穴上。冰得皮肤发紧,她却慢慢眯起眼,
像在享受这份刺痛。“你邻居老头,最后是自己撞墙死的?”她突然开口,声音有点哑。
“不是。”许池数出两颗白色药片,“儿子接去医院了,死在病床上。据说最后那几天,
连撞墙的力气都没了。”他顿了顿,把药片放在桌上,“比起来,跳天台算体面的。
”林简笑了声,很轻,像冰裂的声音。“你呢?为什么选今天?”“公司破产了。
”许池说得干脆,“早上收到法院传票,下午发现合伙人卷走了最后一笔钱。
想想也没什么意思,反正孤身一人,早死晚死都一样。”他指了指茶几上的空酒瓶,
“本来想喝晕了再上去,结果酒不够烈。”林简没接话,拿起那双粉色拖鞋穿上,
尺码有点大,走一步晃一下。她走到沙发边坐下,冰袋从太阳穴移到脚踝,
冰凉的触感让她轻轻吸了口气。“我预约了下周三的住院。”她突然说,“医生说要开颅,
成功率三成。我不想躺手术台上,像块肉一样被人切来切去。”许池正往伤口上贴创可贴,
闻言动作顿了顿,没回头。“三成确实低。”他说,“但总比现在就死强。”“强在哪里?
”林简反问,“多疼几天?还是看他们同情我?”她拿起桌上的止疼药,对着月光看了看,
“我爸走的时候,就躺在我现在坐的这个位置,疼得直哼哼,我妈守在旁边哭,
他却瞪着天花板笑,说终于能解脱了。”许池贴完创可贴,站起身去厨房,
过了会儿端出两碗速冻饺子,用的是微波炉加热,皮有点硬。“吃点吧。”他把一碗推给她,
“死也别做饿死鬼。”林简没动筷子,只是看着碗里的饺子。月光落在她脸上,
能看见她眼角的细纹,明明才二十多岁,却像熬了无数个夜。“你公文包里,
除了润滑油和诊断书,还有什么?”她突然问。许池拿筷子的手顿了下,随即笑了。
“你看见了?”“刚才你蹲下去的时候,露出来了。”林简说,“肺癌晚期,对吧?
诊断书边角都磨卷了,揣了很久?”许池没否认,夹起个饺子塞进嘴里,皮硬得硌牙。
“比你好点,医生说还能活半年。”他嚼着饺子,声音有点含糊,“但疼起来也够呛,
上周咳血,染红了半张床单,看着烦。”两人突然都没了话,只有窗外的风声,
还有偶尔从远处传来的汽车鸣笛。饺子在碗里慢慢变凉,
像两人心里那点刚冒头就被掐灭的暖意。“再去天台看看?”许池突然开口,
把剩下的饺子倒进垃圾桶,“现在风大,跳下去应该很快。”林简站起身,
粉色拖鞋在地板上发出“啪嗒”声。她走到玄关,没拿那只高跟鞋,也没脱拖鞋。“走吧。
”许池抓起公文包,跟在她身后。关门前,他回头看了眼茶几,那两颗白色药片还躺在那里,
在月光下像两粒冰冷的星。楼梯间的声控灯又开始随着脚步亮灭,这次两人走得都很稳,
没有谁再踉跄。快到天台门口时,林简突然停下,回头看他。“你说,
要是我们今天都没死成,明天该怎么办?”许池想了想,
从公文包里掏出那瓶没喝完的润滑油,往手心倒了点,搓了搓。“不知道。”他说,
“也许去医院排队,也许找个地方再喝瓶酒。”他抬头看她,眼睛在暗处亮得惊人,
“但至少,不用穿着不合脚的拖鞋走楼梯了。”林简笑了,这次的笑声很清楚,
像风吹过天台的栏杆。她推开门,夜风瞬间涌过来,带着城市的烟火气。“那就先活着吧。
”她说,“看看明天的太阳,是不是比今天的月亮更刺眼。”许池跟在她身后,走到栏杆边,
没再提跳下去的事。他掏出烟盒,发现里面只剩最后一根烟,递给她。林简接过去,
夹在指间,没点燃。风把两人的影子吹得摇晃,像两片随时会被卷走的叶子。但这一次,
没有谁再往前迈一步。烟蒂在指间转了半圈,林简突然想起什么,
从西装口袋里摸出个皱巴巴的打火机。火苗“噌”地窜起来,在风里抖得像条垂死的虫子。
她没点烟,就那么举着,看着橘红色的火舌舔舐夜空。“你打火机该灌气了。
”许池的声音混在风里,有点飘忽。他靠在栏杆上,公文包滑落在脚边,露出半截诊断书。
刚才没注意,封面上印着的医院名称,居然和林简预约手术的是同一家。林简“嗯”了声,
把打火机塞回他手里。金属外壳沾了点她的体温,许池捏着,
突然觉得掌心那道刚结痂的伤口有点痒。“其实三成成功率不算低。
”他低头蹭了蹭鞋底的灰,“我认识个脑科医生,以前帮过我忙,要不要……”“不用。
”林简打断他,语气平淡得像在说天气,“我怕疼。”许池没再劝。他掏出自己的打火机,
“啪”地点燃那根烟,烟圈在风里散得极快。“我倒是不怕疼,”他吸了口烟,喉结动了动,
“就是烦。咳血的时候,总觉得肺里像塞了团烂棉花,堵得慌。”林简转头看他,
月光刚好落在他侧脸,能看见胡茬青黑的轮廓。她突然想起刚才在他家,他弯腰倒饺子时,
后颈露出的那块皮肤,有颗很小的痣。“你咳血的时候,一个人?”“不然呢。
”许池笑了笑,烟蒂的火星在黑暗里明灭,“总不能拉着合伙人哭吧?他卷我钱的时候,
可没手软。”风突然变大,吹得林简的头发贴在脸颊上。她抬手捋头发,
指尖触到冰凉的耳垂,才发现自己没戴耳环。早上出门时明明戴着的,
大概是在天台栏杆上蹭掉了。那是对银质的蝴蝶耳环,去年生日买的,现在想起来,
倒和那只断了跟的鞋有点像。“冷吗?”许池脱下西装外套递过来,袖口沾着点油渍。
“别感冒了,死前还得遭场罪,不值当。”林简没接,却往他那边挪了半步。
外套上有淡淡的烟味和消毒水味,奇怪的是,并不难闻。“你那瓶润滑油,”她突然说,
“下次修自行车记得用完,别再塞包里发霉。”许池愣了下,随即笑出声。
“你怎么知道我会修自行车?”“公文包侧袋露着半截扳手。”林简瞥了眼他脚边的包,
“而且你刚才拔鞋跟的手法,像经常跟螺丝打交道的。”他还真没注意。
许池弯腰把公文包拎起来,拍了拍上面的灰。“以前穷的时候,靠修车赚过学费。
”他顿了顿,突然觉得这话有点多余,像在解释什么。林简没接话,只是望着远处的霓虹灯。
有盏灯忽明忽暗,像只眨着的眼睛。“我爸走的那天,也有这么大的风。”她轻声说,
“我妈抱着他哭,他却抓着我的手,说想吃巷口那家的馄饨。
其实他那时候已经咽不下东西了,就是……”就是想找个由头,让她出去透透气。
这句话她没说,许池却好像懂了。他掐灭烟蒂,往楼下弹了弹,火星坠下去,像颗流星。
“明天早上,我带你去吃馄饨?”他说得随意,像在约客户谈生意,“巷口那家,六点开门。
”林简转头看他,眼睛在黑暗里亮得惊人。她沉默了几秒,突然抬脚往楼梯口走,
粉色拖鞋在地上发出“啪嗒”声。“走了。”“哎?”许池赶紧跟上,“馄饨……”“去。
”林简的声音从前面传来,带着点不易察觉的笑意,“但我不吃香菜,
你跟老板说的时候别忘了。”他还真记住了。许池快步追上她,跟她并排走在楼梯间,
声控灯随着脚步一层层亮起来。他突然发现,林简走路时,左脚落地比右脚轻一点,
大概是脚踝还疼。到三楼门口时,林简停下脚步。“我家在七楼。”她指了指楼上,
“明天六点,你在楼下等我?”“嗯。”许池点头,突然想起什么,
从公文包里翻出个东西递给她。是颗用纸巾包着的纽扣,黑色的,塑料质地。
“刚才在你头发上发现的,大概是蹭到我外套上的。”林简接过来,捏在手里。
纽扣边缘有点毛糙,像是从旧衣服上扯下来的。“你的西装该补补了。”她说。
“等你做完手术,帮我补?”许池脱口而出,说完又觉得不妥,刚想改口,
却听见林简说:“好啊。”声控灯突然灭了,楼梯间陷入一片黑暗。两人都没说话,
只听见彼此的呼吸声,还有窗外隐约的风声。过了几秒,许池摸索着按下楼道的灯,
昏黄的光重新亮起时,看见林简正低头看着手里的纽扣,嘴角好像有点弯。“上去吧。
”他往后退了半步,“明天见。”“明天见。”林简转身往楼上走,
粉色拖鞋的“啪嗒”声渐渐远了。走到四楼时,她回头往下看,许池还站在门口,
手里攥着那件没送出去的西装外套,像尊沉默的影子。许池等那脚步声彻底消失,
才掏出钥匙开门。屋里还是黑着,他没开灯,径直走到冰箱前,打开门。冷气涌出来的瞬间,
他盯着那盒速冻饺子的空盒子,突然笑了。明天得早点起,去巷口买馄饨,
还要记得跟老板说,不要香菜。他关冰箱门时,手指碰到了什么,低头一看,
是那两颗没吃的止疼药。刚才忘在冰箱上了。许池把药片捡起来,放进药盒里,突然觉得,
其实疼一点也没那么难熬。至少,比一个人在天台吹冷风强。清晨五点半,
楼下的梧桐树影还浸在蓝灰色的雾里,许池已经站在单元门口了。他换了件干净的衬衫,
袖口熨得笔直,手里攥着个牛皮纸包,里面是从隔壁早餐铺买的热豆浆,还温着。
楼梯间传来“啪嗒”声,林简穿着件米白色的风衣走下来,脚上是双平底鞋,
脚踝处隐约能看见贴了块纱布。“没迟到。”她走到他面前,目光扫过他手里的豆浆,
“你倒比闹钟还准时。”“怕你反悔。”许池把豆浆递过去,指尖不小心碰到她的手,
像被烫了似的缩回来,“馄饨摊得等老板生火,先垫垫。”林简咬着吸管,
看着他耳根泛起的红,突然想起昨晚他后颈那颗痣。“许池,”她吸了口豆浆,
甜腻的暖流漫过喉咙,“我想好了。”他脚步顿了顿,没回头,声音却绷紧了:“嗯?
”“去见你认识的那个医生。”林简走到他前面,转过身倒着走,风衣下摆扫过地面的露水,
“但你得答应我件事。”许池的眼睛亮起来,像被晨光镀了层金:“你说。”“看完医生,
带我去游乐园。”林简停下脚步,认真地看着他,“要坐过山车,吃棉花糖,
还要拍那种印着卡通图案的拍立得。”她顿了顿,补充道,“我长这么大,还没去过。
”许池愣了愣。他以为她会提钱,或者别的什么实际的要求,却没想到是游乐园。
他喉结动了动,突然想起自己公文包里那张皱巴巴的诊断书——医生说他肺功能正在恶化,
剧烈运动可能会引发窒息。“怎么,不敢?”林简挑眉,嘴角带着点促狭的笑,
“还是觉得跟我这个快死的人去游乐园,太晦气?”“不是。”许池赶紧摇头,
从口袋里摸出个东西递给她。是颗水果糖,橘子味的,糖纸在晨光里闪着亮。
“小时候我妈带我去公园,每次都买这个。”他有点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游乐园……我也没去过,怕到时候找不着路。”林简接过糖,捏在手心。
糖纸被体温焐得发皱,她却突然笑了,像晨雾里绽开的花。“那正好,两个土包子,
谁也别笑话谁。”去医院的路上,公交车摇摇晃晃的。林简靠在车窗上,
看着外面掠过的街景,突然说:“其实我不怕手术了。”许池正在给脑科医生发消息,
闻言手指顿了顿。“嗯?”“昨天在你家,我看见冰箱上贴着张便签,”林简轻声说,
“上面写着‘周三记得买牛奶’。”她转头看他,眼睛亮得惊人,
“你明明自己都没多少日子了,还想着买牛奶,说明……你也不是真的想死,对吧?
”许池没说话。那张便签是上周写的,那天他咳得厉害,以为撑不过晚上,
却还是习惯性地记下要做的事。原来人在绝望的时候,还是会下意识地给明天留点念想。
医生办公室里,白大褂的味道呛得人发闷。林简坐在椅子上,手指紧张地抠着风衣的纽扣,
许池站在她身后半步的位置,像根定海神针。“三成成功率是保守估计。”医生推了推眼镜,
指着片子上的阴影,“位置虽然刁钻,但林**年轻,恢复能力强,
我们可以试试新的靶向药辅助……”林简没怎么听,
注意力全在许池的手背上——他大概是太紧张,指节都捏白了,虎口那道新伤又裂开了点,
渗出血珠。她悄悄从口袋里摸出片创可贴,趁医生转身翻病历的功夫,往他手背上一贴。
动作很快,像只掠过的蝴蝶。许池浑身一僵,低头看手背上那片印着小熊图案的创可贴,
突然觉得喉咙发紧。他偏过头,看见林简正望着窗外,阳光落在她侧脸,
绒毛都看得清清楚楚。从医院出来时,天已经大亮了。林简手里攥着张缴费单,捏得发皱。
“医生说下周一住院。”她声音很轻,“手术定在周三。”“嗯。”许池点头,
从包里掏出瓶水递给她,“要不要先去吃点东西?我知道有家面馆,味道……”“去游乐园。
”林简打断他,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坚持,“现在就去。”许池没再反对。他拦了辆出租车,
报出游乐园的名字时,司机看他们的眼神有点奇怪——一个穿着风衣,
面色苍白;一个衬衫袖口沾着点血,两人却笑得像要去赴什么盛大的宴会。
过山车冲下来的时候,林简尖叫着抓住了许池的手。风灌进喉咙,疼得像要裂开,
她却笑得眼泪都出来了。许池的脸色有点白,呼吸也乱了,但他没松开手,反而握得更紧了。
棉花糖甜得发腻,粘在嘴角。林简伸出舌头去舔,许池从口袋里掏出纸巾,笨拙地帮她擦掉。
指尖触到她的皮肤,像触电似的缩回来,却被林简一把按住。“别动。”她仰头看着他,
阳光透过棉花糖的缝隙落在她脸上,毛茸茸的,“拍立得呢?不是说要拍照吗?
”拍立得的闪光灯亮起来时,许池下意识地往她那边靠了靠。照片洗出来,
两个人的脸都有点模糊,却笑得格外清楚。林简把照片揣进风衣口袋,像藏了个秘密。
夕阳西下的时候,他们坐在摩天轮的轿厢里。城市的灯火像撒了一地的星星,
林简靠在许池的肩膀上,声音轻得像叹息:“如果手术失败了,你把这张照片烧给我,
好不好?”许池的肩膀僵了僵,从口袋里掏出个东西递给她。是枚银质的蝴蝶耳环,
和她丢的那只一模一样,只是边角有点磨损。“昨天在天台栏杆上捡的。”他声音有点哑,
“本来想等你手术成功了,再给你。”林简接过耳环,指尖抖得厉害。她想戴上,
却怎么也扣不上,最后还是许池替她戴上的。他的手指很稳,动作却很轻,
像在对待稀世珍宝。摩天轮升到最高点时,林简突然凑过去,在他脸颊上轻轻吻了一下。
像羽毛落在湖面,漾开一圈圈涟漪。“许池,”她轻声说,“如果我活下来了,
我们就去学骑自行车,你教我。”许池没说话,只是把她搂得更紧了。他能感觉到她在发抖,
不是因为冷,是因为害怕。他从口袋里摸出那颗橘子糖,剥开糖纸喂到她嘴里。
甜味在舌尖漫开,林简突然哭了。不是嚎啕大哭,是无声的流泪,眼泪打在他的衬衫上,
洇出一小片深色的痕。“别哭。”许池笨拙地拍着她的背,声音哽咽,
“棉花糖都被你哭成咸的了。”林简没理他,只是把脸埋在他胸口,听着他有力的心跳。
原来活着的感觉,是这么具体的——有温度,有声音,还有橘子糖的甜味。摩天轮慢慢降下,
像个即将结束的梦。林简攥着那张拍立得,照片上的两个人笑得傻气,却闪着光。
她突然想起许池说过的话,人在绝望的时候,总会下意识地给明天留点念想。或许,
她的念想,就是他手心的温度,和这张有点模糊的照片。至于明天会怎样,谁知道呢。
至少现在,他们还有彼此,还有一整个晚上的时间,可以慢慢等天亮。秋老虎肆虐的午后,
许池蹲在修车行门口,手里的扳手转得飞快。汗水顺着下颌线往下掉,
砸在满是油污的工装裤上,洇出深色的痕。手机在裤兜里震动,他腾出沾满黑油的手摸出来,
是林简发来的照片——住院部楼下的梧桐树,叶子开始泛黄了。“下周三生日,想要什么?
”对话框里跳出一行字。许池咬着牙拧下最后一颗螺丝,指节因为用力泛白。
合伙人卷走的钱像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医院催缴的手术费通知单更是每天都在眼前晃。
他想打“什么都不用”,指尖悬在屏幕上半天,最终只回了个“随便”。生日那天,
许池收工比平时早。他站在服装店门口,看着橱窗里那条银质的月亮项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