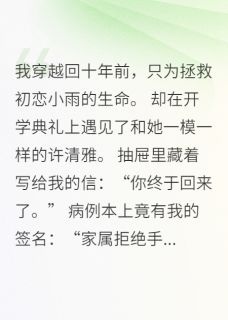混乱中,一支放在桌角的、看起来很旧的黑色钢笔被震得滚落下来,骨碌碌地滚过桌面,然后“啪嗒”一声,掉在我的脚边。
我的目光,下意识地被那支笔吸引了过去。
它静静地躺在冰冷的地面上,距离我右脚只有几厘米。黑色的笔身磨得有些发亮,显然用了很久。吸引我目光的,是笔帽顶端。那里,似乎刻着什么。
我弯腰,几乎是机械地,捡起了那支笔。
指尖触碰到笔帽冰凉的金属表面。我把它举到眼前,借着惨白的荧光灯光仔细看去。
笔帽顶端,刻着两个小小的字母。
不是印刷体,是手刻的,带着一种笨拙却认真的笔触。
XY&QM
XY?小雨?林小雨?!
QM?清雅?许清雅?!
我的呼吸彻底停滞了!血液仿佛在瞬间凝固,又在下一秒疯狂地逆流冲上头顶!耳边只剩下自己心脏狂跳的轰鸣和尖锐的耳鸣!小雨……清雅……她们的名字,为什么会刻在同一支笔上?!这支笔,为什么会在许清雅这里?!
这代表着什么?!她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还给我!”许清雅带着哭腔的嘶喊再次响起,带着一种被彻底逼入绝境的绝望。她不顾地上的水和玻璃碎片,赤着脚(刚才慌乱中似乎踢掉了鞋子)就要冲过来抢夺那支笔。
但她的脚步猛地顿住。
因为就在她扑过来的瞬间,一阵剧烈的、撕心裂肺的咳嗽毫无预兆地从她喉咙深处爆发出来!那咳嗽来得如此凶猛,如此剧烈,仿佛要把整个肺都咳出来!
“咳咳!咳!咳咳咳——!”
她猛地弯下腰,双手死死地捂住嘴,单薄的身体在剧烈的咳嗽中痛苦地痉挛、颤抖,像风中一片即将凋零的枯叶。惨白的灯光下,她瘦削的脊背弓起,每一次剧烈的呛咳都牵动着全身,显得那么脆弱,那么不堪一击。
“清雅!”我失声惊呼,所有的震惊、疑惑、恐惧在看到她痛苦模样的瞬间都被巨大的恐慌淹没。我扔掉那支该死的笔和那张更该死的体检单,一步跨过地上的玻璃碎片和水渍,冲到她身边,下意识地伸出手,想要扶住她。
“别……咳……别碰我……”她挣扎着,试图推开我,声音断断续续,破碎不堪。
但她咳得太厉害了,整个人已经完全失去了力气,身体软得像一摊泥,根本支撑不住。她的身体猛地向前一倾,眼看就要栽倒在地上那片尖锐的玻璃碎片里!
“小心!”我再也顾不得她的推拒,双臂猛地用力,将她颤抖的身体紧紧揽入怀中!
她的身体很轻,很单薄,隔着薄薄的卫衣,能清晰地感觉到她骨头的轮廓。她在我怀里剧烈地咳嗽着,每一次震动都清晰地传递到我身上。一股浓烈的、带着铁锈般的腥甜气息猛地冲入我的鼻腔!
我的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狠狠攥住!
“清雅!你……”我惊恐地低头看向她捂在嘴上的手。
她的手指用力地蜷缩着,指缝间,赫然渗出了刺目的、粘稠的鲜红!
血!
像是最艳丽的罂粟,在她苍白如纸的手指间晕染开,触目惊心!一滴,两滴……滚烫地滴落在她浅蓝色的卫衣前襟,迅速洇开一小片暗色的、不祥的印记。
“不……”她似乎也看到了指缝间的血,身体猛地一僵,咳嗽奇迹般地短暂停歇了片刻。她抬起沾满血污的手,难以置信地看着,那双清澈的杏核眼里,最后一丝光芒如同风中残烛,迅速地被巨大的、无法言喻的恐惧和绝望吞噬。她抬起头看向我,眼神空洞得可怕,嘴唇翕动着,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然后,她的身体彻底软了下去,所有的力气仿佛都被那几滴血抽走了。只剩下细微的、痛苦的喘息。
“清雅!”我紧紧抱着她瘫软的身体,声音嘶哑得变了调。那刺目的红灼烧着我的眼睛,像地狱的业火。恐惧像冰冷的潮水,瞬间淹没了我的头顶。我感觉到她的身体在我怀中越来越冷,越来越轻,仿佛下一秒就要消散。
“没事的……没事的……我在这里……我在……”我语无伦次地重复着,双臂收得更紧,仿佛这样就能留住她正在飞速流逝的生命力。我的脸颊紧紧贴着她冰冷汗湿的额头,鼻尖萦绕着血腥气和她发间淡淡的茉莉花香,两种气息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令人心碎的、毁灭性的气息。
温热的液体毫无预兆地从我眼眶中涌出,滚烫地滑落,滴在她的发间,混入那冰冷的汗水中。
“陈默……”她似乎感觉到了我的泪水,极其微弱地唤了一声我的名字,沾血的手指无力地动了动,似乎想抬起来,却最终只是轻轻搭在我的手臂上。她的声音微弱得像叹息,带着一种奇异的、濒临破碎的平静,“你……怎么哭了……”
她的指尖冰凉,带着血污的粘腻感。我的泪水却更加汹涌,视线完全模糊。实验室惨白的灯光,地上刺目的血迹,怀中她冰冷的触感,还有那支刻着XY&QM的旧钢笔……所有的一切都交织成一张巨大的、绝望的网,将我紧紧缠绕,勒得我几乎窒息。
巨大的恐慌和无助如同冰冷的潮水将我淹没。我抱着她,像抱着一个随时会破碎的梦。她的身体轻得不可思议,带着一种令人心慌的脆弱。那刺目的血迹还在她指缝间残留,如同烙印般灼烧着我的神经。
“别怕,清雅,别怕!”我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每一个字都带着铁锈般的腥气,“我们去医院!现在就去!”
我几乎是半拖半抱地将她扶稳,弯腰试图将她背起来。她软绵绵地伏在我背上,下巴无力地抵着我的肩膀,温热的呼吸拂过我的颈侧,却微弱得几乎感觉不到。
“不……不用……”她气若游丝地抗拒着,声音断断续续,“药……在我包里……白色的……”
药?我猛地想起她刚才的话。目光迅速扫过狼藉的桌面,在倒下的椅子旁边看到了她那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双肩包。我小心地将她放回椅子上,让她靠着实验台,然后几乎是扑过去,抓起那个背包。
手指因为恐惧而僵硬笨拙,拉链拉了好几次才拉开。里面塞满了厚重的医学教材、笔记本、笔袋、一个装着几片面包的塑料袋……我粗暴地将东西往外掏,心慌意乱地翻找着。终于,在背包内侧一个带拉链的小口袋里,摸到了一个冰凉的小塑料瓶。
掏出来一看,是一个没有任何标签的白色小药瓶,里面装着半瓶淡黄色的药片。
“这个?”我急忙把药瓶递到她眼前。
她费力地点点头,连说话的力气似乎都没有了。我颤抖着拧开瓶盖,倒出两粒药片,又冲到旁边一个水槽前,胡乱地用手接了点自来水。冰凉的水顺着指缝流下。
“张嘴,清雅!”我半跪在她面前,一手托着她的后颈,一手将药片送到她唇边。
她的嘴唇苍白干裂,微微张开。我将药片小心地放进她嘴里,又小心地喂她喝了两口水。她的喉咙艰难地滚动了一下,将药片咽了下去。整个过程,她的眼睛一直半闭着,长长的睫毛在惨白的脸上投下浓重的阴影,脆弱得像随时会折断的蝶翼。
喂完药,我依旧半跪在她面前,紧张地注视着她。时间在寂静中流淌,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实验室里只剩下几只受惊后安静下来的小白鼠偶尔发出的窸窣声,以及荧光灯管持续不断的嗡嗡低鸣。
不知过了多久,也许只有几分钟,却漫长得令人绝望。她急促而痛苦的喘息终于慢慢平复了一些,虽然依旧微弱,但不再是那种濒临窒息的撕扯。紧蹙的眉头也稍稍舒展了些许。她缓缓地、极其费力地睁开了眼睛。
那双杏核眼里,没有了之前的惊恐和绝望,只剩下一种巨大的疲惫,像暴风雨后一片狼藉的海滩。她看着我,眼神复杂得难以形容,有痛苦,有无奈,有认命,还有一丝……我读不懂的、深沉的悲伤。
她的目光缓缓移开,落在我脚边不远处的地面上。那里,静静躺着那张摊开的、如同死亡判决书般的体检报告单,还有那支刻着XY&QM的黑色钢笔。
她看着它们,沉默了许久。实验室冰冷的空气仿佛凝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