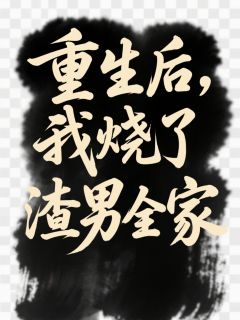前世我死在他和寡嫂手里。孩子咽气那晚,暴雨浇透了乱葬岗的土。
傅璋搂着他那娇弱的寡嫂,冷眼看我刨坑的手鲜血淋漓:「闹够没?孩子病逝是你照看不周。
」直到我咳着血倒在柴房草堆里,
才听见管家啐道:「兼祧两房的秘密总算能见光了——四个小崽子可都姓傅!」
1重生悔婚指尖触到锦被的流苏穗子,冰凉滑腻。我猛地睁眼。
拔步床顶的缠枝莲纹帐子金晃晃的刺眼。窗外蝉鸣撕心裂肺地叫,吵得人脑仁疼。抬手摸脸,
没有咳血后的黏腻,也没有柴房草梗扎进皮肉的刺痛。「姑娘可算醒了!」
丫鬟春桃扑到床沿,眼睛肿得像桃,「傅家又派人来催问婚期了,夫人在前厅应付着呢,
脸色难看得紧……」傅璋。这个名字像淬了毒的针,狠狠扎进我太阳穴。
前世记忆轰地冲进脑子——傅璋拖着六年不完婚,却总往寡嫂柳氏院里钻。
我怀胎八月时「意外」摔下台阶,早产生下的哥儿瘦得像猫崽,三天两头生病。
最后那夜雷雨劈开窗户,孩子浑身滚烫。我光脚冲去拍傅璋书房的门,
却听见里头柳氏娇声啜泣:「……阿璋,孩子们怕雷,你抱紧些呀。」四个孩子。
傅璋和柳氏的四个孩子。管家后来在我断气前狞笑:「兼祧两房懂不懂?
大爷死前就把嫂子托付给咱家大人了!你?占着正妻名分的挡箭牌罢了!」「姑娘?
您指甲掐出血了!」春桃惊呼。我低头。右手掌心被自己掐出四个月牙形的血印子。疼,
但**痛快。「更衣。」我掀被下床,赤脚踩上冰凉的金砖地,「去前厅。」
傅家管事婆子周嬷嬷正翘着腿喝茶。眼皮子耷拉着,话却硬得像铁坨子:「梁夫人,
不是老奴逼您。我家大人如今是圣上跟前红人,多少贵女挤破头想进傅家门?
贵府姑娘占着正妻位子六年了,再不下聘成婚,外头闲话可不好听呐!」我娘攥着帕子,
指节发白:「当年是傅璋亲口说要等功成名就再风风光光迎娶……」「哎哟,
梁夫人还做梦呢?」周嬷嬷嗤笑,茶盖磕得杯沿叮当响,「实话说了吧,我们老夫人念旧,
才容贵府姑娘占着坑。要按大人的意思……」「按他的意思,」我跨过门槛,声音不大,
却惊得周嬷嬷手里茶盏一歪,「该让我这‘占坑的’滚蛋,
好让柳氏带着四个傅家种登堂入室,对不对?」死寂。周嬷嬷脸皮抽搐,
像被抽了一鞭子:「姑、姑娘胡沁什么!柳娘子是守节的寡妇……」「守到傅璋床上去的节?
」我娘手里的佛珠啪地断了,檀木珠子滚了一地。
周嬷嬷跳起来指着我鼻子:「小**敢污蔑朝廷命官!老奴这就回禀大人,退了你……」
「用不着。」我把早就备好的退婚书拍在案几上,震得她刚放下的茶盏跳了跳,
「滚回去告诉傅璋,这正妻的坑,我梁幼仪不占了。让他们一家六口锁死,别放出来祸害人。
」周嬷嬷抓起退婚书,活像抓着烧红的炭,连滚带爬窜出门。我娘瘫在椅子上,
嘴唇哆嗦:「仪儿,你刚说四个孩子……难道傅璋和他嫂子……」「娘,」
我弯腰捡起一粒佛珠,攥进掌心,硌得生疼,「备车马,开祠堂。」「今日这婚,必须死透。
」2火烧傅家傅家祠堂阴得很。牌位层层叠叠压在阴影里,烛火都透不进气。
傅璋拦在供桌前,官袍下摆沾着泥,想是刚从衙门狂奔回来。「幼仪,你闹什么?」
他喘着粗气,试图来抓我手腕,「周嬷嬷老糊涂传错话,我回去就发卖了她!
你我婚约是御赐的,岂能儿戏……」我侧身避开。他指尖擦过我袖口绣的缠枝莲,
前世我就是穿着这件嫁衣,在傅家空守六年冷房。「兼祧两房也是御赐的?」我举起火把,
松油味混进陈年香灰气里,呛得人喉头发紧,「傅璋,柳氏生的老大叫傅明哲,今年五岁,
左耳后有颗红痣。老二傅明睿,三岁,抓周时攥着你给的狼毫笔不放。老三老四是龙凤胎,
刚满周岁——」傅璋的脸褪尽血色,惨白得像祠堂糊窗的桑皮纸:「你……你如何得知?」
「我还知道,」火把往前一递,最下层一排祖宗牌位「呼啦」窜起火苗,「你大哥根本没死。
当年坠马是你动的手脚,就为名正言顺接手嫂子,再吞了我梁家的势!」「住手!」
傅璋目眦欲裂扑上来。迟了。火舌卷过浸透松油的族谱,贪婪地吞掉「兼祧两房」那行墨字。
烈焰腾起的瞬间,我仿佛看见前世乱葬岗的雨,听见我早夭孩子微弱的啼哭。
傅璋的嚎叫混在木料爆裂声里:「梁幼仪!你烧我傅家百年宗祠,我要你偿命!」
火光照亮他扭曲的脸,也照亮祠堂门口不知何时出现的玄色身影。那人斜倚着门框,
苍白的指尖转着一块鎏金令牌,声音懒洋洋砸过来:「傅大人想让谁偿命?」
凤阙小王爷的令牌在火光里转出一道金弧。「本王刚查清一桩冒功欺君的旧案——傅大人,
你猜主犯是谁?」傅璋的嘶吼卡在喉咙里。我扔了烧秃的火把,转身朝门外走去。
热浪掀动我鬓边碎发,祠堂梁柱在身后轰然倒塌。焦土味真呛人。也真好闻。
傅家祠堂的冲天大火,烧红了半个京城的天。傅璋被凤阙小王爷的人当场锁拿下狱,
罪名是「冒功欺君」和「戕害嫡亲兄长」。那身刚穿上没几天的绯色官袍,
沾满了烟灰和泥泞,比丧服还难看。我站在梁府最高的阁楼上,看着那片焦黑的废墟。
春桃给我披上披风:「姑娘,风大。」「烧干净了才好。」我拢了拢披风,指尖冰凉。
傅家倒了。傅璋下了天牢,兼祧两房的丑事随着那场大火烧得人尽皆知。柳氏?
听说她抱着四个孩子想逃,被愤怒的傅家族人堵在城门口,撕扯得钗环散乱,
哭嚎声传了三条街。傅家百年清誉毁于一旦,族人恨毒了她这个「祸水」。「姑娘,
柳氏……被傅家宗族沉塘了。」春桃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快意。沉塘?
便宜她了。我闭了闭眼,前世我儿在乱葬岗连块薄棺都没有,她凭什么得个痛快?
「那四个孩子呢?」「傅家族老做主,除籍,充作官奴。」官奴。世代为奴,永无翻身之日。
傅璋和柳氏心心念念的傅家血脉,终究成了最卑贱的尘土。这还远远不够。
傅璋还在天牢里喘气。他背后的人,还没揪出来。前世我儿病得蹊跷,那场「意外」
的摔跤也绝非偶然。傅璋一个寒门爬上来的,没那胆子也没那本事只手遮天。「备车。」
我转身下楼,「去刑部大牢。」天牢里的气味混杂着霉烂、血腥和绝望。
傅璋被单独关在最里间的死牢。短短几日,他身上的官威荡然无存,头发散乱,脸颊凹陷,
那身囚服污秽不堪。听到脚步声,他猛地扑到铁栏上,枯瘦的手指死死抓住栏杆。「幼仪!
幼仪救我!」他眼中布满血丝,声音嘶哑,「我是被冤枉的!是有人害我!
看在我们六年情分……」「情分?」我隔着冰冷的铁栏看他,像看一摊令人作呕的烂泥,
「傅大人,你和柳氏在书房颠鸾倒凤,算计着我梁家嫁妆时,可想过情分?」
【我儿高烧不退,你在柳氏房里抱着你们的野种听雨声时,可想过情分?】【傅璋,
你真当我不知道?我怀胎八月摔下台阶,是你让管家在青石板上抹的桐油。
】【我儿体弱多病,是你让柳氏收买的奶娘,在汤药里加了寒凉的‘紫背天葵’!
】他脸色灰败,嘴唇哆嗦:「孩子……孩子的事是意外!是柳氏那**故意勾引,是她……」
「哦?」我微微俯身,靠近铁栏,声音轻得像耳语,「那你陷害自家大哥,
冒领军功的事也是她勾引的?」傅璋的瞳孔骤然缩成针尖,
浑身筛糠似的抖起来:「你……你怎么……」「我怎么知道?」我直起身,
从袖中缓缓抽出一张薄薄的纸。那是一张按着鲜红手印的供状。「你的好管家,
骨头可没你想象的硬。」前世那个在我断气前狞笑的管家,这辈子被我爹的人「请」
进梁府地牢。不过两个时辰,就把傅璋和柳氏那点腌臜事吐了个干干净净。
连带着傅璋是如何构陷他大哥,如何冒领边关军功的细节,一字不漏。我把供状展开,
贴在铁栏上,让他看得清清楚楚。「不!这是诬陷!是屈打成招!」傅璋疯狂地摇撼着铁栏,
发出刺耳的哐当声。「是不是诬陷,自有大理寺定夺。」我收起供状,眼神冰冷,「傅璋,
你猜猜,你心心念念想光耀的傅家门楣,还有你那四个宝贝儿子,如今在何处?」
他猛地抬头,眼中闪过一丝希冀。我扯了扯嘴角,吐出两个字:「教坊司。」
傅璋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得干干净净。他喉咙里发出「嗬嗬」的怪响,像被抽掉了所有骨头,
软软地瘫倒在地。浑浊的眼泪混着鼻涕流下来。教坊司,那是官妓所在。他那四个「傅家种」
,男的世代为奴,女的……「梁幼仪!你好毒的心肠!他们是孩子!孩子啊!」他趴在地上,
绝望地嘶吼。「孩子?」我低头看着他,如同看着阴沟里的蛆虫,「我的孩子,
就不是孩子了?傅璋,这滋味,好好受着。你活着的每一天,都会比死更难受。」
不再看他一眼,我转身离开。身后是他撕心裂肺、如同野兽般的嚎哭和咒骂。这声音,
比丝竹管弦悦耳多了。傅璋的案子审得极快。人证物证俱全,冒功、杀兄、欺君,
条条都是死罪。凤阙小王爷把查实的罪证往金銮殿上一递,龙颜震怒。秋后问斩。行刑那日,
我没去法场。听说傅璋一路都在破口大骂,骂我蛇蝎心肠,骂柳氏红颜祸水,骂老天不公。
直到鬼头刀落下,那骂声才戛然而止。我坐在梁府后院的秋千上,有一下没一下地晃着。
春桃端来一碗冰镇的酸梅汤。「姑娘,傅璋……伏法了。」「嗯。」我接过瓷碗,
冰凉的触感沁入掌心。前世剜心蚀骨的恨意,随着那一声刀响,似乎淡去了一丝。
但心底深处那块被挖走的空洞,依旧冰冷地存在着。傅璋死了,柳氏死了。可那些帮凶呢?
那个收了柳氏银子、在我安胎药里做手脚的府医呢?
那个被傅璋收买、替他伪造军功文书的同僚呢?还有……前世我死后,梁家迅速败落,
爹娘郁郁而终。这背后,真的只是傅璋的手笔?3幕后黑手「姑娘,凤阙王府递了帖子来。」
管家捧着一张洒金帖子进来。我展开帖子。字迹瘦劲疏狂,带着几分漫不经心的病气。
「傅氏余烬已冷,梁姑娘心头之火,可曾稍歇?王府新得雨前龙井,不知可否邀姑娘共饮,
以慰……本王好奇之心?」落款:容阙。凤阙小王爷,容阙。
这个前世与我毫无交集、今生却在我焚毁傅家祠堂时恰到好处出现的病弱王爷。他帮我,
图什么?「备车。」我放下帖子。凤阙王府出乎意料的清雅,不见半分皇家的煊赫奢靡。
引路的侍从沉默寡言,将我带到一处临水的敞轩。轩外荷风送爽,轩内药香袅袅。
容阙斜倚在窗边的软榻上,一身素白常服,衬得脸色愈发苍白透明,
仿佛一碰即碎的薄胎玉瓷。他手中把玩着一只玲珑的白玉杯,听见脚步声,抬眼望来。
那双眼睛,却幽深得像不见底的寒潭,带着洞悉一切的锐利,与他病弱的外表格格不入。
「梁姑娘来了。」他唇角弯起一个浅淡的弧度,声音有些低哑,「坐。尝尝这茶,
今年的新贡。」我依言坐下,端起面前碧绿的茶汤,茶香清冽。「多谢王爷当日在傅家援手。
」「举手之劳。」容阙掩唇轻咳了两声,苍白的脸颊泛起一丝病态的红晕,「傅璋罪有应得,
本王不过是顺水推舟,恰好……他挡了本王的路。」他放下玉杯,目光落在我脸上,
带着审视:「倒是梁姑娘,好狠的手段,好快的手脚。傅家百年基业,
被你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连根都没剩下。」「王爷过誉。」我迎着他的目光,不闪不避,
「欠债还钱,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好一个天经地义。」容阙低低地笑了,
笑声牵动肺腑,又引来一阵压抑的咳嗽。他用一方素白的帕子捂着嘴,咳得肩头都在轻颤。
侍从无声地递上一碗浓黑的药汁。他接过,眉头都没皱一下,仰头饮尽。喉结滚动,
将那苦涩的药汁尽数吞下。放下药碗时,唇边沾了一点褐色的药渍,被他随手抹去,
动作带着一种颓靡的优雅。「梁姑娘可知,」他缓了口气,声音更哑了几分,
带着一丝蛊惑的味道,「傅璋背后,还有条没揪出来的大鱼?」我端着茶杯的手微微一紧。
「王爷指的是?」容阙那双深潭般的眼睛看着我,一字一句:「吏部,右侍郎,王崇焕。」
王崇焕!这个名字像一道惊雷劈进我脑海!前世我爹被贬黜出京,梁家产业被巧取豪夺,
最后弹劾我爹、罗织罪名的,就是这个王崇焕!他竟是傅璋背后的人?「傅璋冒领的军功,
当年就是经王崇焕的手运作,才瞒天过海,让他得以青云直上。王崇焕看中的,
是你梁家在江南漕运上的财路和人脉。傅璋,不过是他养的一条狗,用来咬住你梁家的饵。」
容阙的声音平静无波,却字字如刀,「你前世……梁家败落得蹊跷吧?」我指尖冰凉,
茶杯几乎要捏碎。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傅璋是明面上的刽子手,
王崇焕才是藏在幕后的黑手!他们联手,一个要人,一个要财!「王爷告诉我这些,
意欲何为?」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容阙又咳嗽起来,这次咳得更凶,
仿佛要把五脏六腑都咳出来。半晌,他才止住,额角渗出细密的冷汗,脸色白得吓人。
他靠在软枕上,微微喘息,看向我的眼神却亮得惊人,带着一种近乎疯狂的偏执。「因为,」
他喘息着,勾起一个苍白而冰冷的笑,「本王想看看,
梁姑娘这把能烧了傅家祠堂的火……能不能,再烧掉一个王侍郎?」「本王病骨支离,
时日无多,平生最恨的,就是这些结党营私、蛀空国朝的蠹虫。」他伸出手,
那只手骨节分明,苍白得能看见淡青的血管,掌心朝上,对着我。「合作吗,梁姑娘?」
他眼中燃烧着与我同源的火焰,那是复仇的毒火,焚尽一切的疯狂,「本王给你递刀,
你替本王……送他们下地狱。」敞轩内寂静无声,只有窗外风吹荷叶的沙沙轻响。
药味和茶香交织在一起,弥漫在空气中。我看着容阙伸出的那只苍白的手,
又看看他那双燃烧着地狱之火的眼睛。前世冰冷的柴房,孩子滚烫的小手,
乱葬岗的冷雨……一幕幕在眼前闪过。傅璋的血,浇不灭我心底的恨。
王崇焕……还有那些藏在更深处、吸食着梁家血肉的魑魅魍魉……我放下茶杯,
瓷器碰触檀木桌面,发出清脆的一声「叮」。然后,我伸出手,没有去握他那只冰冷的手。
而是稳稳地拿起了他面前小几上,那枚用来拨弄香灰的、小巧精致的铜火折子。
指腹摩挲着冰凉的铜管,轻轻一甩。「嚓——」一簇幽蓝的火苗,瞬间跳跃起来,
映亮了我毫无表情的脸。也映亮了容阙眼中骤然爆发的、近乎病态的亮光。
我盯着那簇跳动的火苗,声音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小王爷,火折子借我用用。」
「下一个,烧谁?」4打蛇七寸王崇焕这名字,像块烧红的烙铁,烫在我心尖上。
前世我爹被贬出京,梁家百年基业顷刻崩塌,最后递上那封致命弹劾奏章的,
就是这只笑面虎!原来傅璋背后,还藏着这么条大蛀虫。容阙那只苍白的手还悬在半空,
掌心朝上,像一张邀请坠入深渊的请柬。我捏着那枚铜火折子,
幽蓝的火苗舔舐着指尖的空气,发出细微的「噼啪」声。「怎么烧?」我抬眼,
撞进容阙那双深不见底、却燃着病态火焰的眸子。他需要我这把刀,我也需要他递来的梯子。
王崇焕盘踞吏部多年,树大根深,单凭梁家,撼不动。容阙收回手,掩唇又咳了几声,
苍白的脸上泛起异样的红晕。「王崇焕有个心尖上的宝贝。」他喘了口气,
声音带着蛊惑的沙哑,「他那个不成器的独子,王珣。在城西金水巷,养了个外室,
生了对龙凤胎。」我指尖的火折子轻轻一晃。「王珣好赌,
欠了‘四海赌坊’阎老五一大笔印子钱,利滚利,足够把他爹的官袍都扒下来。」
容阙从袖中滑出一张薄薄的纸,推到我面前。那是一张摁着血红手印的巨额借据,
落款正是王珣。「王崇焕最重脸面,更怕他儿子出事断了他王家香火。这火,得烧旺点,
烧到他家门口去。」借据上墨迹未干,透着一股新墨的腥气。四海赌坊阎老五?
那可是京城出了名吃人不吐骨头的主儿。王珣这蠢货,真是把好柴禾。
「王爷想怎么递这把火?」我捻着借据,冰凉的纸张触感却像烙铁。
「阎老五手下有个叫‘疤脸张’的,是个认钱不认人的亡命徒。」容阙指尖沾了点茶水,
在光滑的紫檀小几上画了条歪歪扭扭的线,「金水巷,桂花胡同第三家,青砖小院,
门口有棵歪脖子枣树。那对龙凤胎,是王珣的命根子,也是王崇焕的软肋。」他抬起眼,
幽深的瞳孔里映着那跳动的幽蓝火苗,「梁姑娘这把火,能烧得再快些吗?」懂了。
王崇焕要脸,要儿子,更要孙子。那就把他最怕的,全撕开,晾在太阳底下!金水巷,
桂花胡同。空气里飘着一股劣质脂粉和饭菜馊味混合的浊气。第三家小院门口,
那棵歪脖子枣树蔫头耷脑,几片黄叶挂在枝头。
一个穿着半旧绸衫、油头粉面的男人正烦躁地在院门口踱步,时不时朝巷口张望,正是王珣。
「阎五爷那边……真不能再宽限几日?」他搓着手,
对着身边一个满脸横肉、眼角带疤的汉子低声下气。疤脸张抱着膀子,冷笑:「王公子,
宽限?你当五爷开善堂的?利钱都滚到天上去了!今日再不还上这个数,」
他伸出三根粗短的手指在王珣眼前晃了晃,「要么剁你一只手抵利息,要么……」
他目光淫邪地瞟向紧闭的院门,「里头那对水灵灵的娃娃,五爷瞧着也喜欢。」
王珣吓得脸都绿了,冷汗涔涔:「张哥!张哥使不得!孩子还小!钱……钱我一定想办法!
我爹……我爹是吏部侍郎……」「呸!」疤脸张一口浓痰啐在地上,「你爹?
你爹的面子在五爷那儿,顶个屁用!还钱,还是交人?痛快点儿!」就在王珣急得快尿裤子,
疤脸张的手下蠢蠢欲动要砸门时,巷口传来一阵喧哗。「让开!都让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