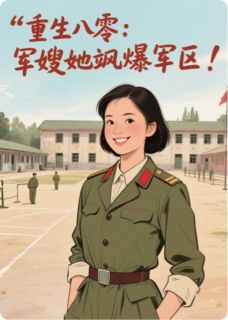槐生十六岁那年,背着行囊走进了军营,穿上了和父亲、爷爷同款的军装。送他去火车站的那天,傅景深站得笔直,像棵老松树,拍着儿子的肩膀只说了句:“好好干,别给傅家丢人。”
槐生敬了个标准的军礼,目光扫过人群中的母亲和妹妹,还有头发花白的太爷爷、奶奶,声音响亮:“保证完成任务!”
火车开动时,姜念看着儿子在车窗后挥手的身影,突然想起三十年前,傅景深也是这样离开的。时光仿佛是个圈,把最珍贵的东西,一圈圈传承下去。
傅念柳没像哥哥那样去当兵,而是考上了财经大学,毕业后回了青柳镇,开了家农产品合作社,把军属们种的蔬菜、养的鸡鸭卖到城里,成了小有名气的“致富带头人”。
有次傅念柳回家,兴奋地跟姜念说:“妈,我把技能班改成电商培训了,教军嫂们直播卖货呢!现在啊,咱们的土鸡蛋都能卖到北京去!”
姜念看着女儿神采飞扬的样子,笑着说:“跟你妈我当年一样,闲不住。”
傅景深已经是傅团长了,鬓角添了些白发,眼神却依旧锐利。他还是习惯每天回家吃晚饭,只是饭桌上的话题,从训练变成了槐生的家书,和傅念柳合作社的新鲜事。
“槐生在部队表现不错,得了个嘉奖。”傅景深放下筷子,语气里带着藏不住的骄傲,“跟我当年一个样。”
“是随了我,机灵。”姜念笑着给他盛汤,“你当年可没他这么细心,上次他还在信里问,太爷爷的腿好了没,奶奶的高血压犯没犯。”
傅奶奶的身体大不如前,却还是惦记着食堂的事,总念叨:“念念啊,那红烧肉的火候可得盯着点,别让年轻人给做差了。”
“知道啦奶奶。”姜念握着她的手,“我每周都去食堂看看,保证还是您当年教我的味道。”
傅爷爷在一个飘雪的冬天走了,走的时候很安详,手里还攥着那把磨了一辈子的军刺。送葬那天,槐生从部队赶回来,穿着笔挺的军装,跪在灵前磕了三个响头,跟太爷爷保证:“您放心,傅家的人,会永远守着这片土地。”
那年秋天,青柳军区举行阅兵式。姜念和傅景深坐在观礼台上,看着槐生穿着崭新的军装,走在队伍里,步伐铿锵,眼神坚定,像极了年轻时的傅景深。
傅念柳带着合作社的军嫂们,举着“军属光荣”的牌子,站在路边欢呼。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得像当年傅景深给她披上的军外套。
阅兵式结束后,槐生找到父母,敬了个军礼:“爸,妈,我申请去边境了,跟您当年一样。”
傅景深看着儿子,突然想起自己年轻时的模样,眼眶一热,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好样的。记住,身后是家,面前是国,不能退。”
姜念没哭,只是帮儿子理了理衣领:“到了那边,照顾好自己。妈给你寄的辣椒酱,记得吃。”
槐生走的那天,傅念柳开车送他去车站。路上,小丫头突然说:“哥,你放心,家里有我呢。就像当年妈守着家等爸回来,我也守着家等你。”
槐生看着妹妹,笑了:“好。”
岁月就这样慢慢流走,家属院的老槐树又落了几次叶,食堂的炊烟依旧每天升起。傅景深退休后,最爱做的事就是坐在院子里,看着姜念在厨房忙碌的背影,或者翻看那本已经泛黄的笔记本——上面有她画的小人,抄的菜谱,还有他写的回信。
“你说,咱们这辈子,是不是挺值的?”姜念端着碗汤走出来,放在石桌上。
傅景深接过汤,看着远处训练场上年轻的身影,又看看身边的老伴,笑着说:“值。有你,有孩子,有家,还有这身没脱下来的军魂,怎么不值?”
夕阳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两棵依偎在一起的老槐树。远处的军号声隐约传来,带着熟悉的节奏,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关于爱、守护和传承的故事。
这个故事里,有铁血硬汉的温柔,有飒爽军嫂的坚韧,有烟火气里的相守,也有家风传承的力量。它像青柳军区的阳光,温暖而明亮,照亮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