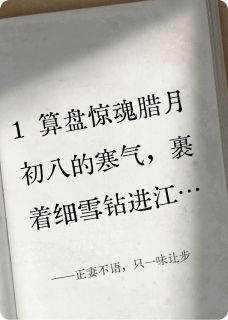1算盘惊魂腊月初八的寒气,裹着细雪钻进江府高阔的门庭。我,沈静书,
正领着瑞哥儿和玉姐儿在暖阁里描红,丫鬟秋菊匆匆打起帘子,
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绷:“夫人,爷回来了!”瑞哥儿欢呼一声扔下笔,
玉姐儿也雀跃地扑进我怀里。我心头微暖,承业离家贩货半年,总算赶在年根前回来了。
牵着儿女疾步迎至前厅,公婆已端坐上位,脸上亦是掩不住的喜色。然而,厅堂中央站着的,
不止是风尘仆仆的承业。他身侧立着一个年轻女子,约莫十七八岁,
一身窄袖束腰的黛青胡服,衬得身姿利落,乌发梳成个古怪的高髻,露出光洁的额头。
最扎眼的,是她腰间悬着的一副铁算盘,乌沉沉的框,玉白的珠,
与她那双亮得惊人的眸子一样,透着一种与周遭格格不入的新奇与审视。
她一手挽着承业的胳膊,姿态亲昵自然。承业脸上是久别重逢的激动,
更有一层难以言喻的兴奋光彩。他扶着那女子的肩,声音洪亮:“爹,娘,静书!
这位是柳思思姑娘!这次北行,多亏了她!路上几番遭险,
都是思思用些…嗯…闻所未闻的‘商战奇谋’化解,更助我谈成了几笔大单,利润翻了几番!
”他顿了顿,目光落在柳思思平坦却紧致的小腹上,声音低了些,带着一丝难以启齿的愧疚,
“且…路途艰险,为护我周全,她与我…已有肌肤之亲。”堂上瞬间落针可闻。
婆母手中捻动的佛珠“啪嗒”一声掉在膝上,公公捋须的手僵在半空。
瑞哥儿和玉姐儿茫然地依偎着我,不明所以。我只觉一股冰冷的寒气,
顺着脚底的青砖直窜上来,冻得指尖发麻。
我看着承业脸上那混杂着愧疚、骄傲与情热的复杂神情,
看着柳思思微微扬起的下巴和眼中毫不掩饰的得意与占有欲,心,一点点沉入冰窖。
拢了拢袖口,指尖掐进掌心,面上却竭力维持着当家主母的平静。我迎上承业闪烁的目光,
声音听不出波澜:“原是位有胆识、有本事的姑娘,又是为救夫君。既如此,不过是纳个妾,
妾身这就去安排,定不会委屈了柳姑娘。”“纳妾?”柳思思清脆的声音带着明显的讥诮,
她上前一步,腰间的铁算盘随着动作发出“叮呤”轻响。她直视着我,眼神锐利如针,
“姐姐,承业答应过我,我们之间是超越时空的真爱!他许了我一生一世一双人。
这深宅大院里的‘妾’字,我可担不起。姐姐辛苦打理这些琐碎多年,也该歇歇,
让位给真正懂他、能与他并肩的人才是。”她说着,手自然地抚上承业的臂膀,
姿态亲昵而宣示**。“放肆!”婆母猛地一拍桌案,气得浑身发抖。公公脸色铁青。
承业急忙跪下:“爹娘息怒!思思心直口快,绝无对静书不敬之意!
她…她只是…”厅内乱作一团。公婆的震怒,承业的辩解,柳思思毫不退让的坚持,
交织成一张令人窒息的网。最终,
思思当场展示了几个诸如“会员预存”、“饥饿营销”等令承业如获至宝的“商道奇策”后,
在公婆对儿子前途的权衡与无奈下,柳思思以“贵妾”之礼入府。虽无平妻名分,
承业却力排众议,赋予她掌管内宅部分庶务及几间重要商铺账目的实权,地位远超寻常侍妾。
2权谋暗涌江家世代经商,富甲一方。我嫁入八年,操持中馈,侍奉双亲,
生养了瑞哥儿和玉姐儿,自问无愧“主母”二字。承业常年在外,这诺大家业,
内靠我稳后院,外靠他掌商路。公婆待我亲厚,视如己出。他离家前夜,
还曾拥着我温存低语,许诺归期。谁曾想,归人带回的,是一场打败我世界的风暴。
柳思思入主东院后,果然雷厉风行。她提出的“连锁经营”概念,让承业热血沸腾,
未经详察便斥巨资在邻镇连开三间新铺;“会员预存”更是强迫老主顾缴纳高额银两,
捆绑消费,暗中提价,引得怨声载道;“饥饿营销”竟用在了米粮布匹等必需品上,
导致市面混乱,黄牛横行,江家口碑一落千丈。她腰间的铁算盘拨得飞快,
手下新提拔的管事却多是溜须拍马之辈,新式账法推行混乱,漏洞百出,亏损日益严重。
更令我如鲠在喉的是,她很快有了身孕。承业大喜,对她更是百依百顺。一日,
他踏入我已显冷清的听松院,期期艾艾地开口:“静书…思思如今身子重了,
主院那边…她说格局逼仄,风水不利养胎…你看…你向来最是温婉贤淑,体谅下人…不如,
先将主院让与她暂住?西边带暖阁的听松院给你和孩子们,离爹娘也近,方便照应。
”我正为瑞哥儿缝着入学的书袋,闻言,细小的针尖猝不及防刺入指尖。
一点殷红迅速在素色锦缎上洇开,像心口无声裂开的血洞。我抬眼,撞上他闪烁的目光,
那里面有一丝愧疚,但更多的是不容置疑的强硬。指尖的痛楚蔓延至四肢百骸,我垂下眼睫,
掩去所有情绪,声音平静得没有一丝波纹:“夫君既已为柳姨娘考量周全,妾身遵命便是。
”搬离主院那日,雪后初晴。柳思思挺着微隆的小腹,裹着华贵的狐裘,
在几个新买丫鬟的簇拥下,像巡视领地般站在主院门口。她看着仆役们搬动我的箱笼,
唇角噙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讽笑。“都给我打起精神,仔细着点!”她声音不高,
却清晰地传遍庭院,“别把什么不该拿的也顺手牵羊了。姐姐,”她转向我,笑容明媚,
“承业在外头风餐露宿地挣钱不易,咱们做女人的,得替他守好这份家业,您说是吧?
”秋菊气得脸色煞白,拳头攥紧。我抬手轻轻按住了她,
目光平静地迎向柳思思:“柳姨娘费心了。府中总账册、库房钥匙、田产地契,
皆在妾身处妥善保管。主院一应陈设器物,入府时皆有册登记,姨娘若觉何处不清,
随时可着人核对。至于替夫君守业,”我顿了顿,目光扫过她年轻气盛的脸庞,
“那是正妻的本分,不劳姨娘挂心。”柳思思被我噎住,脸上红白交错,
那精心维持的得意僵在嘴角。她狠狠瞪了我一眼,最终冷哼一声,扶着腰,
像只骄傲的孔雀般转身踏入主院。腰间铁算盘随着她的步伐,“叮呤”作响,清脆又刺耳。
公婆为此大发雷霆,婆母更是拉着我的手垂泪不止:“静书,委屈你了!是承业混账!
被个不知根底的狐媚子迷了心窍!她那些花哨把戏,看着热闹,焉知不是祸根?
”我反握住婆母枯瘦的手,温言劝慰:“娘,您保重身子要紧。柳姨娘…确有几分新奇手段,
能为江家开源,亦是好事。只要夫君顺遂,家宅和睦,儿媳住哪里都一样。”我抬眼,
目光恳切,“只是瑞哥儿开蒙在即,玉姐儿也需好好教养,万不可因内宅琐事耽搁了。
”婆母浑浊的眼中闪过一丝清明,用力回握我的手:“静书,你放心!只要我这口气在,
瑞哥儿和玉姐儿就是江家嫡出的根苗!谁也越不过去!她那肚皮里出来的?哼!
”这一声冷哼,是承诺,也是我立足的根基。3旧梦新殇搬到听松院,日子反倒清净。
我全心教养儿女,瑞哥儿的功课日益精进,玉姐儿也越发伶俐可人。侍奉公婆,晨昏定省,
从不懈怠。我手中的核心产业,依旧打理得井井有条,暗中积蓄力量。
对柳思思掌管的庶务和那几间铺子,我冷眼旁观,不置一词。
柳思思的“新政”在短暂的虚假繁荣后,弊端如同溃堤般涌现。
老主顾因“霸王条款”纷纷转投别家;盲目扩张的新铺因管理不善、货源不足,门可罗雀,
成了巨大的吞金兽;混乱的账目终于爆出亏空,甚至有管事内外勾结,中饱私囊。
府中下人间怨声载道,那些被她排挤走的老掌柜、老管事,人心浮动。与此同时,
她的身子也随着权柄的膨胀和孕期的消耗,迅速垮了下来。头胎生产便伤了元气,
产后郁郁寡欢,将女儿丢给乳母,一心扑在“事业”上试图力挽狂澜。很快,
她又怀上了第二胎。这一胎怀相极差,孕吐剧烈,夜不能寐,却仍强撑着不肯放权,
脸色蜡黄,眼窝深陷。承业被一封封告急的商信搅得焦头烂额,隐隐察觉不妥。
但每每看到柳思思因不适而憔悴的脸和她眼中那份对“宏图大业”近乎偏执的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