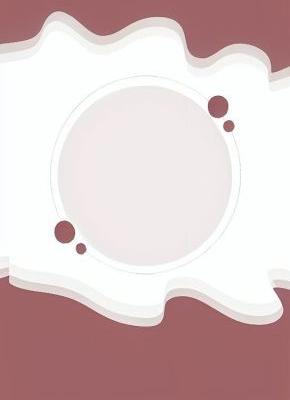我从火场里救出同事一家后,他激动地要把女儿嫁给我。
他女儿是镇花,此刻却满脸鄙夷地打量我。
“你一个月挣三十块,我一件的确良衬衫就二十,你拿什么养我?”
“你住的土坯房,连个厕所都没有,下雨天一身泥,恶不恶心?”
全村人都笑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我没说话,默默揣着兜里所有的钱,去镇南买了三亩无人要的荒地。
他们不知道,我是带着未来四十年的记忆重生的。
1986年的风,带着窑厂烟囱里飘出的煤灰味,刮在脸上,生疼。
我刚从那栋烧得只剩下漆黑框架的房子里爬出来,浑身是水和灰,脸上被熏得黢黑,只剩一双眼睛还在发亮。
怀里,是同事刘大壮家三岁的小儿子,已经被浓烟呛得昏了过去。
我把孩子交到他老婆王翠芬怀里,她抱着孩子,哭得撕心裂肺。
刘大壮冲过来,一把抓住我的胳膊,这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眼泪鼻涕糊了一脸。
他“扑通”一声就要往下跪。
我赶紧扶住他:“刘哥,使不得!”
他站不稳,整个人挂在我身上,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望东,你救了我们全家!你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啊!”
“我……我刘大壮这辈子做牛做马都报答不了你!”
他通红的眼睛死死盯着我,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
“我没啥能给你的,我那个闺女,刘丽,今年十八,长得俊,十里八乡的镇花!你要是不嫌弃,我……我就把她许给你!”
这话一出,周围嘈杂的人群瞬间安静下来。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然后又齐刷刷地转向不远处一个俏生生的身影。
那是刘丽。
她刚从外面回来,还没搞清楚状况,脸上还带着惊魂未定。
但当她听清父亲的话,那份惊恐迅速被一种毫不掩饰的嫌恶所取代。
她细长的眉毛拧在一起,那双被镇上小伙子们夸赞为“会说话”的眼睛,此刻正像x光一样,从上到下,一寸一寸地扫视我。
我能感觉到她的目光在我破了洞的解放鞋上停留,在我沾满黑灰、打了好几个补丁的裤子上停留,最后落在我这张因为常年干体力活而显得黝黑粗糙的脸上。
她红润的嘴唇不屑地撇了一下。
“爸,你说什么胡话呢!”
她的声音清脆,但带着一股子尖刻,像一把小刀子,精准地扎进我刚从火场里逃出生天的余悸里。
刘大壮急了:“丽丽!望东是我们的救命恩人!要不是他,我们一家今天就全完了!”
“救命恩人?”
刘丽冷笑一声,抱着胳膊,朝我走近几步,一股廉价雪花膏的香味混着烟火的气息钻进我的鼻子。
“救了人就得我嫁给他?这是哪门子的道理?”
她停在我面前,仰着那张漂亮的脸,下巴抬得高高的,像一只骄傲的孔雀在审视一只泥地里的土狗。
“林望东,我问你,你一个月工资多少?”
我没说话,只是平静地看着她。
上一世,就是这个问题,开启了我长达半生的屈辱。
“我替他答!”旁边一个看热闹的碎嘴婆娘高声喊道,“窑厂拉砖坯的,一个月撑死三十块!”
人群里发出一阵低低的哄笑。
刘丽脸上的鄙夷更浓了。
她伸手指了指自己身上那件在86年堪称时髦的的确良白衬衫,虽然被烟灰蹭脏了一块,但依然能看出料子的挺括。
“看见了吗?这件衬衫,二十块。你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我买两件衣服的。”
“你拿什么养我?”
她的声音陡然拔高,充满了攻击性。
“再说你住的地方,那个破土坯房,连个正经厕所都没有,下雨天出门就是一身烂泥,走在路上都溅我一脚!恶不恶心?”
“我刘丽要嫁的人,就算不是城里干部,起码也得是能让我天天穿新衣服,顿顿吃白面馒头的!你?”
她上下打量我,最后吐出两个字。
“配吗?”
周围的哄笑声更大了,变成了明目张胆的嘲笑。
“就是,刘家闺女可是镇花,林望东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想疯了吧!”
“救了人就想攀高枝,这算盘打得也太精了。”
流言蜚语像无数根看不见的针,从四面八方扎过来。
我看着眼前这张年轻又刻薄的脸,心中一片冰冷。
上一世的我,面对这场面,窘迫得满脸通红,只会一个劲地摆手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最后在全村人的嘲笑声中狼狈逃走。
但现在,我不会了。
就在这时,一直没说话的王翠芬,也就是刘丽的母亲,突然尖叫一声,像头发疯的母鸡,猛地冲过来,一把将我推开。
我一个踉跄,差点摔倒。
“你个丧良心的!想娶我女儿?你做梦!别以为救了我们家,就能赖上我们!”
她叉着腰,唾沫星子横飞。
“我告诉你林望东,这事没完!你救人是没错,可我女儿被这场大火吓得魂都快没了,你得赔我们惊吓费!”
我眯起眼睛。
来了,这熟悉的戏码。
“还有,我们家里的家具,缝纫机,电视机,全烧光了!你冲进火场,是不是你笨手笨脚碰倒了什么东西才烧得这么快?你也得赔!”
这简直是颠倒黑白,恩将仇报!
刘大壮在一旁拉着她的胳膊,脸上满是羞愧和无力:“孩他娘,你胡说什么!是望东救了我们啊!”
“你给我闭嘴!你这个窝囊废!”王翠芬反手就给了刘大壮一巴掌,“家里什么事你都做不了主!这事我说了算!”
她转过头,伸出一只手,五根手指在我面前张开。
“我也不多要,我女儿这件的确良衬衫被吓得以后都穿不了了,还有她的精神损失,你赔五十块钱!这事就算了了!”
五十块!
这在86年,是一个普通工人近两个月的工资。
我救了他们全家,不求回报,反倒要我赔钱。
我气到极致,反而笑了。
就在这时,一阵“突突突”的马达轰鸣声由远及近。
一辆崭新的嘉陵摩托车在人群外停下,一个穿着喇叭裤、戴着蛤蟆镜的青年跳下车,手里还拿着一瓶橘子汽水。
是窑厂厂长的儿子,李少。
“哟,这么热闹呢?”李少推开人群,径直走到刘丽身边,把汽水递给她,“丽丽,没吓着吧?”
刘丽看到李少,脸上的刻薄立刻化为一片娇羞。
她接过汽水,拧开喝了一口,然后自然地挽住了李少的胳膊,用一种胜利者的姿态瞥了我一眼,对我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看见没,这才是男人。”她用不大不小的声音说,确保我能听见。
李少轻蔑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就像在看一堆路边的垃圾。
村民们的议论声再次响起。
“林望东这下脸可丢到家了。”
“跟李少一比,他算个什么东西。”
“活该,穷就是原罪。”
我一言不发,冰冷的目光缓缓扫过刘丽一家三口那三张截然不同的脸:刘丽的得意与刻薄,王翠芬的蛮横与贪婪,刘大壮的懦弱与愧疚。
最后,我的目光停留在刘丽挽着李少的那只手上。
很好。
我记下了。
所有羞辱过我的人,一个都跑不掉。
我在所有屈辱、嘲讽、轻蔑的目光中,平静地转过身,一瘸一拐地离开。
我没有回家,而是直接走向村长家。
我掏出兜里所有的钱,那是二百块,是我辛辛苦苦攒了一年多,准备用来翻修土坯房的钱。
我把它拍在村长家的桌子上。
“村长,镇南那三亩盐碱荒地,我要了。”
村长正在抽着旱烟,被我吓了一跳。
他看着桌上的钱,又看看我,皱起了眉头。
“望东,你疯了?那地是盐碱地,种啥啥不活,白送都没人要,你花二百块买它,不是拿钱打水漂吗?”
“我就要那块地。”我的语气不容置疑。
村长叹了口气,最终还是给我签了合同,按了手印。
我揣着那份薄薄却重若千斤的合同,走出村长家。
背后,是闻讯赶来看热闹的村民们的哄堂大笑,和刘丽夹杂在其中的、不屑的嗤笑声。
他们笑我痴人说梦,却不知道,我脚下踩着的,根本不是通往坟墓的烂泥路。
而是一条用未来四十年记忆铺就的,通往世界之巅的黄金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