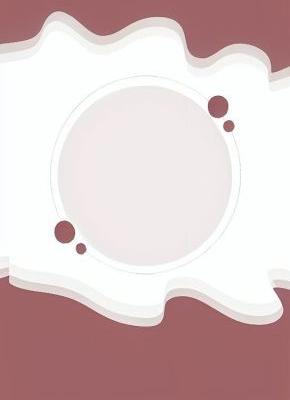我真的像个疯子一样,开始在我的“新地”上挖坑。
镇南这三亩地,名副其实的荒地。
地表泛着一层白花花的盐碱,别说庄稼,就连生命力最顽强的杂草都长得稀稀拉拉,半死不活。
村里人说,这地邪性,以前有人想在这开荒,结果种下去的种子连芽都发不出来。
我拿着一把铁锹,天不亮就出门,天黑透了才拖着一身泥回来。
我没日没夜地挖,不是平整土地,而是像个盗墓贼一样,执着地往下挖一个又一个深坑。
很快,林望东被刘丽**疯了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红星镇。
村民们干完农活,最大的乐子就是三三两两地凑到我的地头,看我这个“疯子”挖坑。
“啧啧,这孩子是真傻了,好好的二百块钱,买这么个破地方给自己挖坟。”
“可不是嘛,听说他现在连窑厂的工都不去上了,就天天在这刨土。”
“八成是受不了那口气,魔怔了。”
我充耳不闻,只是沉默地挥动着铁锹。
汗水顺着我的额头流下,滴进脚下的泥土里,砸出一个个小小的坑。
身体是疲惫的,但我的心,却因为那个即将被揭开的秘密而剧烈跳动着。
这天下午,太阳正毒。
一阵摩托车的轰鸣声再次传来,由远及近,停在了我的地头。
我不用抬头都知道是谁。
李少搂着刘丽,从摩托车上下来。
他们就像来逛公园一样,特意来看我的笑话。
刘丽今天穿了一件崭新的红裙子,脚上是一双白色塑料凉鞋,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显得格外刺眼。
李少嘴里叼着一根烟,学着港台电影里的样子,痞里痞气地走到我挖的坑边,朝里面吐了口唾沫。
“喂,林望东,”他用脚尖踢了踢坑边的土块,“在这吃土呢,吃饱了没?”
刘丽在他身边发出银铃般的笑声,那笑声里充满了毫不掩饰的优越感。
“李哥你别这么说,”她娇滴滴地说,“他家穷得叮当响,不吃土还能吃什么呀?”
我停下动作,缓缓抬起头。
阳光刺眼,我眯着眼睛,看着坑边那对依偎在一起的男女。
他们的脸上,挂着同一种残忍又愚蠢的笑容。
我没有愤怒,也没有反驳。
我的眼神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就好像在看两个与我毫不相干的死物。
上一世,他们确实也跟死了差不多。
李少后来因为聚众斗殴,被人捅死在县城的录像厅里。
而刘丽,在嫁给一个跑运输的司机后,没过几年好日子,男人就出了车祸,她守着一个药罐子丈夫,熬了半辈子,最后穷困潦倒,郁郁而终。
他们是被时代洪流轻易碾碎的蝼蚁,可笑的是,现在的他们,却以为自己站在了世界的中心。
或许是我的眼神太过平静,平静到有些骇人。
李少和刘丽脸上的笑容都僵了一下。
李少壮着胆子,把抽了一半的烟头恶狠狠地弹到我的脚下。
“看什么看!再看把你的眼珠子挖出来!”
他骂骂咧咧地搂着刘丽,跨上摩托车,一溜烟地走了。
我低下头,看着脚下那个还在冒着青烟的烟头,脚尖轻轻一碾,将它埋进了土里。
然后,我继续挖。
我知道,我离那个秘密越来越近了。
又挖了将近一米深,铁锹的尖端突然传来一种不同寻常的触感。
不是坚硬的石块,也不是松软的泥土,而是一种黏腻又柔韧的感觉。
我心中一动,扔掉铁锹,直接用手往下刨。
很快,一大块雪白细腻,宛如凝脂的泥土,出现在我眼前。
我抓起一把,紧紧地攥在手里。
触感温润,质地纯净。
就是它!
高岭土!
而且是品质最顶级,纯度最高,几乎不需要任何提纯加工就能直接用于高档瓷器生产的特级高岭土!
上一世,这个秘密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才被一个省地质队的专家偶然发现。
这片被所有人嫌弃的盐碱荒地,一夜之间变成了价值连城的宝藏,引来了无数人的争抢。
而这一世,它只属于我一个人。
这,就是我的第一桶金。
是捅向那些羞辱我的人的第一把尖刀。
我小心翼翼地用布包好一大块样品,藏在怀里。
第二天一早,我偷偷搭上去县城的便车。
在县地质局的门口,我犹豫了很久。
直接送检,目标太大,容易引起不必要的注意。
我需要一个更稳妥的办法。
我想起了上一世的一个人。
地质局的老技术员,姓孙,一个因为性格耿直、不懂变通而被排挤了一辈子的老实人。
再过两年,他就会因为一次检测失误,被单位开除,晚景凄凉。
但那次所谓的“失误”,其实是替领导背了黑锅。
我记得他的住处。
我绕到地质局的家属院,找到了孙师傅的家。
开门的是一个五十多岁,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的老人。
我说明来意,说自己是在山里偶然挖到的“怪土”,想请他帮忙看看是什么。
孙师傅一开始很警惕,但当他看到我拿出的那块雪白的高岭土样品时,眼睛瞬间就亮了。
他把我让进屋,拿出放大镜和一堆我看不懂的瓶瓶罐罐,开始仔细研究。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他的表情从好奇,到惊讶,再到狂喜。
“天呐……天呐……”他喃喃自语,“这是……这是宝贝啊!特级高岭土!纯度这么高的高岭土,我这辈子都没见过!”
他激动地抓住我的手:“小伙子,你这土是在哪里发现的?”
我看着他激动得通红的脸,微微一笑:“孙师傅,我想请您帮我出具一份正式的检测报告,但来源……我想保密。”
孙师傅愣了一下,他是个聪明人,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
他看着我,眼神复杂:“你想……卖掉它?”
“不,”我摇摇头,一字一句地说,“我要用它,建一个属于我自己的陶瓷王国。”
与此同时,红星镇李家的窑厂,正陷入一片愁云惨雾之中。
“又是废品!全都是废品!”
李厂长,也就是李少的父亲李富贵,抓起一块刚出窑、布满裂纹的砖头,狠狠地摔在地上。
“这个月的次品率已经超过百分之四十了!再这样下去,我们窑厂就得关门!”
一个管事愁眉苦脸地报告:“厂长,没办法啊,咱们从西山拉来的土,质量越来越差,烧出来的砖不是变形就是开裂。前两天给张家村盖猪圈的那批砖,墙都塌了,人家正找上门来要我们赔钱呢!”
李富贵气得一**坐在椅子上,捂着胸口直喘气。
“好土!我需要好土!谁能给我找到好土,我给他发奖金!”
他声嘶力竭地吼着,声音里充满了绝望。
而在县城,我正从孙师傅手里,接过那份足以改变我一生的检测报告。
报告的最后,结论清晰地写着:特级高岭土,主要成分含量95.7%。
我看着那行字,嘴角勾起一丝冰冷的笑容。
李厂长,你的“好土”,就在我手里。
不过,你可要准备好大出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