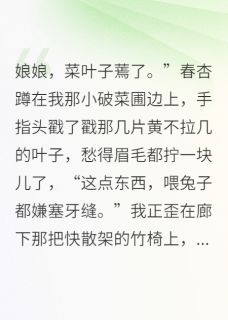我以为这咸鱼日子能天长地久地过下去,直到我把自己熬成宫里最资深的老咸鱼干。结果,老天爷大概看我太安逸了,非得给我这潭死水里扔块大石头。
这天,我正指挥春杏把院子里那点可怜的野菜挪到稍微有点日头的地方,清辉阁那扇一年到头也响不了几次的破木门,“吱呀”一声,被人从外面推开了。
进来的是个面生的太监,穿着体面,身后还跟着两个低眉顺眼的小宫女。那太监脸上堆着笑,眼神却带着点居高临下的打量,扫了一圈我这破败的院子,最后落在我身上。
我穿着半旧的粗布衣裳,袖口还沾了点泥巴,头发随便挽着,插了根磨秃了的木簪子。春杏也差不多,主仆俩活脱脱两个乡下土妞。
“这位可是欧阳宝林?”太监拖着长腔问,那调子,听得人耳朵痒痒。
我拍了拍手上的土,站直了:“是我。公公有事?”
太监清了清嗓子,脸上笑容更盛,却透着一股子假:“恭喜欧阳宝林!贺喜欧阳宝林!皇上有旨,宣宝林即刻前往养心殿侍寝!”
“啥玩意儿?”我怀疑自己耳朵被太阳晒坏了。
春杏手里的野菜“啪嗒”掉在地上,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
侍寝?!
这两个字像平地一声雷,炸得我脑瓜子嗡嗡的。皇帝?那个胡子花白、走路都打晃的老头儿?他后宫佳丽三千,环肥燕瘦,争奇斗艳,排着队等他翻牌子呢!怎么会想起我这个在冷宫发霉快两年的咸鱼?
荒谬!太荒谬了!
那太监还在等着我谢恩,或者激动得晕过去?可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行!绝对不行!我这冷宫咸鱼当得好好的,逍遥自在,凭什么要去伺候一个糟老头子?想想那画面……呕!
“公公,”我强压下胃里的翻腾,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您看我这……蓬头垢面的,身上还一股子土腥味,怎么敢去污了皇上的眼?再说,我这清辉阁偏远,消息闭塞,怕是……怕是身子也不大好,万一过了病气给皇上,那罪过可就大了。”
我一边说,一边赶紧给春杏使眼色。春杏这丫头关键时刻脑子转得飞快,立刻捂着嘴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得撕心裂肺,小脸通红,还偷偷掐了自己大腿一把,眼泪都飚出来了:“咳咳咳……娘娘……您这风寒还没好利索……咳咳咳……”
太监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狐疑地上下打量我:“病了?可咱家瞧着宝林气色……尚可?”
“哎呀公公您是不知道,”我立马扶着额头,身子晃了晃,做出一副弱柳扶风的模样,“我这病啊,是内里的,一阵阵的,看着没事,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起不来身了。前些日子还烧得说胡话呢,是吧春杏?”
“是是是!”春杏咳得喘不上气,连连点头,“烧得可厉害了!嘴里直念叨……念叨……”她卡壳了。
我赶紧接上,眼神飘忽,声音放得又轻又虚:“念叨……先帝爷……说地下……凉……”
“嘶——”那太监倒抽一口冷气,脸上的假笑彻底挂不住了,看我的眼神瞬间变了,像是看到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
宫里最忌讳什么?晦气!尤其还是涉及先帝的晦气!我这“烧糊涂了”念叨先帝,还说什么“地下凉”,这往大了说,就是跟死人沾了边,是大不敬!往小了说,那也是极其不吉利!
太监的脸白了又青,青了又白,眼神在我和春杏之间来回扫视,充满了惊疑不定。他大概在权衡,是强行把我这个“病气缠身又带晦气”的女人拖去皇帝面前邀功风险大,还是回去复命说人病了风险大。
显然,前者风险更大。万一皇帝真沾了晦气或者过了病气,他十个脑袋也不够砍的。
“这个……这个……”太监搓着手,明显慌了神,“宝林既然凤体违和,那……那咱家这就回去禀明皇上。宝林好生将养,好生将养……”他一边说,一边带着两个小宫女,几乎是落荒而逃,生怕走慢了沾上晦气。
破门“哐当”一声关上,院子里恢复了死寂。
我和春杏对视一眼,同时长长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后背都汗湿了。刚才那番表演,简直耗尽了毕生的演技。
“娘娘!您刚才……可吓死奴婢了!”春杏拍着胸脯,心有余悸,“念叨先帝……这话也敢说!”
我瘫回我的破竹椅,感觉像打了一场硬仗,浑身脱力。“不说点狠的,能吓跑他吗?”我抹了把额头的虚汗,“侍寝?开什么玩笑!我这小身板,经不起折腾。还是躺这儿晒太阳舒服。”
春杏忧心忡忡:“可……可娘娘,咱们今天糊弄过去了,万一……万一皇上他……”她没敢往下说。
“万一他惦记上我了?”我嗤笑一声,抓起旁边缺了口的茶壶灌了口凉水,“放心吧,老头儿记性不好,后宫美人又多,过两天就把我这号人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再说了,我刚才那‘病’和‘晦气’,够他膈应一阵子的。”
话是这么说,我心里其实也有点打鼓。皇帝的心思,谁能说得准?我这清辉阁,怕是消停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