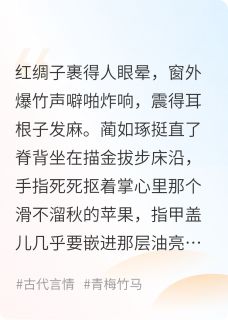红绸子裹得人眼晕,窗外爆竹声噼啪炸响,震得耳根子发麻。
蔺如琢挺直了脊背坐在描金拔步床沿,手指死死抠着掌心里那个滑不溜秋的苹果,
指甲盖儿几乎要嵌进那层油亮的红蜡里去。金丝银线绣的百子千孙被褥硌着腿,
沉甸甸的凤冠压得脖颈又酸又僵。她微微侧了侧头,听着外头喧嚣渐歇,心里那点烦躁,
像泼了油的火星子,呼啦一下全燎了上来。门轴“吱呀”一声**,被推开了。
冷冽的夜风裹挟着一股浓烈的酒气猛地灌进来,冲散了满室甜腻的熏香。脚步有些虚浮,
踩在猩红的地毯上,发出沉闷的声响。蔺如琢没动,红盖头沉沉地垂在眼前,
遮住了所有光亮,只余下一片刺目的猩红。那脚步声在离床几步远的地方停住了,
带着明显的迟疑,空气瞬间凝滞,只剩下两人极力压低的呼吸声,
在偌大的新房里针锋相对地交错着。沉默像一块冰冷的石头,重重压在两人之间。“呵,
”一声短促的冷笑突兀地撕破了寂静,是祁砚之的声音,带着酒后的微哑和毫不掩饰的嘲讽,
“蔺大**,委屈你了?坐得这般僵硬,倒像是上刑场。”那熟悉的、针尖对麦芒的腔调,
像根细针,精准地刺破了蔺如琢紧绷的神经。她猛地抬手,一把将沉甸甸的红盖头扯了下来。
金丝流苏扫过脸颊,带着一丝凉意。眼前骤然明亮,红烛高烧,映得满室金红,
也映亮了她对面那人一身同样刺眼的大红吉服,和那张清俊却写满疏离与不耐的脸。
祁砚之斜倚在门边不远处的紫檀雕花圆桌旁,身姿看似随意,
骨节分明的手指却用力扣着桌沿,指节微微泛白。他眼睫低垂,
浓密的阴影遮住了眼底的神色,薄唇紧抿着,唇线绷得像一把出鞘的刀。
烛火跳跃在他轮廓分明的侧脸上,一半明亮,一半深陷在阴影里,透着拒人千里的冷硬。
憋了一整天的火气“噌”地顶到了嗓子眼。蔺如琢“嚯”地站起身,
凤冠上的珠翠一阵急促地叮当作响,像是她此刻被怒火撞击的心跳。她几步冲到祁砚之面前,
仰起头,几乎能看清他低垂的眼睫在烛光下投下的细小阴影,还有他下颌绷紧的线条。
“祁砚之!”她声音不大,却字字带刺,像淬了冰,“你娶我,是不是憋屈得紧?
连合卺酒都懒得喝一口,是怕沾了我的晦气?”祁砚之终于抬起了眼。那双眼眸深黑,
如同不见底的寒潭,清晰地映出她因愤怒而涨红的脸颊和燃着火焰的眸子。
他嘴角极其缓慢地向上牵了一下,勾出一个毫无温度、近乎刻薄的弧度。“是。
”他吐字清晰,声音冷得像窗外的夜风,“憋屈得很。
若非祖父临终遗命难违……”他顿了顿,目光在她脸上转了一圈,带着一种审视器物的漠然,
“你以为,我会站在这里?”“遗命?”蔺如琢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
胸腔里翻涌着酸楚和屈辱,却硬生生被倔强压了下去,化作更锋利的刀刃,
“好一个孝子贤孙!祁砚之,你这辈子,也就只会抱着块死人的牌位过日子了!
”祁砚之眼底骤然卷起风暴,扣着桌沿的手猛地收紧,指节发出轻微的“咔”声。
他倏地欺身向前,高大的身影瞬间笼罩下来,带着浓重的压迫感和酒气。
蔺如琢下意识想后退,脚跟却钉在原地,梗着脖子,
毫不示弱地迎上他近在咫尺的、翻涌着怒意的目光。“那你呢?”他压低了嗓音,
每个字都像从齿缝里磨出来,“蔺如琢,你嫁我,难道不是因为你那急于攀附祁家的爹?
我们,”他唇边的冷笑更深,带着残忍的洞悉,“半斤八两。”空气凝固了,
只剩下红烛燃烧时细微的滋滋声。两人离得太近,鼻息几乎纠缠在一起,
目光在空中凶狠地厮杀、碰撞,溅出无形的火花。愤怒、不甘、被戳穿的难堪,
还有那深埋在心底、连自己都不愿承认的、被命运摆布的无力感,在这一刻,
如同滚烫的岩浆,在两人之间无声地沸腾、灼烧。僵持,仿佛没有尽头。
祁砚之的目光沉沉地扫过她紧抿的唇和喷火的眼睛,
最终落在那对摆在圆桌中央、用红绸系好的合卺杯上。他忽地伸手,
动作带着一种决绝的粗暴,一把抓起其中一只玉杯。“既是祖父遗命,该走的过场,
总要走完。”他声音恢复了之前的冰冷,不再看她,只盯着杯中晃动的琥珀色液体。
蔺如琢心头那股邪火被这话彻底点燃。她猛地抬手,狠狠拍向他握着酒杯的手腕!“啪!
”清脆的碎裂声骤然炸响,撕裂了新房里虚假的寂静。
冰凉的酒液和细小的玉杯碎片飞溅开来,有几滴溅在蔺如琢的手背上,刺骨的冷。
那只精致的合卺杯,已然摔落在地毯上,裂成几块不规则的残片,浸在深色的酒渍里,
狼狈不堪。祁砚之的手僵在半空,腕骨处被她的指甲刮出两道刺目的红痕。
他缓缓地、缓缓地抬眼,看向蔺如琢,眼神阴沉得能滴出水来。蔺如琢胸口剧烈起伏,
看着地上那摊狼藉,又抬眼迎上他那山雨欲来的目光,
只觉得一阵莫名的快意和更深的空茫席卷上来。她用力吸了一口气,挺直背脊,
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却异常清晰:“祁砚之,我蔺如琢这辈子最后悔的,
就是当年在书院后山,没把你一脚踹进那水潭里淹死!”说完,她猛地转身,
裙裾带起一阵风,决绝地朝着内室的屏风后走去,将那满室狼藉和身后男人冰冷噬人的目光,
一同隔绝在外。日子像水磨盘,吱吱嘎嘎地碾着,竟也碾过了小半年。那夜摔碎的合卺杯,
如同一个不祥的预兆,将本就疏离的两人彻底分割开来。祁砚之的书房成了他的堡垒,
蔺如琢则固守在正房这一隅天地。除了初一十五去祁家老宅给老夫人请安时,
两人不得不硬着头皮装出几分相敬如宾的假象外,其余时刻,
他们如同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陌路人。偶尔在回廊下、庭院中狭路相逢,
也不过是眼神冷漠地一触即分,连唇舌都懒得再动。这日午后,窗外难得放晴,
几缕温吞的日光透过雕花窗棂斜斜地洒进来,在光洁的金砖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蔺如琢正坐在临窗的罗汉榻上,有一搭没一搭地翻着一卷话本子,
心思却全然不在那些才子佳人的故事上。贴身丫鬟青杏轻手轻脚地进来,
手里捧着一个打开的锦盒,脸上带着几分欲言又止的兴奋。“少夫人,”青杏压低声音,
凑近了些,“方才前院送来的,说是新得了几方上好的徽墨。管事知道少爷今日不在府里,
就……就送到您这儿来了。”她小心翼翼地觑着蔺如琢的脸色。蔺如琢的目光从话本上抬起,
落在锦盒里那几方乌黑润泽、泛着幽光的墨锭上,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祁砚之的东西?
她下意识地想挥手让拿走,话到嘴边却又咽了回去。指尖无意识地捻着书页的一角,半晌,
才淡淡开口:“搁书房条案上吧。”她终究还是那个蔺如琢,即便心里堵着气,
该有的分寸,也不会丢。“是。”青杏应了,捧着锦盒退了出去。书房在正房东侧,
穿过一道小小的月洞门便是。蔺如琢在榻上又枯坐了片刻,
直到那卷话本子上的字一个也看不进去,才起身,慢悠悠地踱了过去。书房里很静,
弥漫着淡淡的、熟悉的墨香和旧书纸张的味道。紫檀木的大书案上堆着些卷宗和摊开的书,
略显凌乱。她一眼就看到了青杏刚放下的锦盒,端端正正地摆在条案一角。她走过去,
拿起一方墨锭在手中掂了掂,触手温润微凉。目光随意地扫过桌面,落在那方厚重的端砚旁。
砚台旁边,靠墙立着一个多宝格,
上面错落摆放着一些书籍、卷轴和几件看着颇为古旧雅致的文房清玩。其中一个格子里,
孤零零地放着一个青瓷小瓶,瓶口塞着软木塞。鬼使神差地,蔺如琢伸出手指,
轻轻碰了碰那个看起来格格不入的小瓷瓶。指尖传来冰凉的触感。她犹豫了一下,
好奇心终究占了上风,小心地将它拿了起来。瓶子很轻,里面似乎没装什么液体。
她拔开软木塞,往里瞧了瞧,空空如也。正要放回去,瓶身倾斜时,
瓶底却似乎有什么东西轻微地动了一下。蔺如琢的心莫名一跳。她将手指探进瓶口,摸索着,
指尖很快触到一个微小的凸起。轻轻一按。“嗒。”一声极轻微的机械弹响。
旁边那看似浑然一体的紫檀木多宝格侧板,竟无声无息地滑开了一线,
露出一个巴掌大的狭长暗格。暗格里没有金银珠玉,没有机密文书,
只静静地躺着一支竹蜻蜓。竹片早已褪尽了青翠,呈现出一种干枯黯淡的深褐色,
边缘磨损得厉害,布满细小的裂纹,连那根用来捻转的竹柄也歪歪扭扭,仿佛随时会断裂。
它静静地躺在那里,像一个被遗忘在时光角落里的旧梦。蔺如琢的呼吸骤然停滞了。
她认得它。那还是好多年前的事了。春日里,祁家祖父不知从何处得了些稀罕的湘妃竹,
兴致勃勃地亲手削制了几只精巧的竹蜻蜓。她一眼就相中了其中飞得最高的那只,
偏偏祁砚之也看中了。两人争抢起来,谁也不让谁。她气急,趁他不备一把夺过,转身就跑,
得意洋洋地举着战利品在山坡上炫耀。脚下却不知被什么绊了一下,整个人失去平衡,
骨碌碌就滚了下去。竹蜻蜓脱手飞出,她顾不上浑身摔得生疼,连滚带爬地扑过去捡。
膝盖和手肘**辣地疼,泥土沾了满脸,眼泪混着灰土往下淌,狼狈不堪。
她死死攥着那只摔歪了叶片的竹蜻蜓,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还抽抽噎噎地骂他是“祁小狗”。
后来,她赌气地用簪子尖,在竹蜻蜓的叶片背面,
歪歪扭扭、用尽全力地刻下了几个字——祁砚之是小狗。彼时少年祁砚之站在坡上,
看着她的狼狈样,脸上又是气恼又是无奈,最终也只是绷着脸把她拉了起来,
拍掉她身上的草屑,嘴里却依旧不饶人地嫌弃她“哭得鼻涕泡都冒出来,丑死了”。
记忆的潮水汹涌而至,带着旧日青草与泥土的气息,瞬间淹没了她。蔺如琢指尖颤抖着,
小心翼翼地拿起那支轻飘飘、仿佛一碰即碎的竹蜻蜓。岁月的侵蚀让竹片脆弱不堪,
她屏住呼吸,将它翻转过来,目光急切地搜寻着叶片背面。那行刻痕还在!历经岁月磨砺,
字迹已经模糊得几乎难以辨认,
但笔画间那熟悉的、属于她自己的、带着一股子不服输的稚拙力道,却穿透了时光的尘埃,
清晰地烙印在眼前——“祁砚之是小狗”。指尖抚过那凹凸不平的刻痕,
蔺如琢只觉得心头被什么东西猛地撞了一下,又酸又胀,一股难以言喻的热流直冲眼底。
她下意识地将竹蜻蜓翻回正面,目光无意识地扫过那片磨损得最厉害的叶根处。那里,
在深褐色的竹纹缝隙里,似乎还藏着些更细微的痕迹?她凑近了些,
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光线仔细辨认。就在她刻下那行“小狗”的旁边,极其隐蔽的角落,
几道同样深深浅浅、却明显更为细密沉稳的刻痕,组成了另外三个字——“配蔺小虎”。
蔺小虎……那是她幼时撒泼打滚、爬树掏鸟蛋,像个野小子时,他给她起的浑名。
那时她气得追着他打,他却边跑边笑,说“蔺如琢”这名字太文气,
配不上她这虎虎生风的架势。“配蔺小虎”……蔺如琢死死盯着那四个字,
指尖用力抠着冰凉的竹片,几乎要嵌进去。一股巨大的荒谬感夹杂着说不清道不明的震颤,
从指尖蔓延至四肢百骸,让她几乎站立不稳。他是什么时候刻上去的?
是在她摔下山坡哭得惊天动地之后?是在他们无数次争吵斗嘴的间隙?
还是……在那些被她忽略掉的、他沉默不语的瞬间?竹蜻蜓冰冷的触感透过指尖传来,
却像烙铁一样烫着她的心。她猛地将它按回暗格深处,像被烫到一般缩回手,
用力将那块滑开的侧板推回原位。青瓷小瓶被她胡乱塞回多宝格,发出轻微的磕碰声。
书房里静得可怕,只有她自己擂鼓般的心跳,一下下撞击着耳膜,震得她头晕目眩。
她几乎是逃离般地快步走出书房,砰地一声带上了门,背脊紧紧抵在冰凉的门板上,
大口喘着气,试图平复那汹涌而来的惊涛骇浪。窗外,天光不知何时已暗沉下来,
铅灰色的云层低低压着,酝酿着一场蓄势待发的风雪。夜色渐浓,祁府正堂灯火通明,
人声喧沸。除夕守岁宴席已近尾声,杯盘狼藉,空气中弥漫着酒肉和脂粉的混合气味。
主位上的老夫人面带倦色,却强撑着精神,含笑看着满堂儿孙。祁砚之坐在下首,
一身深青锦袍,衬得他面色在烛火下显得有些过分的苍白。他面前杯盏里的酒水,
不知被谁殷勤地添满了又空,空了又添,往复多次。蔺如琢坐在女眷席中,
隔着攒动的人头和缭绕的烟雾,目光几次不由自主地飘向祁砚之的方向。
他端坐的姿态依旧一丝不苟,只是握着酒杯的手指关节微微发白,偶尔抬手饮酒时,
动作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迟滞。她想起那支藏在暗格里的破旧竹蜻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