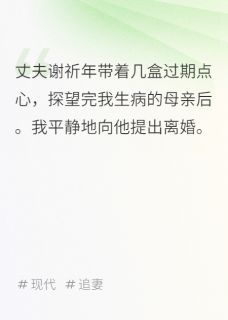丈夫谢祈年带着几盒过期点心,探望完我生病的母亲后。我平静地向他提出离婚。
他难以置信地瞪着我:“就因为几盒过期点心?你闹够了没有!”“你要是觉得没面子,
我明天把整个商场搬到咱妈病房里去!”我没理他,径直走向停车场。直到走到车前,
我才开口反问他:“谢祈年,结婚五年,你真以为我会因为那几盒点心,就跟你提离婚吗?
”而此刻,副驾驶车窗摇下来。他的娇艳小秘书正坐在我的专属位置上,举着小镜子补口红。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心死也从来不是一瞬,都是一件件小事堆积而成。
1我拉开后座的车门,面无表情地坐进去。谢祈年从后视镜里看我,眉头紧锁。“夏澜,
你非要这样吗?”“几盒过期点心而已,反正发现得早没吃,有必要闹成这样?
”他发动车子,语气里带着明显的不耐烦。“都结婚五年了,
还因为这些小事把离婚挂在嘴边,你不累我都累了。”我一个字都懒得说。因为,
我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这时,副驾驶上的秘书许简一开口道:“祈年,
你别这么说嫂子,嫂子也是为了阿姨的身体好,关心则乱嘛。”她说着回过头,
对我露出一个善解人意的微笑。“嫂子,你别生祈年的气,他就是太忙了,
下次我帮他仔细检查,保证不会再出这种错了。”我扯了扯嘴角,没看她,
视线依旧落在窗外,淡然道:“许秘书,你手伸得真长,连我家的事都要管。
”许简一的脸色僵了一下,随即委屈地看向谢祈年。谢祈年立刻维护道:“夏澜!
你怎么说话的?简一是好心。”我终于回过头,冷冷地看着后视镜里他的眼睛。“好心?
那我是不是还要谢谢她,八年长跑没上位,现在来我的婚姻里做慈善?”“你!
”谢祈年的脸瞬间涨红。车子猛地一个急刹,停在了小区门口。“你简直不可理喻!
”“公司还有个紧急会议,我没时间跟你吵!”说完,他便带着许简一,驱车扬长而去。
我站在原地,看着车尾灯彻底不见,却没有上楼。一年前,也是这样一个夜晚。
谢祈年告诉我,许简一来公司面试了,他想让她当自己的秘书。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澜澜,我欠她的。当年是我对不起她,现在她有困难,我不能不管。”是啊,
他欠她的。他欠了她八年的青春,所以要用我们婚姻的安稳去偿还。那我呢?
我这五年的付出,又算什么?一阵冷风吹来,我裹紧了身上的大衣,转身走向路边,
拦下了一辆出租车。“师傅,去市一院。”……我独自坐在医院冰冷的长椅上,
手里紧紧攥着一张薄薄的报告单。“早孕,6周+。”我子宫壁薄,
医生早就断言我很难受孕。结婚五年,我喝了多少苦死人的中药。做了多少次检查,
肚子却始终一点动静都没有。我甚至都快放弃了。可偏偏在这个时候,
在我对谢祈年、对这段婚姻彻底死心的时候,这个孩子来了。
我的手开始不受控制地微微颤抖,纸张被我捏得起了皱。
我曾多渴望能有一个我和谢祈年的孩子,可绝不是现在。2我拿出手机,
指尖悬在谢祈年的号码上,久久没有按下去。鬼使神差地,我点开了朋友圈。最新的一条,
是许简一在三分钟前发的。照片是在一家格调高雅的西餐厅。她亲昵地靠在一个男人怀里,
男人只露出一只手臂,揽着她的肩。那只手臂上,戴着一块表。我的呼吸,
在那一瞬间停滞了。那是我爸的遗物。结婚那天,我哭着亲手给谢祈年戴上。告诉他,
这是我爸留给我唯一的念想。他当时握着我的手,郑重地向我承诺:“澜澜,你放心。以后,
我会替岳父那一份,加倍地爱你,保护你。”那时我真的信了。我信他会像我父亲一样,
成为我一生的依靠。可现在,他戴着我父亲的手表,抱着别的女人,
在高级餐厅里享受着浪漫的烛光晚餐。而这个妻子,正一个人坐在冰冷的医院里。
手里攥着我们孩子的孕检单,像个天大的笑话。我自嘲地扯了扯嘴角。收起手机,
将孕检单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包的最深处。然后我平静地走出医院,拦了车回家。
打开家门,一片漆黑。我没有开灯,借着窗外透进来的月光,
一眼就看到客厅墙上挂着的那副画。画上,一个温柔的男人和一个美丽的女人,
中间牵着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一家三口,在草地上幸福地笑着。这幅画,
是谢祈年带回来的。结婚第二年,我开始积极备孕。中药喝了一碗又一碗,
检查做了一遍又一遍。可我的肚子,始终没有任何动静。那段时间我变得格外焦虑和敏感,
常常半夜躲在被子里偷偷地哭。有一天,谢祈年下班回来,神秘兮兮地拿回这幅画。
他将我揽在怀里,指着画对我说:“澜澜,别着急,你看,这不就是我们的以后吗?
”“医生都说了,我们身体没问题,只是缘分还没到。你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为了让我宽心,他还陆陆续续买了很多婴儿用品。小小的衣服,软软的鞋子,
还有各式各样的玩具,堆放在了家里的储物间。他告诉我:“你看,东西我都准备好了,
万事俱备,只欠我们的小宝贝了。”“所以,任何时候都不晚。”可如今,这幅画在我眼里,
却显得无比讽刺。泪水打湿枕畔,不知不觉间,我沉沉睡去。3半夜一阵动静将我吵醒,
我看了一眼手机,凌晨一点。我起身来到客厅,门被推开。一股浓烈的酒气扑面而来。
谢祈年搀扶着烂醉如泥的许简一走了进来。他看到我,愣了一下,随即开口解释。
“怎么还没睡?”“简一今晚替我挡了不少酒,喝多了。她没带家门钥匙,
一个女孩子住酒店我不放心。”“就在家里住一晚,你别太介意。”我没什么反应,
甚至懒得掀起眼皮看他们。这种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就在我准备转身回房时,
视线无意中扫过他的手腕。我父亲留下的那块表,不见了。我猛地抬起头,走到他面前。
“你的表呢?”谢祈年顺着我的目光看了眼手腕,脸上没有丝毫在意。“哦,那个啊。
”“简一说我,好歹也是上市企业老板。那块表太老太破了,戴着不符合我现在的身份。
”“说要给我重新挑一块配得上我的。”我感觉一股凉气从脚底直冲天灵盖,
浑身的血液都像是被冻住了。转向那个醉倒在他怀里的女人,声音发紧。“许简一,
你把我爸爸的表弄哪儿去了?”“夏澜!”谢祈年立刻拦在我面前,眉头紧锁,一脸不悦。
“她都喝成这样了,你跟她计较什么?让她先休息,有什么事明天等她醒了再说!
”那是父亲留给我唯一的东西。也是我准备在离婚后,从这个家里带走的唯一的东西。
“不行,今天一定要找到!”谢祈年的耐心终于耗尽,他一把将许简一扶到沙发上,
转过身来呵斥我。“你闹够了没有?夏澜!不就是一块破表吗?你非要拿这个当借口跟我吵?
”他的眼神里充满鄙夷和不耐,像是看一个无理取闹的疯子。“我知道,
你不就是因为这么多年都没怀上我的孩子,心里有了危机感吗?”“怕我不要你了?
所以才用各种事情来博取我的关注?”“我告诉你夏澜,别这么敏感,也用不着自卑。
”“我谢祈年是个有责任感的男人,还不至于因为你生不出孩子,就跟你离婚!”4说罢,
他要去给许简一煮醒酒茶。我没有动,也没有回房,就那么坐在许简一对面的沙发上,
毫无困意。谢祈年进了厨房,我听着里面传来烧水的声音。客厅里,
只剩下我和沙发上那个还在装醉的女人。过了一会儿,许简一的眼睫毛动了动,缓缓睁开眼。
她坐直身子,揉了揉太阳穴,脸上哪还有半分醉意。立刻换了一副嘴脸,看着我,
眼神里满是轻蔑和挑衅。“夏澜,演戏演了这么久,不累吗?”我懒得跟她废话,
只想找到我爸的东西。“表在哪儿?”她嗤笑一声,靠在沙发上,好整以暇地打量着我。
“你一个下不了蛋的母鸡,守着这个空房子,守着一个不爱你的男人,一定很寂寞吧?
”她的视线转向墙上那副画,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看到那幅画了吗?好看吧?
”“那是当年我和祈年热恋时,我亲手画的,画的是我们的未来。”我的心跳,
在那一刻像是骤停一般。原来,我视若珍宝的未来,不过是他们早已画好的过去。
我压下心头翻涌的恶心感,只想拿回我唯一的东西。我冷着脸,一字一句地重复。“我问你,
表在哪儿?”“丢了。”“一块生了锈的破表,戴着都掉价,早就该扔了。”她说着,
目光在我身上上下扫视。“就像某些不健全的人一样,也该被丢掉。
”我脑子里那根紧绷的弦,彻底断了。“啪!”我用尽全身力气,一巴掌狠狠扇在她脸上。
她被打得偏过头,脸上瞬间浮起五个清晰的指印。她捂着脸,难以置信地瞪着我,
随即尖叫起来。“夏澜!你敢打我!”而后疯了一样扑过来,抓我的头发,挠我的脸。
我们两个纠缠在一起,就在这时,我突然感觉脑袋一沉。天旋地转间,我站立不稳,
向后倒去。“砰”的一声,一个玻璃杯在我头上炸开。滚烫的液体顺着我的头发流下来,
烫得我皮肤生疼。我还没回过神,就看见谢祈年冲过来一把抓住我的头发,将我从地上扯开。
紧接着,一只脚狠狠地踢在我的小腹上。我眼前一黑,撕心裂肺的剧痛从小腹处炸开。
我疼得蜷缩在地上,浑身都在发抖,冷汗浸透了我的衣服。谢祈年却看都没看我一眼,
小心翼翼地扶起许简一,声音里满是心疼。“简一,你没事吧?有没有伤到哪里?
”他安抚好许简一,才转过头,居高临下地看着在地上颤抖的我。“别装了,
我没用多大力气。”他打开大门,冰冷的雨点混着寒风灌了进来。“滚出去好好反省一下!
”“什么时候知道错了,跟简一道了歉,再滚回来!”门外的世界,瓢泼大雨,电闪雷鸣。
我捂着剧痛的肚子,看着他冷酷的侧脸。心里最后一点念想,也随着那穿堂而过的冷风,
彻底熄灭了。我承认,谢祈年心里,从来没有我。我颤颤巍巍地从地上爬起来,一步一步,
走出这个我曾以为是家的牢笼。冰冷的雨水瞬间将我浇透,我强忍着小腹的坠痛,
在小区门口的路灯下,发疯似的寻找着。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终于在泥水里,摸到了那块表。
我把它紧紧攥在手心,借着微弱的灯光看去。表盘的玻璃碎了,里面的指针,
也永远地停住了。我再也撑不住,靠着路边的树干滑坐在地,从口袋里摸出湿透的手机。
我找到一个号码,拨了过去。电话很快被接通:“澜澜?这么晚了,怎么了?
”是父亲生前的战友,秦叔。我的眼泪,终于决堤。“秦叔……”我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他不要我了……他把我爸的表也弄丢了……”“秦叔,你帮帮我……”“带我走,
带我离开这个地方,我一分钟都不想再待了。”电话那头的秦叔沉默了几秒,
随即是压抑着怒火的声音。“好孩子,别怕,秦叔在。”“我马上派人过去接你!你等着我!
”挂了电话,我紧绷的神经彻底松懈下来。眼前一黑,彻底失去了意识。5再次睁开眼,
我已经在医院了。秦叔坐在床边,熬红的双眼写满了心疼和愤怒。“澜澜,你醒了?
现在感觉怎么样?”我动了动干涩的嘴唇,还没发出声音。病房门被推开,
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走了进来。他看了一眼我的病历,神情严肃。“病人这次算运气好,
送医及时。”“再晚一点,大出血可就不是流产这么简单了,你命都可能保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