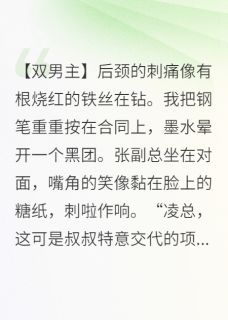【双男主】后颈的刺痛像有根烧红的铁丝在钻。我把钢笔重重按在合同上,
墨水晕开一个黑团。张副总坐在对面,嘴角的笑像黏在脸上的糖纸,刺啦作响。“凌总,
这可是叔叔特意交代的项目,您不签,怕是说不过去吧?”他指尖敲着桌面,
金戒指反光晃得我眼疼。我没抬头,左手悄悄摸向抽屉里的止痛药。
三年前那场“意外”留下的旧伤,最近总在阴雨天发疯。“签不了。
”我的声音比中央空调的风还冷。张副总嗤笑一声,俯身凑过来,
呼吸里的酒气喷在我手背上:“凌辰,别给脸不要脸。你以为这总裁位置坐得稳?
你爸要是没死……”“闭嘴。”我猛地攥紧拳头,后颈的疼瞬间窜到太阳穴。门被推开时,
我正疼得眼前发黑。一个影子堵在门口,逆着光看不清脸,只能看到宽肩窄腰,
黑色运动背心勒出的肌肉线条像刀刻的。空气里突然多了股阳光晒过的味道,
混着淡淡的消毒水味,把张副总的酒气冲得一干二净。“凌总,我是沈燃。
”男人的声音像磨砂纸擦过木头,低得发沉。
张副总显然没把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健身教练放在眼里,斜着眼上下打量他:“哪来的?
不知道凌总在谈公事?”沈燃没理他,径直走到我办公桌前。他太高了,
站在我面前像一堵墙,把顶灯的光都挡了大半。我被迫抬头,
正好对上他的眼睛——黑得像深潭,扫过我脸时顿了顿,又落回我僵硬的后颈。
“先处理你的伤。”他丢下这句话,弯腰从背包里掏出个筋膜枪。张副总不乐意了,
拍着桌子站起来:“你算什么东西?敢在某集团指手画脚……”沈燃突然转头看他,
眼神冷得像淬了冰。就一眼,张副总的话卡在喉咙里,脸涨成了猪肝色。“出去。
”我对张副总说,声音哑得厉害。他还想说什么,沈燃已经把筋膜枪插上电,
嗡嗡的低鸣声里,张副总灰溜溜地走了,关门时的力道差点把墙上的挂画震下来。
办公室里只剩我们俩。沈燃把椅子拉到我身后,距离近得能闻到他身上的味道——不是香水,
是皂角混着汗水的味道,干净得让人发慌。“低头。”他说。我没动。活了二十八年,
除了我爸,还没人敢用这种命令的语气跟我说话。后颈的刺痛突然变本加厉,我闷哼一声,
差点从椅子上滑下去。沈燃的手快得像闪电,一把按住我的肩膀。他的指尖没碰到我,
只是虚虚地悬在衬衫布料上,却像有电流窜过来。我浑身一僵,
听见他说:“这伤不光是累的吧。”我猛地抬头,撞进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没有同情,
没有好奇,只有一种了然——好像早就看穿我这副“冰山总裁”的壳子下,
全是没愈合的伤口。“不用你管。”我甩开他的“手”,后背却控制不住地发颤。
沈燃没再逼我,只是把筋膜枪的档位调到最低,枪头离我后颈还有半寸时停住:“放松点,
不然更疼。”他的呼吸落在我后颈,像一小簇火苗,顺着脊椎往小腹钻。
我攥着桌沿的手越收越紧,指节泛白。办公室里只有筋膜枪的低鸣,
还有他偶尔吐出的几个字——“往左一点”“慢点呼吸”。每一次他的声音响起,
我后颈的皮肤就像被烫了一下,又麻又痒。“好了。”他关掉筋膜枪,起身时带起一阵风。
我没回头,盯着桌上那份被我戳烂的合同,突然觉得喉咙发紧。“凌总。”他在我面前站定,
“下次疼得厉害,别硬扛。”我抬头看他。阳光从百叶窗缝里钻进来,
正好落在他锁骨的凹陷处,那里还挂着颗没擦干的汗珠,顺着肌肉线条往下滑,
滑进运动背心的领口,消失不见。我的喉结滚了滚。“工资会按时打给你。”我移开视线,
假装看文件。沈燃笑了一声,那笑声像羽毛搔过心尖:“我不是来赚你工资的。”我愣住。
他已经走到门口,手搭在门把上时回头看我,眼神亮得惊人:“我是来帮你把那些蛀虫,
一个个揪出来的。”我盯着他消失的背影,后颈的疼痛不知什么时候减轻了。
桌上的止痛药还躺在抽屉里,没开封。下午的董事会,叔叔凌志远果然发难了。“小辰啊,
你这身体怎么回事?”他坐在主位上,手指敲着桌面,“连个项目都拿不下来,
是不是该让张副总多分担点?”几个董事跟着附和,声音像苍蝇一样嗡嗡叫。**在椅背上,
后颈的旧伤又开始隐隐作痛,但这次,我没像以前那样低头沉默。我想起沈燃临走时的眼神。
“叔叔说笑了。”我缓缓坐直,目光扫过全场,“张副总今天喝多了,胡言乱语而已。
至于项目——”我从文件袋里抽出另一份合同,“我已经和合作方签好了。
”凌志远的脸瞬间沉了下去。散会后,我刚走出会议室,就看见沈燃靠在走廊的墙上。
他换了件白色T恤,胳膊上的肌肉线条更明显了。“看来不用我出手了。”他挑眉笑了笑。
我没说话,径直走过他身边。擦身而过时,他突然低声说:“晚上七点,我来接你训练。
”我脚步顿了顿,没回头,也没拒绝。回到办公室,我把抽屉里的止痛药全扔进了垃圾桶。
窗外的阳光正好照进来,落在桌面上,暖得像沈燃身上的味道。也许,这座冰山,
真的该融化了。训练室的空调坏了。沈燃的T恤被汗水浸透,贴在背上,
勾勒出流畅的肌肉线条。我趴在训练床上做核心训练,余光能瞥见他弯腰调整瑜伽垫的动作,
每一次俯身,领口垂下的阴影都扫过我的手背。“腰再绷紧点。”他的声音带着喘,
热气喷在我耳后。我猛地收紧腹部,后颈的旧伤却突然抽痛。这种痛跟平时不一样,
像有根针在往骨头缝里扎。我闷哼一声,额头撞在垫子上。沈燃的手立刻伸过来,
停在我后脑勺上方半寸的地方:“怎么了?”“没事。”我撑起身子,冷汗已经浸湿了额发,
“继续。”他没动,盯着我的眼睛看了足足三秒:“凌志远又找你麻烦了?”我心里一震。
昨天董事会上,凌志远借着“优化管理层”的名义,把我亲手提拔的两个部门经理全换掉了,
换成了他的人。我忍了一晚上,以为藏得很好。“不关你的事。”我别过脸,
不敢看他的眼睛。沈燃突然蹲下来,视线跟我平齐。训练室的窗户没关,风灌进来,
掀起他额前的碎发。他的睫毛很长,垂下来的时候在眼睑上投出一小片阴影。“凌辰,
”他第一次连名带姓叫我,声音轻得像叹息,“你不用在我面前装。”我的喉结滚了滚,
刚想说什么,训练室的门被一脚踹开。张副总带着两个穿西装的男人站在门口,
手里拎着个保温桶,笑得一脸油腻:“凌总真是好兴致,
上班时间躲在这里跟教练‘切磋’呢?”沈燃站起来,不动声色地挡在我身前。
他比张副总高出一个头,阴影压过去,正好把对方的脸罩住。“张副总有事?
”沈燃的声音冷下来。“没事就不能来看看凌总?”张副总晃了晃手里的保温桶,
“叔叔特意让家里阿姨炖了汤,给凌总补补身体——毕竟,这身体要是垮了,
有些人可就称心如意了。”他意有所指地瞟了沈燃一眼。我知道这汤不能喝。
凌志远的“好意”,从来都裹着毒药。“放着吧。”我掀开训练垫,起身时动作太急,
旧伤又疼起来,差点踉跄。沈燃的手在我胳膊旁虚扶了一下,指尖擦过我的衬衫袖口。
就这一下,张副总的眼睛亮得像发现了新大陆。“哟,沈教练还挺关心凌总。
”他拍着大腿笑,“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俩……”“滚出去。”我打断他,
声音里的冰碴子能冻死人。张副总脸上的笑僵了,随即又换上一副无赖相:“凌总别生气啊,
我就是开个玩笑。对了,晚上有个酒局,合作方点名要沈教练作陪,说是想请教健身秘诀呢。
”我心里咯噔一下。那帮合作方是什么货色,我比谁都清楚。让沈燃去,等于羊入虎口。
“他不去。”我直接拒绝。“这可由不得你。”张副总掏出手机,点开一段录音,
里面是凌志远的声音:“让沈燃陪王总喝几杯,这事关公司下个季度的合作。
”沈燃突然笑了,伸手扯了扯湿透的T恤领口:“喝几杯?”“不多,也就……一箱吧。
”张副总笑得更得意了,“王总最喜欢跟沈教练这种‘练家子’喝酒了。”我攥紧拳头,
指甲掐进掌心。后颈的疼痛越来越烈,眼前开始发黑。我知道,
这是凌志远的圈套——要么让沈燃被灌死,要么我拒绝,
他就有理由在董事会上说我“因私废公”。“我去。”沈燃突然开口。我猛地抬头看他,
他却没看我,只是盯着张副总:“时间地点发我手机上。”张副总愣了一下,
大概没料到他会答应得这么痛快,讪讪地笑了笑:“还是沈教练懂事。”他们走后,
训练室里只剩我和沈燃。“你不能去。”我咬着牙说,后颈的疼让我说话都费劲。
沈燃拿起毛巾擦脸,水珠顺着他的下颌线往下掉,滴在锁骨窝里:“为什么不能去?
”“他们是故意的!”我提高声音,“王总那个人……”“我知道。”他打断我,
把毛巾扔到架子上,“以前在健身房,我见多了这种人。”我看着他转身收拾东西的背影,
突然觉得无力。我连自己都护不住,更别说护着他了。“别管我了。”我低声说,
“凌家的浑水,你蹚不起。”沈燃停下动作,回头看我。阳光从他身后照过来,
把他的轮廓描成金色。他走过来,离我很近,近到我能看清他瞳孔里的自己——狼狈,懦弱,
像个没长大的孩子。“我不是来蹚浑水的。”他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劲儿,
“我是来帮你的。”那天晚上的庆功宴,我找了个借口提前离席,
开车去了张副总说的私人会所。包厢门没关严,里面传来王总的浪笑:“小沈教练,
再喝一杯!这杯喝完,我跟凌氏的合同立马签!”接着是沈燃的声音,
带着点不耐烦:“最后一杯。”我推开门的时候,正看见王总伸手想去摸沈燃的脸。
沈燃侧身躲开,手里的酒杯“哐当”砸在地上。“给脸不要脸是吧?”王总恼羞成怒,
站起来就要动手。我冲过去,一把将沈燃拉到我身后。王总的手差点打到我脸上,
被我躲开了。“凌总?”王总愣住了,“你怎么来了?”“我的人,你也敢动?”我盯着他,
后颈的疼痛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股烧起来的怒火。王总脸色变了变,
随即又笑了:“凌总别误会,我跟沈教练闹着玩呢。”“我没跟你闹着玩。
”我拿起桌上的一瓶白酒,拧开盖子,对着王总的脸就泼了过去,“现在,给我滚。
”酒液顺着他的头发往下流,滴在昂贵的西装上。王总的脸一阵青一阵白,
指着我半天说不出话。“滚不滚?”我又问了一遍,声音不大,却带着狠劲。
他大概是被我吓住了,撂下一句“你等着”,带着人灰溜溜地跑了。包厢里只剩我和沈燃。
地上全是碎玻璃,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酒气。“你怎么来了?”沈燃的声音有点哑。
“我再不来,你就要被人吃了。”我转身看他,发现他的嘴角破了,
应该是刚才被推搡的时候撞到的。我伸手想碰,又猛地缩回来。沈燃却笑了,
用手背擦了擦嘴角的血:“你刚才那一下,挺帅的。”我没说话,拉起他的手腕就往外走。
他的手腕很粗,肌肉硬得像石头,却在我碰到的瞬间,轻轻颤了一下。车开出去很远,
我才发现自己还攥着他的手腕。他没挣开,就那么任由我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