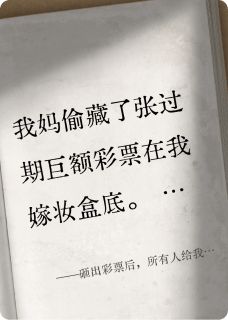我妈偷藏了张过期巨额彩票在我嫁妆盒底。婆家冷眼嘲讽三年,我终于爆发砸了木盒。
彩票飘出瞬间,我妈电话疯响:“千万别动那张废纸!!!”两家疯抢这张“过期宝藏”,
撕打哭嚎如同地狱。我舔舔干裂的嘴唇,在燃烧的火光里轻笑:“都别吵了,谁跪下磕个头,
这堆灰就归谁。”结婚时我妈只给了我一个木盒当嫁妆。那盒子沉得像口小棺材。
我妈塞给我时,眼神躲闪,像抛掉什么烫手山芋。“老物件了,你姥姥传下来的,值钱着呢!
”她嘴上抹蜜,手却推得飞快,仿佛多沾一秒都嫌晦气。就这,一个木头疙瘩,
边角糊着不知哪辈人蹭上的油垢,沉甸甸地压在我衣柜最底层,像我在这家里多余的存在。
三年了。每一天都像钝刀子割肉。“林薇,楼下王阿姨的儿媳,人家又升职了,
一个月这个数!”婆婆翘着兰花指,比划了一个让我眼晕的数字,
视线刮骨刀似的在我身上逡巡,最后钉死在我洗得发白的睡衣上,“哪像有些人,白吃白住,
蛋也下不了几个。”她说的蛋,是指我没能再给张家添个孙子。丫丫是女儿,赔钱货。
公公吭哧吭哧喝着稀饭,呼噜声震天响,算是默许的伴奏。丈夫小杰刷着手机,
眼皮都懒得抬:“妈你跟她废什么话,她就那点出息。
当初要不是看她家要的少……”后面的话被一声嗤笑淹没。只有丫丫,摇摇晃晃走过来,
把一小块啃得湿漉漉的苹果核往我嘴里塞,黑葡萄似的眼睛看着我。
婆婆立刻夸张地叫起来:“哎哟,还是我们丫丫疼人,比你妈那个木头疙瘩强!”三年,
一千多个日夜,这种细碎绵密的痛楚浸透了每一寸骨头缝。他们忘了,我婚前那点工资,
大半填了娘家的坑。我弟的新手机,我爸的酒钱,我妈看中那条金链子。剩下的,
变成了这屋里他们最瞧不上的“破烂”嫁妆。这盒子,是我妈压箱底塞给我的。
她说:“薇薇,妈给你留个好的!”笑容虚浮,像糊了一层劣质的纸。我当时竟信了。
压垮骆驼的,从来不是最后一根稻草,而是之前每一根稻草的冤屈。丫丫夜里起高烧,
额头烫得起疹子。药没了,退烧贴也用光了。我翻遍所有抽屉,连钢镚都算上,
凑不出五十块。婆婆麻将局正酣,电话里不耐烦地吼:“赔钱货就是事多!找你男人去!
”小杰电话关机,不知道又在哪个网吧泡着。我抱着火炉似的孩子,在冰冷的客厅里转圈,
恐慌和绝望像藤蔓勒紧喉咙。视线一次次撞向衣柜底层。就它了。这破盒子,这唯一的,
我妈给的,所谓“念想”。砸了!劈了!看看里面是不是藏着能救我女儿的救命钱。
我把它拖出来,死沉,油污沾了我一手,恶心。我几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把它高高举起,
对着冰冷坚硬的地砖,狠狠砸下去!“哐啷——!”木头碎裂的声音闷哑,不像解脱,
倒像一声痛苦的**。几块侧板崩裂开,里面黑洞洞的。没有金银,
只有一股积年的陈腐霉味扑面而来。一张轻飘飘的纸,随着木屑,晃晃悠悠,荡了下来,
羽毛般落在我脚边。粉色的。巴掌大。上面的数字撞进我眼里,像烧红的烙铁烫了一下。
我猛地闭眼再睁开,心脏骤停一拍,然后疯狂擂鼓,几乎要撞碎胸骨!日期,期号,
那组数字……电视里天天滚播,街角广告牌贴烂了,小杰和他爸做梦都念叨的那组号码!
一期独中,得主神秘消失的亿万巨奖!它就在这儿。藏了三年。在我夜夜安眠的床底下。
在我被唾沫星子淹死的每一天下面。血液轰的一声全涌上天灵盖,耳鸣尖锐刺破鼓膜。
我抖得站不住,扶着冰冷的墙壁才没瘫下去。就在这一刻,我那破旧手机像索命一样炸响。
屏幕上我妈的名字疯狂跳动,带着一种从未有过的、歇斯底里的急促。我接通,
喉咙紧得发不出声。那头是我妈彻底变了调的、尖利到劈叉的嘶吼,
几乎戳破我耳膜:“薇薇!薇薇!你听着!别动那个盒子!千万别砸!里面有张纸!废纸!
一张没用的废纸!千万别碰!等我来!我马上到!你听见没有?!
千万别……”她的声音因为极致的急切,扭曲得像鬼嚎。
我看着手里这张价值亿万、轻得没有重量的纸,看着地上狼藉的碎木片。听见我自己的声音,
平静得像结冰的湖面,裂开一丝纹路:“晚了。”“什么晚了?!什么叫晚了?!
林薇我告诉你你敢动一下我撕了你!那东西是——”我爸抢过电话,咆哮声震得手机嗡嗡响。
背景音里,我弟急躁地吼叫:“跟她啰嗦什么!快打车!不!跑过去!抢时间啊!”晚了。
我已经把它砸开了。电话那头瞬间死寂,然后爆发出更疯狂的、语无伦次的嚎叫和诅咒。
“哐当!”房门几乎是被撞开的。婆婆输光了麻将,脸色铁青地进来:“作死啊!
拆房子还是……”话卡在半道,她的眼睛猛地凸出,死死钉在我手上那张粉色纸片上,
呼吸骤然急促,嘴唇哆嗦得像发了鸡爪疯。“彩……彩……”她“彩”了半天,
猛地发出一声能掀翻屋顶的尖叫,破了音:“老张!小杰!钱!钱啊!!我们的钱!!!
”稀里哗啦——我公公提着裤子从厕所冲出来。小杰手机啪嗒摔地上,屏幕稀碎。三双眼睛,
瞬间烧得通红,贪婪的光几乎凝成实质,钉死在那张纸上,然后猛地转向我,
灼热得能烫伤人。“薇薇!哎哟我的好儿媳!妈的心肝宝贝!”婆婆第一个扑上来,想抱我,
又不敢碰彩票,脸笑成了一朵扭曲的菊花,“妈就知道你有大造化!咱们家全靠你了!
丫丫以后就是公主命!”公公搓着手,语无伦次:“兑奖!现在就兑!
我找我三舅姥爷的侄子在省中心!”小杰一把推开他妈,眼神狂热得吓人,试图搂我,
声音激动得变调:“老婆!你太神了!这惊喜太大了!咱们买别墅!买跑车!
妈的看谁还敢给老子脸色看!”他们围着我,唾沫星子几乎喷到我脸上,
浓郁的、虚假的热情包裹上来,快得令人作呕。刚才的冷漠、刻薄、嫌弃,
被一种极度狂热的、扭曲的谄媚取代,翻脸比翻书还快。丫丫被这阵仗吓得哇哇大哭,
小脸憋得通红。没人看她一眼。他们的世界里,只剩下那张纸。“滚开!那是我姐的东西!
是我们林家的!”我弟的吼声从门外炸响,伴随着咚咚咚砸门般的脚步声。娘家人到了。
我弟一脚踹在门上,哐当巨响:“林薇!开门!彩票是妈存的!是妈的!你给我拿出来!
”“放你娘的屁!”我婆婆反应极快,母鸡护崽般张开手臂挡在我身前。实则是挡住彩票,
尖声回骂,“嫁进张家就是张家的!你们这群穷疯了的吸血鬼滚远点!”“那是我亲姐!
你们家怎么虐待她的?现在有脸要钱?”“抢劫!你们这是入室抢劫!报警!老头子报警!
”“报啊!看警察来了抓谁!这明明是我们家的东西!”两家人,像两群饿红了眼的鬣狗,
在我家狭窄的客厅里撕咬起来。推搡,咒骂,唾沫横飞,面目狰狞。
我弟猛地推了我公公一把,婆婆尖叫着去抓我爸的脸。小杰和我弟扭打在一起,撞翻了餐桌,
碗碟稀里哗啦碎了一地,混合着女人的尖叫声、男人的怒吼声、丫丫撕心裂肺的哭声。
乌烟瘴气,群魔乱舞。我被他们挤在角落,像风暴里的一片烂树叶。
那张彩票被我死死攥在手心,汗浸湿了,指甲掐进肉里,却麻木得感觉不到疼。
我看着我爸脖子上暴起的青筋,看着我媽头发散乱像个疯婆子,
看着婆婆唾沫横飞咒骂我全家,看着小杰为了这张纸和他称兄道弟的舅子往死里抡拳头。钱。
都是因为这纸。这纸能换钱。很多很多钱。能立刻买走亲情,买走脸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