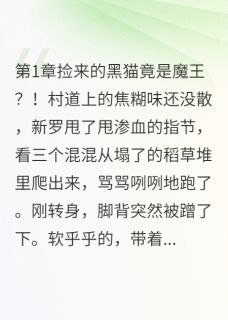王城,寝宫,烛火被夜风撕得只剩豆大,在铜壁上来回爬。新罗披着旧式白袍——不是王袍,
是奴隶穿的粗麻——立在龙榻前。龙榻上的人形几乎被锦被淹没,只剩一张蜡黄的脸。
那是“秀·新罗”,在位三十七年,民间叫他“秀王”。“长生石……找到了吗?
”秀王喉咙里滚出铁锈味。“继承人,我找到了。”新罗抬手,毛毛牵着个孩子走进来。
孩子不足八岁,赤足,脚踝上还有泥。
毛毛把一束象征“退位”的枯发放在枕边——那是毛毛的一小撮头发,蕴藏着契约的力量。
秀王苦笑,用指甲划破自己的掌心。血珠滚落,却没有一点魔力的蓝光。“您早知道了,
对不对?”他抬眼,看向新罗,像看一面照出自己全部谎言的镜子。“我不是秀·新罗,
我只是……一个冒牌货。”新罗的声音低得像自言自语:“真正的血脉,
早在二十年前就死了,痨病。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你不是我和安东尼的血脉。你,
你隔壁屋那孩子,和毛毛都没有契约的魔力痕迹。”她看向那孩子,“就连他,
也不是真正的继承者。”秀王喘得像破风箱:“那您为何还让我坐在这张椅子上三十七年?
”“因为王国需要这个姓氏。”她忽然低笑一声,语气里带着几分自嘲:“很奇怪吧?
‘新罗’曾是我的名字,一个连姓氏都没有的奴隶的孩子。如今,它成了国王的姓氏,
成了所谓的正统。”秀王用尽最后的力气,抓住新罗的袖口。“我……只是害怕死。
当了国王以后,更怕。”新罗抽回手,袖口留下五道血指印。“那就把位置让出来!
王座上不需要怕死的懦夫。”————————————————清晨,番茄地里露水太重,
番茄叶被压得“啪嗒”一声弹回。水精灵伏在无数的叶脉里,像一汪会说话的清水。
新罗脱了鞋,赤脚踩进泥里。泥从脚趾缝挤出,带着昨夜的雨味。“我还是想不明白。
”她对水精灵说,也像对土地说。“他年轻时那么克制、那么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