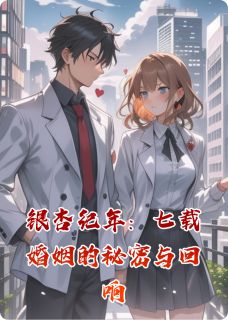第一章:暗涌深秋的上海总被连绵细雨笼罩,像是老天爷忘了关紧的水龙头,淅淅沥沥,
把整座城市都泡得发潮。陆沉站在公寓三十八楼的落地窗前,指尖捏着块麂皮眼镜布,
反复擦拭着镜片上的薄雾。玻璃映出他清瘦的侧脸,眼下的青黑像是被墨汁晕染开的痕迹,
与对面写字楼里零星亮起的灯光相互映衬,那些光点散落在夜幕上,倒像是被揉碎的星屑。
这是他和沈念结婚的第七年。飘窗上的景象早已不是初婚时的模样。
曾经摆满多肉植物的角落,如今被一摞摞文件占领,A4纸的边缘在潮湿的空气里微微卷曲,
像某种蜷缩的生物。最角落里,那盆见证他们初遇的蓝雪花彻底枯死了,
干瘪的枝条纠缠在一起,如同凝固的蛛网。陆沉伸手碰了碰干枯的枝叶,
指尖立刻沾染上褐色的叶脉碎屑,轻轻一吹,便散在风里,了无痕迹。
就像他们之间那些悄悄溜走的时光,连告别都吝啬给予。“叮——”手机屏幕突然亮起,
打破了室内的沉寂。是医院发来的体检报告推送。陆沉深吸一口气,
胸腔里翻涌着说不清的钝痛,指尖在屏幕上滑动,准备点开那个PDF文件时,
手腕却猛地顿住。一阵尖锐的灼烧感从胃部传来,像是有团火在里面炸开,
沿着食道一路蔓延到喉咙,带着铁锈般的腥气。报告单上“胃部间质瘤”五个字,
像一把生了锈的锯子,在他的神经末梢来回拉扯,钝痛中带着撕裂般的尖锐。
他盯着诊断日期看了很久——三个月前,那天正好是沈念母亲的七十大寿。
他记得自己当时借口公司有紧急应酬,其实是独自留在医院做了胃镜检查。
那天走廊里飘着寿桃的甜香,护士递来的麻醉同意书上,他的签名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
地铁穿过黄浦江底的瞬间,车厢里的灯光忽明忽暗。陆沉靠在扶手上,
盯着隧道壁上流动的光影发呆。七年前的这个时候,他们也挤在末班地铁里,
沈念穿着米白色的羽绒服,肩膀时不时蹭到他的胳膊,呼吸间飘来淡淡的茉莉洗发水香味。
那时他刚做完一台失败的手术,整个人都在发抖,是她攥住他的手,
掌心的温度透过薄薄的毛衣渗过来,轻声说:“别怕,我陪你去。”可现在,
他连告诉她真相的勇气都没有。怕看见她眼里的光熄灭,怕那些积攒了七年的安稳,
像摔在地上的玻璃杯,瞬间碎成扎人的碴。推开家门时,玄关处的感应灯应声而亮,
暖黄色的光打在地板上,却驱不散空气中的寒意。沈念正在客厅给绿萝浇水,
细长的手指捏着洒水壶,水珠顺着翠绿的叶脉滚落,在灯光下折射出细碎的光斑。
她的侧脸在逆光里柔和得像幅水墨画,只是眼角的细纹比去年深了些。“今天这么早?
”她转过身,身上的棉布围裙带子扫过料理台,“哐当”一声,碰倒了旁边的盐罐。
白色的晶体星星点点洒出来,落在旁边的结婚照上,
正好盖住了照片里他们头挨着头微笑的嘴角。那是七年前拍的,
那时沈念的眼睛亮得像盛着星光,如今镜片后的目光,总蒙着层化不开的雾。
“项目提前结束了。”陆沉把公文包塞进衣柜,指尖不经意间触到了夹层里那个硬质的信封。
那是上周客户塞给他的,说是某位重要人物的手书,让他务必收好。
此刻信封的边角已经被磨得起了毛边,像一块硌在心口的碎玻璃,怎么都不舒服。
他想起三天前的酒局上,客户醉醺醺地拍着他的肩膀说:“陆医生好福气,
沈**这样的贤内助,打着灯笼都难找啊。”酒气喷在脸上时,
他看见对方眼里一闪而过的暧昧,像根针轻轻刺了下心脏。沈念端出一碗山药排骨汤,
砂锅里腾起的热气模糊了她鼻梁上的金丝眼镜:“你脸色好差,要不要去躺会儿?
”她伸手想摸他的额头,指尖带着刚洗完菜的凉意,却被陆沉下意识地侧身躲开。
这个动作让两人都僵在了原地。沈念悬在半空的手顿了顿,像被冻住的蝴蝶,慢慢收了回去。
手里的汤匙磕在碗沿上,发出清脆的响声,惊醒了趴在窗台打盹的虎斑猫。
猫咪“喵”了一声,纵身跳下窗台,消失在客厅的阴影里,留下满室的寂静,浓稠得化不开。
深夜两点,陆沉在书房核对报表时,鼻尖突然钻进一缕若有若无的檀香。
那是沈念去年去普陀山求来的平安香,他记得她一直放在那个常年锁着的檀木匣里。
他放下笔,鬼使神差地走到卧室的梳妆台前,看着那个雕花的檀木匣。铜锁是虚掩着的,
他轻轻一拧就开了,像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掀开匣盖的瞬间,
一沓泛黄的信笺像雪片般飘落下来。最上面那封的邮戳是三个月前的,
右下角画着一个小小的银杏叶图案——那是他们大学时代在图书馆银杏树下约定的暗号,
只有彼此才懂的标记。那时他总在银杏叶上写情诗,夹在她常看的书里,
她会回赠画着银杏的便签,藏在他白大褂的口袋。“念念,我在老地方等你。
记得带那本《霍乱时期的爱情》。”信纸上的字迹娟秀如初,
和沈念大学时写给他的情书一模一样。陆沉的太阳穴突突直跳,像有只鼓在里面敲。
记忆闪回上周三深夜,沈念说要去参加读书会,
出门时脖子上围着他去年送的那条墨绿色羊绒围巾。当时他还注意到,
她的耳后沾着一片银杏叶,她说是在地铁上捡的。可他分明记得,那天的地铁播报里说,
夜间有七级大风。次日清晨,厨房里传来煎蛋的滋啦声。沈念把煎好的鸡蛋盛进盘子,
突然开口:“我申请了普陀山的禅修营,下周出发。”陆沉握着咖啡杯的手一抖,
褐色的液体溅在摊开的晨报上,晕染开一片深色的痕迹,像朵难看的墨花。
他想起那份诊断书还在公文包的夹层里,像一颗随时会引爆的定时炸弹。
窗外的梧桐叶被风吹得打着旋儿落下,有一片正好落在沈念的发间。他这才发现,
她的鬓角不知何时多了几根银丝,在晨光里泛着淡淡的白,像落了层霜。
结婚时她总说自己不会老,他还笑着说要陪她白发苍苍,原来岁月从不会等谁做好准备。
第二章:裂痕禅修营的第四天傍晚,暮色像一块浸了水的布,沉甸甸地压在普陀山的群峰上。
沈念坐在寮房的蒲团上,小心翼翼地擦拭着案头的佛像。檀香在空气中氤氲,
形成一道道细小的烟柱,缓缓向上飘散,带着清苦的味道,像她心里那些说不出的委屈。
手机屏幕突然亮起,
一条来自陌生号码的短信跳了出来:“陆医生今晚在思南书局有读者见面会。
”后面附着一张照片,是书店的橱窗,玻璃倒影里,
陆沉正低着头给读者签售新书《生命的褶皱》,摊开的书页间露出半截银杏叶书签,
金色的叶脉在灯光下清晰可见。那是她亲手做的书签,去年他生日时送的,
他当时笑着说要永远夹在最重要的书里。沈念的心脏猛地一缩,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了,
疼得喘不过气。她猛地站起身,撞翻了旁边的香炉,黑色的香灰簌簌落在素白的僧袍上,
留下星星点点的痕迹。她顾不上这些,抓起手机就冲出了禅房,僧鞋踩在青石板上,
发出急促的声响,惊飞了檐下的鸽子。跑过七重殿宇时,
手腕上的菩提手串突然“啪”地一声绷断了,檀木珠子滚落石阶,发出清脆的响声,
一路向下滚去,像是在丈量她一点点溃散的信仰。那串手串是陆沉陪她求的,
当时住持说“心诚则灵”,他还笑着把她的手包在自己掌心,说“我们的心意,
菩萨一定听得见”。思南书局的穹顶是玻璃幕墙,映着外面璀璨的城市灯火。
陆沉的声音透过麦克风传来,清晰地落在每个人的耳朵里:“医学有时就像在迷雾中航行,
你不知道前方有暗礁还是风暴,但请相信,总有人会陪着你等天亮。
”他说这话时眼里带着温柔的笑意,像极了当年向她求婚的模样。沈念站在人群外围,
隔着攒动的人头望着他。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衬衫,袖口挽到小臂,低头给读者签名时,
后颈露出一道淡红色的抓痕——那个位置,
和上周她在厨房不小心撞到他时留下的淤青一模一样。那天她伸手去扶他,
指尖触到他皮肤时,他像被烫到般躲开,说“没事,小磕碰”。
一个穿着书局工作服的年轻人走过来,递给她一杯温水:“这位女士,
刚才有位先生说有东西要交给您。”他递过来一个牛皮纸袋。沈念接过纸袋,指尖有些发凉,
像握着块冰。打开一看,里面是撕碎的诊断报告,每一片碎纸上都用钢笔写着“对不起”,
字迹力透纸背,带着深深的无力。最后那片最大的纸上,写着一行字:“下周三的飞机,
我在普陀山等你。”墨迹有些晕开,像是被泪水浸过。暴雨倾盆的午夜,
沈念蜷缩在禅房的角落,浑身都在发抖。窗外的雨砸在屋檐上,噼啪作响,
像无数根鞭子在抽打。手机相册突然自动跳出三年前的视频,
是陆沉在手术室门口狂奔的样子,白大褂的下摆被风吹得翻飞,像一只受伤的鸥鸟。
她点开旁边的语音条,听见自己带着哭腔的声音:“要是手术失败……我就在普陀山出家。
”背景音里还能隐约听到护士的惊呼:“陆医生!3床大出血!”那天她难产,
他在另一个手术室抢救病人,隔着走廊的玻璃窗,她看见他红着眼眶朝产房的方向望了一眼,
又转身冲进了抢救室。窗外的山风突然变得猛烈,撞开了虚掩的雕花木窗,
吹散了案头未燃尽的安魂香。沈念伸手摸向枕头下,
触到一个硬硬的东西——是陆沉去年送她的银杏叶标本,被透明的塑封膜仔细地包着。
她凑近看,发现叶脉间藏着极小的字迹:“等春天来了,带你去日本看千年银杏。
”那是她念叨了很久的心愿,他总说忙,却悄悄记在了心里。眼泪突然就掉了下来,
砸在标本上,晕开一片水雾。第三章:倒影太平间的白炽灯管发出嗡嗡的响声,光线惨白,
照在冰冷的金属台面上,反射出刺眼的光。沈念站在母亲的遗体旁,轻轻抚摸着她冰凉的手。
母亲的手指蜷缩着,像是在临终前攥着什么。指尖划过母亲的无名指时,
她突然顿住了——那里戴着一枚银杏叶形状的戒指,银质的表面已经有些氧化发黑,
但纹路依旧清晰。这枚戒指,和父亲遗物盒里那枚一模一样。父亲去世那年她才五岁,
只记得他总把这枚戒指戴在小指上,说“这是你妈妈送我的定情物”。
二十年前的医疗事故报告从文件袋里滑落出来,“陆远山”三个字像一根针,
猛地刺进她的眼睛。她记得这个名字,母亲生前偶尔会提起,说那是当年给父亲主刀的医生,
语气里总带着说不清的复杂。“令尊是位了不起的外科医生。”陆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他手里拿着一个保温杯,递到她面前,“里面是你母亲爱喝的陈皮茶,我刚泡的。
”他的指尖有些凉,像是刚从外面回来。“他主刀的第三千例手术,是我作为实习生记录的。
”沈念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砸在泛黄的病历本上,晕开一小片水渍。
她翻开1999年9月9日的手术记录,上面写着:“患者拒绝使用进口吻合器,
坚持用国产器械。”下面的签名是父亲的名字,旁边还有一行小字,
是主治医生的批注:“患者家属要求,尊重其意愿。”母亲总说父亲节俭,
原来连生命攸关的时刻,他都在为这个家省钱。他们站在当年医院抢救室的位置,
这里现在已经改成了储藏室。陆沉指着墙角的一棵银杏树幼苗:“这是他去世前一天栽的。
”树干上有一道浅浅的刻痕,隐约能看出是个“念”字。“是女儿六岁时用圆规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