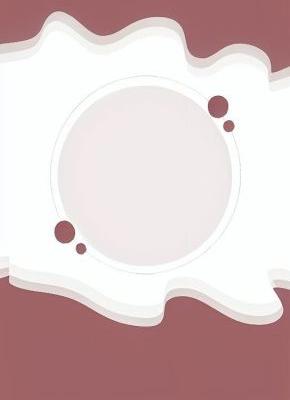一、凭吊者海风咸涩,林致远站在崖山古战场遗址的礁石上,
手中的探测仪发出规律的滴滴声。作为海洋考古学教授,他第六次来到这里,
寻找1279年那个春天沉入海底的秘密。“林教授,潮水开始退了。
”助手小陈在后面喊道,“今天能探测的区域会更大些。”林致远没有回头。
他的目光投向远处平静的海面,那里如今只有渔船和货轮经过,谁会想到七百四十多年前,
这片海域埋葬了整整一个王朝?“小陈,你说十万人集体投海,需要多大的决心?
”助手愣了愣:“按现在心理学分析,这属于群体性认知失调吧……但古代那种忠君思想,
我们现代人很难理解。”忠君思想?林致远苦笑。他读过无数史料,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
就在此时,探测仪突然发出尖锐的鸣叫。这不是寻常的金属反应,而是一种奇特的频率波动。
林致远低头查看显示屏,上面的波形图正自动生成文字:“后来者,你想知道真相吗?
”他的手微微一颤。仪器故障?不可能,这是所里最先进的设备。“教授?
”小陈注意到他的异常。“你先回营地整理昨天的数据。”林致远尽量保持平静,
“我想一个人再待会儿。”等助手的脚步声远去,他对着探测仪低声说:“你是谁?
”海风突然变得轻柔,一个声音仿佛从四面八方传来,又似直接响在脑海:“我是陆秀夫。
大宋最后的丞相。”二、困兽之局陆秀夫的声音透过某种时空的阻隔,带着海风的咸涩传来。
林致远闭上眼睛,感觉意识被拖入另一个维度。我抱着八岁的皇帝赵昺站在船头,
看着眼前这支庞大的流亡船队。说是朝廷,不如说是一座漂浮在海上的城市。
这里有二十万军民,一千四百余艘大小船只。从天子坐舰到渔民的小舢板,
密密麻麻铺满了崖门水道。“丞相,张将军有请。”副将杨镇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他声音沙哑得像生锈的铁器。我点点头,将小皇帝交给贴身宦官。皇帝的龙袍已经洗得发白,
袖口有脱线的痕迹。三个月前,我们从雷州出海时带的绣娘,上周生病,
因为缺乏医药、又是长期颠簸,不幸死了。中军船上,张世杰正对着海图发呆。
这位与我同榜进士的武将,如今两鬓全白,背也微微驼了。“甫阳兄,”我用了他的字,
“情况如何?”他头也不回地向我解释:“我们目前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情况,
淡水补给线已经被敌人或者其他未知因素完全切断了。
这就意味着我们失去了稳定的淡水来源。现在,已经有不少士兵因为实在忍受不了干渴,
开始饮用海水来解渴。然而,饮用海水的后果十分严重,
那些士兵纷纷出现了上吐下泻的症状,身体状况急剧恶化。”海图上,
代表元军的黑色标记像一把钳子,死死卡住崖门出口。张弘范,这个曾经的宋将,
如今成了元军最锋利的刀。“士气呢?”张世杰终于转过身,
眼里的血丝像蛛网:“昨晚三条民船试图趁夜突围,元军用火箭逼他们回来。
船上的不是士兵,是临安逃出来的工匠、读书人,还有……太学生。
”他顿了顿:“张弘范昨日遣使,承诺只要交出陛下,所有平民皆可活命。”“你如何答复?
”“我射死了使者。”张世杰的声音突然低下去,
“但今晨营中流传一句话——‘赵宋气数已尽,何必累及苍生’。”这句话像一根针,
刺穿了我数月来刻意维持的平静。回到御船时,赵昺正在习字。八岁的孩子握着笔,
临摹我前日写的《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
上则为日星……”“陛下,”我跪坐于前,“今日功课如何?”他抬头,
眼睛亮得惊人:“丞相,朕有一问。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要是这样的话,那咱们干脆投降得了,老百姓的命不是更重要吗?
”看着眼前这位流亡的孩童君王,我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说不出话来。
三、火海之夜元军的总攻在次日黎明开始。那不是寻常的水战。张弘范调集了数百艘小船,
满载硫磺、火油与火药,借着北风直直地冲向我方船阵。“保护御船!
”张世杰的吼声在混乱中依然清晰。我站在高处,看着那些火船像流星般撞进我们的阵列。
一条载满妇孺的民船被点燃,火舌瞬间吞没整艘船。惨叫声隔着半里海面依然刺耳,
有几个身影带着火焰跳入海中,在海面上挣扎片刻,沉了下去。“丞相!请带陛下移至后船!
”亲兵满脸烟灰冲上来。我抱起赵昺,孩子紧紧搂住我的脖子,小小的身体在发抖。
“陛下莫怕。”“朕不怕。”他的声音细如蚊蚋,“朕只是……想念临安的荷花。”临安。
我想起那座城市的最后时刻——太皇太后谢道清抱着传国玉玺出降,
文武百官脱去官服混入难民,只有寥寥几人选择随我们南下。文天祥在江西被俘,
张珏在重庆殉城,李芾在潭州举家自焚。大宋三百年基业,最后陪在一个八岁皇帝身边的,
竟只剩下我们这群残兵败将。第二日,张世杰组织突围。二十艘快船如利剑刺向元军阵线。
我在瞭望台上,看见大宋的龙旗在黑色船阵中左冲右突。整整三个时辰后,
只有五艘船伤痕累累地归来。“陆相,”张世杰肩头中箭,军医正在为他包扎,
“北面……北面守将孙安叛变了。”船舱里陷入了死一般寂静。
四、儒家困局那个声音在此刻停顿了。林致远睁开眼睛,发现自己仍在礁石上,
夕阳正沉入海平面。“后来呢?”他轻声问,明知七百年前的一切早已发生。
“后来我做了此生最艰难的决定。”陆秀夫的声音里有一种奇异的平静,
像是汹涌波涛下的深海。夜幕降临,我独自在船舱里踱步。
桌上摊着文天祥被俘前送来的最后一封信:“秀夫吾兄:履善被执,生死已置度外。
唯念一事——我辈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今事至此,惟有一死以报。然死有重于泰山,
有轻于鸿毛。望兄善择。”善择。我苦笑。我有选择吗?忽然想起四十年前,
我中进士那年的殿试。理宗皇帝亲自出题:“论君子小人之辨”。我洋洋洒洒写了三千言,
阐述君子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考官批语:“深得程朱之要旨”。程朱理学。
这四个字贯穿了我一生,也贯穿了大宋最后百年。我推开舱门走上甲板。
海面上飘着未散的硝烟,远处元军营地的篝火像野兽的眼睛。几个值夜的士兵看见我,
默默行礼。“家中还有何人?”我问其中一个年轻士兵。“回丞相,父母在吉州老家,
还有个妹妹……不知还在否。”“恨吗?”他愣了愣,摇头:“不恨。
只恨自己不能多杀几个**。”多杀几个?我望向无边黑暗。杀了又如何?大宋走到今日,
真的是因为蒙古人太强吗?我想起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本欲富国强兵,
却被司马光一句“祖宗之法不可变”打回原形;想起靖康之耻后,朝廷不思进取,
偏安江南;想起理宗朝,贾似道专权,朝中衮衮诸公仍在争论“理气先后”“心性本源”。
我们把儒家经典读得滚瓜烂熟,把圣贤话语挂在嘴边,却忘记了最基本的道理:“民为邦本,
本固邦宁。”或许,大家有意忘却了。“丞相!”急促的脚步声打断我的思绪,
“元军……元军开始喊话了!”五、最后的晨光张弘范的喊话在黎明时分传来,
用的是字正腔圆的汴梁官话:“大宋军民听真!赵宋气数已尽,天命归于大元!今日投降者,
平民可活,军士不杀!若执迷不悟,辰时过后,片甲不留!”声音通过特制的号筒,
在整片海域回荡。我看见周围船只上,许多人站到船舷边倾听。“丞相,”杨镇声音发颤,
“民船那边……有异动。”果然,几条载满百姓的船只开始升起白旗。但更多的船毫无动静。
一条小渔船上,白发老翁朝御船方向深深一揖,然后转身进了船舱。辰时正刻,
元军战鼓擂响。黑色的船阵开始移动,像乌云压向海面。“准备迎战!
”张世杰的吼声响彻舰队。但我已经做出了决定。回到御船,赵昺已经穿好朝服。
八岁的小孩子站在那儿,竟有了一种不属于这个年龄的威严。“陛下,”我跪下行礼,
“今日,臣陪陛下走最后一程。”他点点头,伸手扶我起来:“丞相,朕昨夜梦见父皇了。
他说,黄泉路上不冷清,很多人在等我们。”我实在没忍住,眼泪掉下来了。
抱起他走向船尾时,我最后看了一眼这支大宋最后的舰队。我看见张世杰站在舰首,
长剑指天;看见士兵们握紧武器;看见那些民船上,百姓们互相搀扶着站到船边。没有哭喊,
没有骚乱。只有一种近乎庄严的沉默。海浪在脚底下翻腾,黑黢黢的望不到底。“皇上,
您害怕不?”“有爱卿你在,朕不怕。”我紧紧搂住他,一起跳进了那片深蓝的海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