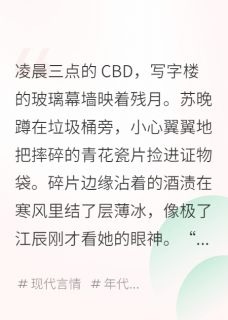凌晨三点的CBD,写字楼的玻璃幕墙映着残月。苏晚蹲在垃圾桶旁,
小心翼翼地把摔碎的青花瓷片捡进证物袋。碎片边缘沾着的酒渍在寒风里结了层薄冰,
像极了江辰刚才看她的眼神。“苏**,确定要立案吗?”穿制服的警察呵出白气,
“江先生说这只是情侣间的小争执。”证物袋里的碎瓷片突然硌得手心发疼。
那是她爷爷临终前交托的清代青花笔洗,上个月刚被列入国家三级文物。半小时前,
它还好好地摆在江辰公寓的博古架上,此刻却成了他盛怒之下的牺牲品。“立。
”苏晚的声音比冬夜的风还冷,“不仅要立案,还要申请文物损伤鉴定。
”警灯在空旷的走廊里明明灭灭,江辰被两个警察架着胳膊,昂贵的定制西装皱成一团。
他看见苏晚把证物袋塞进包里,突然挣脱束缚扑过来:“晚晚!你别闹了!
不就是个破瓷碗吗?我赔你十个!”苏晚侧身躲开,高跟鞋踩在碎瓷片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她想起三小时前,江辰母亲挽着那个穿香奈儿套装的女孩走进来,说“这是林市长的千金,
以后就是你江家的媳妇”时,博古架上的笔洗还在暖光里泛着温润的光泽。“江辰,
”她扯下无名指上的素圈戒指,扔进他怀里,“乾隆年间的青花笔洗,
市场估价两百三十万。记得开发票,我好报销。”警车呼啸而去时,
苏晚仰头看了眼江辰公寓的落地窗。那个叫林薇薇的女孩正踮脚擦掉博古架上的灰尘,
动作轻柔得像在抚摸稀世珍宝。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是博物馆同事发来的微信:“苏姐,
明早九点的‘古陶瓷修复展’布展,你还来吗?”苏晚望着天边渐淡的残月,
指尖在屏幕上敲出两个字:“准到。”故宫角楼的晨雾还没散尽,苏晚已经站在展厅中央。
她穿着藏蓝色工作服,头发利落地挽成髻,露出纤细的脖颈。案台上摆着七零八落的碎瓷片,
在特制灯光下泛着幽光。“这是上周刚收的北宋汝窑残片?
”戴白手套的老专家推了推眼镜,“小苏,你确定能修复?”苏晚没说话,
先用软毛刷清理掉碎片缝隙里的土锈,再取出特制的黏合剂。这种以鱼鳔胶为基底的配方,
是苏家祖传的修复秘术,从她太爷爷那辈起就守护着宫里流出的珍宝。
黏合剂接触瓷片的瞬间,空气中浮起淡淡的鱼腥味。苏晚忽然想起七岁那年,
爷爷把她抱在膝头,用同样的黏合剂修补摔碎的青花瓷碗。“丫头记住,
”老人布满老茧的手覆在她的小手上,“修补瓷器就像缝补人心,急不得,假不得。
”手机在工作服口袋里震动,是陌生号码发来的彩信。照片里,江辰跪在月老祠的香案前,
额头抵着冰凉的地面,手里举着的红绸带写着“苏晚江辰永结同心”。苏晚的指尖顿了顿,
黏合剂在瓷片上拉出细如发丝的银线。她认得那地方,是琉璃厂街尾的百年月老祠,
去年七夕,江辰就是在那里给她系上了同款红绸。“小苏?”老专家的声音拉回她的神思。
“没事。”她深吸一口气,将最后一块碎瓷片精准对接。阳光下,
原本破碎的瓷瓶渐渐显露出完整的轮廓,接缝处的银线在光线下流转,
像极了雨后初晴的彩虹。这是苏家修复术的精髓——金缮。用天然漆黏合碎片,
再以金粉修饰裂痕,让残缺成为独特的风景。就像她此刻的心情,
被摔碎的部分或许永远无法复原,但至少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展厅入口突然传来骚动。
苏晚抬头,看见江辰被保安拦在门外,他手里捧着个锦盒,西装上还沾着泥土,
显然是从月老祠直接赶来的。“晚晚!我知道错了!”他隔着玻璃幕墙大喊,
声音在空旷的展厅里回荡,“我已经跟林薇薇断了!笔洗我会赔!你想要多少都可以!
”苏晚低头继续用金粉勾勒瓷瓶的裂痕,笔尖在釉面上游走,留下细碎的金光。
她想起三个月前,江辰带她去见家长,他母亲看着她工作服上的瓷粉,
皱眉说“我们江家不需要修破烂的媳妇”时,江辰也是这样沉默着,
任由那些刻薄的话像冰锥一样扎进她心里。“江先生,这里是文物展厅。
”保安的声音带着警告,“请你保持安静。”江辰突然打开锦盒,里面铺着的红绸上,
赫然是那枚被苏晚扔掉的素圈戒指。“晚晚,你看!”他举起戒指对着阳光,
“这戒指是我们在周大福挑的,你说要素圈的,
像你爷爷给你奶奶打的那枚……”苏晚握着画笔的手猛地一颤,金粉滴落在洁白的工作台面,
像颗突兀的星辰。爷爷给奶奶打的银戒,此刻正躺在她贴身的荷包里。
那是对民国年间的素圈戒指,内壁刻着彼此的名字,经历过战火纷飞,
却被苏家祖辈用修复瓷器的耐心,呵护了一辈子。“把他请出去。”苏晚的声音没有起伏,
目光始终落在眼前的瓷瓶上。当保安架着江辰离开时,她听见他嘶哑的哭喊:“晚晚!
下个月就是我们的订婚宴!你忘了你答应过要穿旗袍来的吗?
”画笔在瓷瓶的最后一道裂痕上落下收尾的一笔。苏晚放下笔,看着眼前重生的珍宝,
忽然想起爷爷说过的另一句话:“真正的修复,不是掩盖裂痕,而是让裂痕成为勋章。
”订婚宴那天,苏晚果然穿了旗袍。绛红色的杭绸旗袍,盘扣是用老玉雕琢的蝙蝠纹样,
领口绣着细密的缠枝莲。这是她奶奶的嫁妆,上周刚被她亲手修复好磨损的开衩。
宴会厅里觥筹交错,江辰穿着笔挺的礼服站在门口,看见苏晚的瞬间,
眼睛亮得像藏了整片星空。他快步迎上来,想牵她的手,却被她不着痕迹地避开。“晚晚,
你肯来……”他的声音带着难以置信的狂喜。苏晚没理他,径直走向主桌。
江母脸色铁青地坐在那里,身旁的林薇薇穿着白色礼服,像朵不合时宜的白玫瑰。“苏**,
”林薇薇端起香槟,笑意盈盈,“听说你是修文物的?真巧,我爸最近收了个唐三彩,
改天请你去鉴定鉴定?”苏晚看着她腕上的玉镯,那抹浮白的光泽像极了注胶的假货。
“林**,”她淡淡开口,“你这只和田玉手镯,注胶痕迹太明显,
下次不妨去潘家园淘个仿品,至少不会让人看出破绽。”林薇薇的脸瞬间白了。
江母重重放下酒杯:“苏晚!你别给脸不要脸!”“江夫人,
”苏晚从手包里取出一份文件,“这是文物局的鉴定报告,
青花笔洗的修复费用加上精神损失费,总共两百八十万。麻烦让江辰签个字。
”江辰接过文件,手抖得厉害:“晚晚,我们一定要这样吗?”“不然呢?”苏晚看着他,
“你摔碎笔洗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我们?”宴会厅突然安静下来,
所有目光都聚焦在他们身上。江辰的母亲气得浑身发抖,
指着苏晚的鼻子骂:“你这个扫把星!我们江家哪里对不起你?”苏晚没说话,
只是缓缓解开旗袍领口的第一颗盘扣。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
她从贴身的荷包里取出那对民国素圈戒指,轻轻放在桌上。
“这是我爷爷给我奶奶的订婚戒指。”她的声音清晰而稳定,“1943年,
我爷爷在战乱中弄丢了奶奶的戒指,后来他用修文物的手艺,一点点重新打造了一对,
刻上了彼此的名字。”她拿起其中一枚戒指,内壁的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他们说,
感情就像这戒指,磕磕碰碰难免,但只要用心修补,总能回到最初的模样。可惜啊,江辰,
你连修补的耐心都没有。”江辰突然跪了下来,膝盖砸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闷响。“晚晚,
我改!我一定改!”他抓住她的裙摆,“你要我怎么做都行!只要你别走!
”苏晚轻轻挣开他的手,将那对素圈戒指放回荷包。“江辰,”她整理好旗袍的开衩,
“有些东西碎了,就再也拼不回去了。就像这青花瓷,金缮能让它重获新生,
却终究不是原来的样子。”她转身走向门口,绛红色的旗袍裙摆扫过光洁的地面,
留下淡淡的香樟味——那是奶奶用来保存旗袍的香料,带着岁月沉淀的温柔。
走到门口时,苏晚回头看了一眼。江辰还跪在地上,手里紧紧攥着那份鉴定报告,
像个迷路的孩子。林薇薇站在他身后,脸上的得意慢慢变成了困惑。外面的阳光正好,
苏晚深吸一口气,感觉胸口那道被瓷片硌出的伤口,好像终于开始愈合。三个月后,
苏晚在琉璃厂开了家小小的修复工作室。工作室的门楣上挂着块木匾,
是她亲手写的“拾光”二字,笔锋里带着爷爷教的柳体风骨。
靠窗的位置摆着张宽大的工作台,上面总是摊着待修复的瓷器,阳光透过雕花木窗洒进来,
在碎片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这天下午,一个穿藏青色中山装的男人推门进来。
他戴着金丝眼镜,气质温润,手里捧着个锦盒。“请问是苏晚**吗?
”男人的声音像浸过温水的玉,“我叫顾时砚,想请你修复一件东西。”苏晚抬头的瞬间,
心跳漏了一拍。男人的眉眼像极了古画里走出的人物,尤其是鼻梁上那副眼镜,
让她想起博物馆里那幅《柳荫高士图》。“请坐。”她定了定神,接过锦盒。打开的瞬间,
苏晚倒吸一口凉气。锦盒里躺着的,竟然是半块战国时期的玉龙佩,
断裂处还留着明显的火烧痕迹。“这是……”“我家传的东西。”顾时砚推了推眼镜,
“抗战时期被炮火炸成两半,另一半至今下落不明。”苏晚指尖拂过玉佩上的云纹,
触感冰凉而温润。这种级别的古玉修复,在业内堪称难题,尤其是断裂处的火烧痕迹,
几乎不可能完全消除。“顾先生,”她抬头,“这很难。”“我知道。
”顾时砚的目光落在工作台的金缮瓷瓶上,“但我听说,苏**能让裂痕变成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