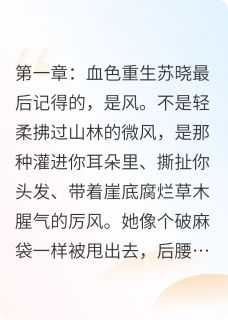苏晓最后记得的,是风。
不是轻柔拂过山林的微风,是那种灌进你耳朵里、撕扯你头发、带着崖底腐烂草木腥气的厉风。她像个破麻袋一样被甩出去,后腰上她爹苏大强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残留的推力还没散干净,耳边炸响的,是她妈王金花尖利的咒骂,和她那个宝贝弟弟苏宝柱拍着巴掌的嘎嘎怪笑。
“赔钱货!军校?你也配?!”
录取通知书那硬挺的纸角,好像还硌在她贴身的口袋里,带着她偷偷焐出来的体温,然后就被她爹粗糙的手指头硬生生扯了出去,撕成了漫天飞舞的碎雪片。
骨头撞上石头的声音,闷得让人心口发紧,然后是刺啦啦的裂响,不知道是衣服还是皮肉。黑暗兜头罩下,又冷又沉。
……
疼。
不是坠崖粉身碎骨那种撕心裂肺的剧痛,是一种细密、钝涩、无处不在的酸疼,丝丝缕缕地从骨头缝里钻出来。苏晓猛地睁开眼。
视野里糊着一层黏腻的汗,屋顶黑黢黢的,几块歪斜的油毡布补丁上,洇开几大片深褐色的水渍霉斑,像死人身上溃烂的疮。一只肥硕的蜘蛛正慢悠悠地爬过那根悬在房梁上、沾满灰吊子的十五瓦灯泡线。昏黄的光晕在清晨灰白的天色里挣扎,勉强照亮了对面墙上那本卷了边、用破钉子歪歪斜斜钉着的日历。
2008年,5月12日。
日期像烧红的烙铁,狠狠烫在她的视网膜上。
苏晓僵住了,连呼吸都忘了。她猛地抬起自己的手——瘦骨伶仃,指关节粗大,手心一层厚厚的老茧,还有几道新鲜的、被猪草汁液染得发绿的口子。指甲缝里塞满了黑泥。
这不是二十二岁、在工厂流水线上熬了七年、指腹被磨得光滑、甚至偷偷攒钱涂过劣质护手霜的那双手。这是她十五岁的手!青峦村,她家这间漏风漏雨的破灶房,那张用门板和砖头垫起来的“床”!
“死丫头!挺尸呢?!猪都没喂,想饿死你弟弟啊?!烂了心肝的下作东西!”木板门被踹得山响,门框上簌簌往下掉灰土,王金花那把能刮破人耳膜的尖嗓子像淬了毒的针,狠狠扎进来。
这声音!苏晓浑身不受控制地一哆嗦,每一个毛孔都在尖叫。太熟悉了!就在她像块石头一样砸向崖底之前,灌满她耳朵的,就是这把嗓子,同样的刻毒,同样的歇斯底里!
“赔钱货还敢藏录取通知书?军校是你这种贱骨头配上的?下去跟你那短命的亲妈作伴吧!”记忆里的狞笑和此刻门外泼妇骂街的声音,诡异地重叠在一起,分毫不差。
一股冰冷的、带着铁锈腥味的恨意,猛地从脚底板窜上天灵盖,瞬间冲散了那点刚重生回来的茫然和酸疼。不是梦。阎王爷不收她这条贱命!老天爷也看不过眼,把她这粒沙子,又给扔回了这滩烂泥里!
“苏晓!耳朵塞驴毛了?!”哐!哐!哐!踹门声更急了,还夹杂着菜刀砍在破门栓上的刺耳刮擦声,木屑飞溅。
苏晓深吸一口气,那口气带着灶房角落里烂菜叶和猪食的馊味,直冲肺管子。她掀开身上那床又硬又沉、一股霉味的破棉被,赤脚踩在冰冷潮湿、黏着泥巴的地面上。脚底的寒气激得她一哆嗦,却也让脑子里最后那点混沌彻底消散。
“来了。”她应了一声,声音干涩嘶哑,没什么力气。可就在她低头穿那双露着脚趾头的破胶鞋时,嘴角却不受控制地、极其缓慢地向上扯了一下,勾出一个冰冷僵硬的弧度。
回来了。
那就好好算算账。
那把撕碎她前程、把她推下悬崖的录取通知书?这次,她要让它变成**那些人喉咙里的刀!一刀,一刀,剐干净!
---
门栓被粗暴地拉开。王金花那张刻薄寡淡的脸堵在门口,三角眼吊着,颧骨高耸,薄嘴唇抿成一条向下撇的线。她手里还拎着那把砍门栓的菜刀,刀刃上沾着新鲜的木屑。
“磨蹭你娘的尸呢?猪饿得嗷嗷叫,听不见?宝柱长身体,等着吃早饭上学!你想饿死他?!”唾沫星子几乎喷到苏晓脸上,带着一股隔夜的蒜臭味。
苏晓垂着眼,长长的睫毛遮住了眼底翻涌的冷意。她没吭声,侧着身子想从王金花旁边挤出去,去院子角落的猪圈。
“哑巴了?跟你那死鬼娘一样是个闷葫芦丧门星!”王金花一把揪住苏晓的胳膊,指甲狠狠掐进她皮肉里,枯树枝一样的手力气大得惊人,拽得她一个趔趄,“大清早丧着个脸给谁看?晦气东西!赶紧喂完猪滚去做饭!宝柱要吃煎鸡蛋,两个!黄要嫩!听见没?!”
胳膊上的剧痛让苏晓咬紧了后槽牙。她抬眼,飞快地扫了一眼院子里。苏大强正蹲在门槛上,“吧嗒吧嗒”抽着旱烟,烟雾缭绕里,那张黑黄干瘦、布满沟壑的脸没什么表情,仿佛眼前发生的一切都跟他无关。他脚边放着一把磨得锃亮的锄头,刃口闪着寒光。
苏晓的目光在那锄头上停留了半秒,前世就是这玩意儿,先砸断了她的腿。她强迫自己移开视线,看向主屋门口。
她那个宝贝弟弟苏宝柱,穿着明显不合身但崭新的“名牌”运动服——那是用本该给她交学费的钱买的——正斜倚着门框,嘴里叼着根棒棒糖,一脸看好戏的得意。他今年十二,被王金花喂得白白胖胖,像个发面馒头,可那双小眼睛里,却闪烁着和他年龄不符的恶毒和贪婪。看见苏晓被揪住,他咧开嘴无声地笑了笑,然后故意地、响亮地“呸”一声,把嘴里的糖渣吐在地上。
苏晓垂下眼,掩去瞳孔深处的冰寒风暴。“听见了,妈。”声音平板无波。
“哼!”王金花这才嫌恶地甩开她的胳膊,像是甩掉什么脏东西,扭头对着苏宝柱时,那张脸瞬间笑成了一朵皱巴巴的菊花,“宝儿啊,快进屋,外头凉!妈这就让这赔钱货给你煎蛋去!双黄的!”
苏晓没再看他们,默默走到墙角,拿起那个豁了口的破木桶,把旁边大锅里隔夜的、已经有些馊味的猪食舀进去。冰冷的木柄硌着掌心的老茧,沉甸甸的。她拎着桶,走向角落用石头垒起来的猪圈。
圈里唯一的那头半大的黑猪,饿得正用鼻子拱着石头缝,哼哼唧唧。苏晓把猪食倒进石槽,看着那猪迫不及待地把整个脑袋都埋进去,发出“呼噜呼噜”的吞咽声。
她站在污浊的泥泞里,清晨山间清冽的空气混着猪粪的恶臭,冲得人脑仁疼。身后主屋里,传来王金花刻意拔高的、带着谄媚的笑语,和苏宝柱颐指气使的嚷嚷声。
“妈!我要喝娃哈哈!昨天小卖部进的!”“喝!妈这就给你钱!省着点花啊宝儿,你爸挣钱不容易…”“哎呀知道啦!啰嗦!快拿钱!还有,我书包脏了,让赔钱货给我洗了!用香皂洗!闻着臭死了!”
苏晓面无表情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抠着粗糙的木桶边缘,指甲缝里塞满黑泥。她慢慢蹲下身,就在猪圈旁边那块被猪拱得格外松软的湿泥地上。
她没有工具。只有手指。
食指的指尖,带着一种近乎麻木的冷静,狠狠戳进冰冷的泥里。泥土的湿气和微弱的腐殖质气味钻进鼻腔。她用力,在泥地上,一笔一划,刻下一个字。
那笔画很深,带着一种刻骨的恨意,仿佛要把指尖的骨头都摁进泥土深处。
正。
第一个笔画,又直又深,像一把刀。
前世,她被推下悬崖前的那个月,在工厂流水线旁边的破本子上,也写满了这样的“正”字。一个笔画代表一天,她数着自己离军校开学还有多少天,数着自己离逃离这个地狱还有多少步。
然后,所有的“正”字,都在漫天飞舞的碎纸片里,在她急速下坠的绝望里,化作了齑粉。
湿冷的泥土沾满了指甲,指尖传来摩擦的刺痛。苏晓盯着那个歪歪扭扭、却透着股狠劲的“正”字,眼神空洞了一瞬,随即被一种更沉、更暗的东西覆盖。
她缓缓抬起沾满泥污的手指,在同样脏污的裤子上随意擦了擦。动作很慢,擦得很用力,仿佛要擦掉的不是泥,而是别的什么东西。
猪还在呼噜噜地抢食。主屋里,苏宝柱正为了新玩具还是新衣服跟他妈撒泼耍赖,声音尖利刺耳。
苏晓站起身,拎起空了的木桶。清晨微弱的阳光,终于费力地爬过远处青黑色山峦的轮廓,吝啬地洒下一片稀薄的光晕,落在她洗得发白、袖口还带着破洞的旧校服上。
光斑跳动在她低垂的眼睫上,却照不进那双深潭般的眸子里。
她转过身,朝着那个喧嚣、恶毒、散发着令人作呕气息的主屋走去。背影单薄得像秋天最后一片挂在枝头的叶子,仿佛一阵风就能吹走。
但每一步,都踩得很实。
泥地上,那个孤零零的“正”字,像个沉默的烙印,浸在冰冷的泥水里。